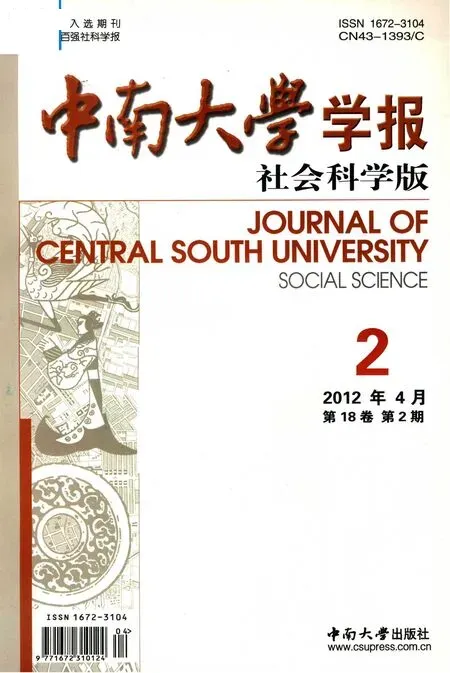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左傳》夢境記載的史官文化特色
夏繼先
(湖北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62)
夢境記敘與描寫是《左傳》記事之一大特色,其次數之多、行文之細、類型之復雜在先秦著作中絕無僅有,以至于招致后世學者諸多非議。晉范寧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1](2361)宋胡安國曰:“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2](784?785)清馮李驊亦曰:“(《左傳》)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3]用諸如此類之儒學家遠離鬼神的眼光看待《左傳》,此種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拋開狹隘的經、史論爭,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分析《左傳》,應更為合理與中肯,也能更接近其本意。
在先秦文獻中,夢的記載并不由《左傳》始,現存最早的文字資料甲骨文中便存有數量眾多的夢境事例,如“貞:王夢隹大甲?王夢不隹大甲?”(《乙編》3085),“王夢不追咸?”(《乙編》3991),“貞:王夢婦好不隹薛?”(《鐵》一一三·四),“貞:亞多鬼夢無疾?”(《前》四·一八·三),“辛丑卜,爭貞:王夢隹齒?”[4](3108)(《丙編》一〇〇)。據熊道麟統計,“現存卜辭占夢記錄,共計二百一十六條辭條”。[5](466)到了周朝,人們對于夢更加看重,甚至設有專門占夢之官。《周禮?春官?占夢》記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兇。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鄭玄、賈公彥注疏說:“正,謂無所感動而自夢;噩,驚愕也;思,覺時所思念也;寤,寐覺也,謂如覺所見而實夢也……。”[1](807?808)在鄭玄、賈公彥看來,正夢為無所思欲也無外物相加的平安自然之夢,噩夢是因驚愕而做之夢,思夢是有所思念而做之夢,寤夢即醒時言及者之夢,喜夢即因喜悅而做之夢,懼夢即因恐懼而做之夢;占夢者根據夢象的吉兇,參照天地陰陽日月星辰的變化去預言國家、君主、臣民的吉兇。可見,占夢、記夢是巫史的重要職責。
即使到了漢代,史官文化仍與卜筮密切相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這同樣說明史官與巫祝相近,除掌史之外,他們又兼司天地鬼神、司災祥占卜等職。因而,對神怪夢異之類的事情的記載與解釋原本就是史官職責的分內之事。夢,在古人看來是一種來自上天的神秘力量,是鬼神的示昭,是對善惡的獎懲,是兇吉禍福的預兆。夢既為上天之預兆與鬼神所驅使,那么,自然可以也必須通過占卜才能知曉其原委。正是由于夢境及闡釋在當時社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夢占、記夢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災祥變異自然就成為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先秦史書中夢的記載的根本原因。因此,作為春秋歷史重要載體的《左傳》,其記夢特色極為鮮明,便不足為奇。
一
盡管占夢、記夢為我國早期歷史書籍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若說夢占在《左傳》作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好像不能令人接受,目前學界有觀點主張,至遲春秋以降史官已經獨立。如尤學工先生認為,周代是史官文化的成熟期[6](13?18)。史官有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后,他們的歷史意識必然也在不斷加強,注重人事應是史官意識之主流。按照這種看法,《左傳》之夢境記載自然不免有些巫卜甚至獵奇因素。
但是,要正確看待《左傳》的夢占,有一點絕不能被忽視——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春秋以來的史官越來越注重人事,并不意味著他們與巫卜完全分離;事實上,史巫之間仍存在著割不斷的密切聯系,有時,這種聯系可能會密切到令人難以置信。因此,有人認為,直至東周,巫史仍密不可分。劉師培在《古學出于史官論》一文中說:“三代之時,稱天而治,天事人事相為表里。天人之學,史實司之。”[7](13)也就是說,夏商周之時,史官肩負著“相為表里”的“天人之學”,包括占夢在內的“天學”是史官的分內職責。臺灣學者李宗侗明確指出:“史至東周時,其職務仍與巫祝難有所分。”[8](3)李宗侗先生談到東周時期巫與史關系密切之觀點,無疑是有其道理的。《帛書·要》記載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云:“我觀其德義耳,我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可見,即使春秋晚期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家孔子,也是把史與巫等同看待的。《左傳》夢境記載,不少與事實相應驗甚至毫厘不爽,正是受這種傳統觀點影響的結果。如“聲伯之夢”:
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9](899)
這是發生在成公十七年的一件事情:聲伯夢見在渡洹水時有人給了他“瓊瑰”讓他吃。“瓊瑰”就是美玉,由于古人死后飯含,所以聲伯懷疑是兇夢而不敢占卜,從鄭國回來后,聲伯又以為“瓊瑰盈懷”指的是自己的從屬眾多,所以就進行了占卜,而聲伯就在占卜的當晚死去。夢對于現實的預言作用在這里簡直無可懷疑。類似的例子在《左傳》中還有許多,例如“韓厥夢子輿”: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9](793)
這是在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時,晉大臣韓厥夢見父親子輿的一個夢。按當時的慣例,作戰時,作為主將的韓厥本來是應該站在車的左邊,但是,由于受到夢中父親的“告誡”,第二天打仗時,韓厥就站在了車的中間自己駕車追趕齊侯,結果與他同車站在兩邊的人都被射中,而韓厥安然無恙。所以,當失去了自己戰車的綦毋張請求上韓厥的車時,韓厥為了安全不讓他處在戰車的兩邊,而是讓他站在自己的身后。這個事例中,夢的應驗同樣準確。“晉侯夢厲鬼”之事更是神乎其神:
晉侯夢大厲,被發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9](849?850)
這件事發生在成公十年。從內容上看,這是一個涉及復仇的夢境記載——此前,趙同、趙括被晉侯所枉殺,于是,趙同、趙括的爺爺向上帝請命,索取晉侯的性命;晉侯之所以亡命,是因為“不義”所致,故晉侯“不食新”。從情節上看,“二豎子”的巧妙應對,良醫的束手無策以及桑田巫對晉侯應時而亡的準確預測,構成了趣味橫生的故事鏈條,使事件顯得離奇曲折。從人物塑造方面看,“二豎子”的機智,良醫的高明,晉侯的反復無常,均栩栩如生。雖然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學技巧,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在史官眼中,關涉人物生死、王位興替的重大事情往往有占釋的神秘色彩,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也就是說,在作者的思想意識中,夢占占據著重要位置。
另外,統治者對巫卜夢占極為重視,妖言惑眾要被處于極刑,因而,無論巫卜夢占過程本身還是對其過程的記載,他們的態度應是極為嚴肅的。《禮記·王制》規定:“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墨子·號令》也記載:“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可見,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準確應驗之夢,在《左傳》中都不是獵奇、不是杜撰;作者真實意圖在于借助這些夢的記述、解釋及其靈驗的“史實經驗”告誡人們——夢是一種準確的預言,夢代表著上天意志,可以決定人事和國家興衰。
總之,歷史是在繼承之中前進的,它的前進不會拋開歷史的積淀;史官與占釋由來已久的天然聯系是《左傳》夢境記敘與記載數量多、行文細、情況復雜的根本原因。
二
《左傳》記夢是復雜的,除了準確無誤的應驗事例外,《左傳》還記述了不少沒有應驗或不遵夢示的事例。對于這些沒有應驗或不遵夢示的事例記載,簡單地講,似乎可以概括為《左傳》實錄精神的體現。但是,仔細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問題并不如此簡單;隱藏在史料背后的作者的思想意識與思維方式,才是決定夢境材料取舍的根本原因。例如“嬰夢天使”: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之乎?”祭之,之明日而亡。[9](821?822)
成公五年,趙嬰夢見天使對自己說:“祭余,余福女。”他按照神的夢示而祭祀天使,卻依然第二天就被放逐。此處神的昭示失去了它威嚴的神秘色彩。在這里趙嬰的非德行為與天使的神通能力之間出現了直接的交鋒,其結果是神的威力也避免不了趙嬰最終受到懲罰。根據《周禮》對夢的分類看,這原屬一個吉夢,但由于趙嬰與其侄媳趙莊姬私通,品德敗壞,雖然做了好夢,卻依然于事無補。其根本原因是“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得其亡乎?”這里作者并不掩飾神的尷尬地位,反而以注重人事的態度客觀敘述,表現了作者的變通思想。
再如“昭公適楚”。這里,夢境更是失去了它的神秘性,甚至夢境究竟何兆,也變得模糊不清: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9](1286?1287)
昭公七年,魯昭公將往楚國,夢見襄公。在根據這個夢來判斷昭公該不該出行時,梓慎與子服惠伯出現了意見分歧。最后昭公聽從了子服惠伯的解釋。就整個事件的前后經過來看,魯昭王去了楚國并沒有發生什么危害,但整個過程又不太順利——在鄭“不能相儀”,在楚不能“答郊勞”。對同一個夢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釋,而并沒有一種解釋完全與后來的事實相一致。
因此,單純從夢占卜筮觀念這一角度看待《左傳》夢境,顯然有失偏頗。可是,我們又不能因為這些沒有應驗與不遵夢示的事例而否認《左傳》作者的占筮意識。要正確看待這一復雜甚至矛盾現象,就不能不注意當時在思想觀念上極具指導作用又為史官掌握的《周易》。
《周易》的變通思想對春秋戰國的史官的作用極為重要。易,歷來有變易、不易和簡易之解說,而以變易為中心。這是用變通的觀點說明社會變動、歷史興亡的必然。總之,變通是貫穿《周易》的指導思想。
《周易》最初是用作卜筮的書,又為史官掌握與收藏。朱熹說:“《易》本為卜筮而作。……《易》本卜筮之書。”《左傳》記載,魯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到魯國,“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可見,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職責需要,而史官的職掌又為其精通《周易》提供了方便。更為重要的是,春秋史官擔任著相當重要的職責,許兆昌先生認為,史官有記事、宣命、占筮、祭祀、禳災、編史等 39項職事,[10](99?103)其歷史使命與現實責任要求他們不僅要掌握足夠的歷史知識,還要貫通古今,通曉歷史的發展、變化及事物之間的聯系,以便以史為鑒,有補于時。因此,吳懷祺先生說:“中國史學還處在童年時期,就和易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受到《周易》的影響。”[11](14)再者,春秋戰國這樣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客觀上也要求史官看待問題必須具有通變思想。《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
趙簡子問于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候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衿之?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9](1519?1520)
這里史墨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論述江山易主、君臣易位這一歷史發展變化的規律,并引用《詩經》的詩句和《周易》的卦象來論證這種變化的合理性。這段議論代表了春秋戰國史官的通變思想。因此,即使對于那些沒有應驗的夢境,作者并沒有掩飾或隱瞞它們的存在,而是盡力從禮與人道的角度去解釋。這從側面也說明了史官觀念由巫史到史官的歷史轉化過程。
受《周易》變通思想影響的另一直接結果就是對人事的注重。由“尊神”到“重人”,人,越來越成為社會的主導,正如何新文先生所說“在這一切變化中,人的變化,亦即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價值和作用的被認識,是最顯著、最引人注目的”。[12](273)在這種變通思想影響下,《左傳》夢境記載自然就打破了神秘神圣的一統局面,而具有了人事的特色。例如“寧武子諫祭相”: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 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9](487)
在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見康叔(衛成公的祖先)對他說:“相奪予享。”于是衛成公就讓人祭祀相,但是遭到了寧武子的反對,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對于這一事件,明代傅遜有精辟論斷,他在《春秋左傳屬事》中就此事贊嘆寧武子道:“武子之忠一也……且文公時衛亦多故矣,武子安能養晦以自逸也。魯史載諸國事多略,遂不少概見。惜哉噫!其論相祀尤能據正守禮而不媚神于邪矣!”[13](823)“據正守禮”是傅遜對寧武子通曉禮儀的肯定與贊揚,“不媚于神”表明了以寧武子為代表的春秋知識分子開始了從天命到人事的思想轉化。《左傳》的客觀記述,同樣也表明了《左傳》作者的注重人事的思想傾向。上文提到的“ 趙嬰夢天使”同樣具有人事因素。“結草報恩”更是純粹關乎人事的一個夢境記載: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9](764)
宣公十五年記載,秦晉在輔氏交戰之時,一老人用結草的方式將秦國大力士杜回絆倒,魏顆因此俘獲了杜回。晚上,魏顆做的一個夢揭示了這一離奇事件——原來魏顆曾經違背父命自作主張嫁了魏武子的小妾而沒有將她殉葬。這是一個完全沒有上天神秘意志的夢境,在這個夢的記載中,人的行為成為了主宰。魏顆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事的勝利。
對于這些夢境,作者沒有因為它們無法驗證就刻意回避,相反,《左傳》是以史家的變通思想客觀看待、闡釋它的。正是具有了這種變通思想,《左傳》記夢才顯得如此復雜,如此靈活,也如此客觀。
三
要全面分析《左傳》的夢境描寫,還要注意《左傳》受禮的觀念的影響。周代史官與周禮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周代史官匯天下學術于一身,他們不僅參與了周禮的制作,還是周禮的管理者和執行者。此外,他們還通過特殊的“書法”方式捍衛周禮。《左傳》特別注重“禮”的原因也在于此,上自祭祀、戰爭,下至言語、服飾等等,無不突顯禮的特征。據統計,整部《左傳》講到“禮”字共462次,禮成為社會生活最有權威的制約因素。《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晏子與齊侯談話時說到: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9](1480)
禮要求作為君主發布命令要不違背道理;作為臣子要恭敬,不懷異心;作為父親要慈愛;作為子女要孝順。只要有了禮的存在,社會就會和諧,家庭就會美滿。禮在整個社會、家庭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禮,社會就會混亂、敗亡。例如,《左傳·僖公十一年》記載,周天子派內史過到晉國賜命,晉惠公受玉時表現得不夠恭敬,內史過回去向周天子報告說:“晉侯其無后乎! 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半年以后,晉惠公果然死去。內史過的預言之所以應驗,是因為他從這小節中看出了大問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無論《左傳》中記載的應驗性的夢境還是沒有應驗的夢境,甚至以夢為借口實現個人私利之事,大多都貫穿著一個“禮”的主題。好多無法解釋的夢境,從禮的角度分析,就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如僖公四年,驪姬為了立自己的親生兒子為嗣君,欲陷害太子申生,《左傳·僖公四年》記載: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9](296?297)
驪姬為陷害太子以“君夢齊姜”為幌子,誘使太子祭獻母親,歸胙于獻公。如此一來,驪姬乘機下毒陷害申生。這顯然不是一個真實的夢,但它與夢密切相關,更與禮密不可分。這里夢成了驪姬殺人的工具,驪姬的行為從內在而言是其私欲使然,從外在看是失去了禮的約束的結果。又如,《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9](1035?1036)
這樣一個夢看起來不可思議,其實,對它的記載正體現了《左傳》重禮的特色——晉伐齊,引起了荀偃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心病。成公十八年,晉厲公被荀偃派人所殺,雖時過已久,但“弒君”的不仁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于是夢中就發生了與厲公爭執的情節,并被厲公戈擊“首墜于前”,捧著腦袋跪走。從中可以窺知荀偃做出“弒君”這樣僭禮的行為是此夢的根源,一年以后他的死自然是對他這種越禮行為的懲罰。僖公二十八年記載的“子玉夢河神”更是由于子玉對“神”和“國家”的雙重無禮招致了自己的身亡:
初, 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 況瓊玉乎?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將何愛焉?”弗聽。[9](467?468)
在晉楚城濮之戰前,楚國令尹子玉夢見河神要子玉把自己的瓊弁和玉纓送給河神,子玉沒有照辦,后來子玉果然戰死。在這里,神對于子玉違反自己意愿的懲罰已變得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子玉對國家利益的態度。按照時人的看法,子玉無論如何都應該把瓊弁和玉纓獻給河神,如榮季所說:“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但子玉舍不得自己的瓊弁和玉纓,所以當時人們就說:“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軍事上的失敗不僅僅有神的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子玉自身對于國家的“無禮”造成的。
《左傳》夢境記載數量多、情況復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分析的因素之外,《左傳》作者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左丘明還是他人?是一個人還是經過不同作者之手?這些顯然都會影響到《左傳》記夢的特色。囿于材料所限,關于《左傳》作者至今仍爭論不休,慎重起見,本文沒有談及。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左傳》的夢境記載是巫史文化交錯時代的必然結果,它的記述方式及特色與史官文化、史官意識密不可分。
[1](清)阮元.十三經注疏[M].中華書局, 1980.
[2](宋)王應麟.困學紀聞[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清)馮李驊、陸浩評點.左繡[M].清康熙善成堂刊本.
[4]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M].中華書局, 1996.
[5]熊道麟.先秦夢文化探微[M].學海出版社, 2004.
[6]尤學工.先秦史官與史學[J].史學史研究, 2001(4): 13?18.
[7]劉師培.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李宗侗.中國史學史[M].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84.
[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10]許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與文化[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11]吳懷琪.說《周易》的變通史學思想[J].史學史研究, 1987(3):14.
[12]何新文.人的發現與文的新變——春秋時代文學藝術略論[J].社會科學戰線, 1990(1): 273.
[13](明)傅遜.春秋左傳屬事[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第169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