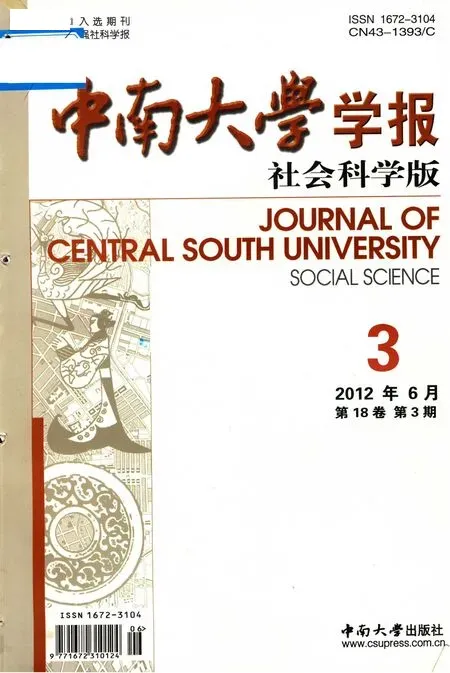區分即成犯、狀態犯與繼續犯的再審視
陳洪兵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46)
區分即成犯、狀態犯與繼續犯的再審視
陳洪兵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46)
屬于何種犯罪形態,主要關系到共犯、罪數的認定與追訴時效起算時間的確定。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僅具有觀念上的意義,而區分狀態犯與繼續犯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屬于何種犯罪形態,背后的規范性考量還是法益的保護。值得持續地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屬于繼續犯,否則屬于狀態犯或即成犯。典型繼續犯有非法拘禁罪、不真正不作為犯、持有型犯罪、危險駕駛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重婚罪、綁架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拐騙兒童罪屬于狀態犯而不是繼續犯,拐賣婦女、兒童罪不屬于繼續犯而是即成犯。窩藏罪、贓物犯罪屬于何種犯罪形態應根據行為表現具體確定。
即成犯;狀態犯;繼續犯;法益
一、區分的意義
根據犯罪既遂時期、終了時期、法益侵害狀態及構成要件符合性之間的關系,刑法理論通常對具體犯罪進行即成犯、狀態犯與繼續犯的歸類。一般來說,即成犯是指隨著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犯罪即成立而且同時終了的犯罪。殺人罪、放火罪等大多數犯罪都是即成犯。繼續犯(也稱持續犯)是指隨著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犯罪便既遂,但其后不法行為與不法狀態仍然處于持續狀態的犯罪。逮捕監禁罪(即非法拘禁罪)與不保護罪(即遺棄罪)是其適例。狀態犯是指隨著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犯罪便終了,但法益侵害的狀態仍在持續的犯罪。盜竊罪與傷害罪是其適例。[1](55)
對犯罪進行分類一定是服務于某種目的,否則就純屬學者們的游戲。刑法理論通常認為進行這種區分具有如下理論意義:
第一,犯罪實施期間出現新法或刑罰變更時會存在適用新法還是舊法的不同。[2](131)我國相關司法解釋也肯定了這一立場。例如,1997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第十二條若干問題的通知》指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對10月1日以后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學界均認為這里的“繼續到”指的是繼續犯的情形,即假定行為人從舊法實施期間非法拘禁他人一直持續到新法生效之后,則可以適用新法一并追訴。本來,新法原則上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繼續犯可能適用新法而排斥舊法的適用。
但是,以前不受懲處的情形,即便是繼續犯也并不當然地適用新法而追究責任。例如,刑法理論一般認為持有型犯罪屬于繼續犯。[3]《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持有偽造的發票罪作為第210條之一。假定行為人在該修正案通過之前一直在家中藏有大量偽造的發票,修正案通過之后,行為人雖然知道持有偽造的發票的行為已經入罪,但由于本人從該修正案通過之前(2011年2月25日之前)直至生效之后(2011年5月1日之后)一直處于被非法拘禁的狀態,而無法消除非法持有偽造的發票這種狀態。行為人雖然已經意識到非法持有偽造的發票是犯罪,但沒有消除非法持有狀態的可能性,根據責任主義原則,還是沒有適用新法的可能性。因此,所謂繼續犯可能適用新法,其實不過是可以根據刑法評價新法生效之后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并非能夠以新法評價生效之前的行為。[4](29)
第二,涉及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問題。理論上通常認為,狀態犯完成后,在法益侵害狀態持續期間,只要是在該構成要件已經完全評價的范圍內,不另外構成犯罪。例如,盜竊財物后加以毀壞、拋棄的,不在盜竊罪之外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這就是理論上所稱的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即共罰的事后行為)。但是事后行為若超出構成要件預定的范圍,侵害了新的法益,則仍有另外定罪的可能性。例如,盜竊他人銀行存折后到銀行柜臺取款,則在盜竊罪之外因為侵害了新的法益而另外構成詐騙罪。[5](131)事后行為能否進行單獨評價,與屬于何種犯罪形態并沒有關系,而是取決于是否實施了新的行為、侵害了新的法益,是否已由前行為所符合的構成要件進行了充分的評價,以及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等方面。例如,盜竊之后窩藏贓物,之所以不另外成立贓物犯罪,是因為缺乏期待可能性。盜竊之后加以毀壞,是因為法益侵害事實已由盜竊罪進行了包括性評價,沒有侵害新的法益。但如果十六周歲生日這一天進行盜竊,因未達到刑事法定責任年齡而不成立盜竊罪,若生日過后第二天加以毀壞的,無疑符合故意毀壞財物罪構成要件。因為,先前盜竊行為(符合盜竊罪的客觀違法構成要件)沒有對法益侵害事實進行評價。不知是槍支而盜竊,之后予以藏匿的,是因為在侵害財產權之外,藏匿槍支的行為還對公共安全形成了抽象性危險,盡管期待可能性也較低,但為了有效保護法益,還是可能在盜竊罪之外另外評價非法持有槍支罪。又如,理論上一般認為殺人罪是典型的即成犯,而且認為殺人后碎尸的,不另定侮辱尸體罪。但是,尸體的尊嚴顯然不同于活人的生命法益。從有效保護法益角度考慮,殺人后碎尸的,應當數罪并罰。
第三,涉及能否進行正當防衛的問題。理論上通常認為,在狀態犯的場合,由于犯罪終了后僅僅是法益侵害狀態的繼續,因而不能進行正當防衛;而在繼續犯的場合,由于實行行為在繼續,犯罪并未終了,因而有實施正當防衛的可能。[2](131)但是,進行正當防衛的前提并非必須存在該當構成要件的行為,只要具有防衛的緊迫性、挽救法益的可能性,就能進行正當防衛。這樣不僅繼續犯,對于狀態犯也可能進行正當防衛。[6](105)例如,盜竊犯剛離開現場,雖然已經既遂,之后僅僅是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但理論上公認,只要還存在及時挽回法益的可能性,仍有成立正當防衛的可能。同樣,雖然一般認為傷害罪是狀態犯,但在已經造成傷害結果(如受傷流血,被害者正忍受著劇痛),被害人本人或者其他人實施正當防衛逼迫加害人救助法益(如強迫送醫)也是可能的。
第四,涉及何時開始計算追訴時效的問題。刑法理論公認,屬于何種犯罪形態,直接關系到從何時開始計算追訴時效。[7](158)我國刑法第89條第1款后段規定:“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理論通說認為,這是關于連續犯和繼續犯的規定,繼續犯的追訴時效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例如,非法拘禁罪的追訴時效從結束非法拘禁狀態(即被拘禁人重獲自由)之日起計算。[8](315)又如,如果認為重婚罪是繼續犯,則意味著追訴時效從結束重婚狀態而不是從重婚之日起計算。重婚罪法定最高刑為二年,追訴時效為五年。若堅持認為重婚罪是繼續犯,則意味著即便已經重婚三十年(已經抱上了孫子)也沒有超過追訴時效。還如,若認為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法定最高刑為三年)與拐騙兒童罪(法定最高刑為十年)是繼續犯,則意味著只要被拐賣、拐騙的兒童不被解救,則追訴時效就一直不能開始起算。相反,若認為重婚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拐騙兒童罪是狀態犯或者即成犯,則追訴時效從重婚、收買、拐騙之日起開始計算。因此,犯罪形態的確定對于追訴時效的計算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第五,涉及到罪數認定的問題。例如,理論通說認為,非法拘禁罪是典型的繼續犯,犯罪既遂之后,因為犯罪的實行行為還處于繼續中,而僅成立非法拘禁罪一罪。[9](175?176)又如,如果認為拐騙兒童罪是繼續犯,則拐騙兒童后非法剝奪兒童自由的,不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相反,若認為拐騙兒童罪是狀態犯,則因為拐騙者實施了新的行為,侵害了新的法益,應當以非法拘禁罪與拐騙兒童罪數罪并罰。再如,若認為綁架罪是繼續犯,則綁架之后繼續非法剝奪自由的,不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相反,若認為屬于狀態犯,則應以非法拘禁罪與綁架罪數罪并罰。可見,屬于何種犯罪形態直接關系到罪數的認定。
第六,涉及到共犯的認定。例如,理論通說認為,對于非法拘禁罪這種典型的繼續犯,將他人關押在某一場所,只要不釋放他人,該當構成要件的行為便尚未終了,只要行為尚未終了,如果其他人在這期間參與了犯罪,則可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10](86)又如,若認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騙兒童罪是繼續犯,則收買、拐騙之后參與撫養的,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騙兒童罪的共犯。相反,若認為屬于即成犯或者狀態犯,則不成立上述犯罪的共犯,對被拐賣人、被拐騙人存在非法剝奪自由行為的,單獨成立非法拘禁罪。再如,若認為重婚罪是繼續犯,則在他人重婚之后勸說他人繼續保持重婚狀態的,有成立重婚罪幫助犯的余地。反之,若認為屬于狀態犯,則沒有成立重婚罪共犯的余地。還如,若認為綁架罪是繼續犯,則在他人綁架人質后參與看管人質的,成立綁架罪的共犯。反之,若認為屬于狀態犯或者即成犯,則只能單獨成立非法拘禁罪。可見,屬于何種犯罪形態,對于確定共犯的成立范圍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雖然理論上認為屬于何種犯罪形態關系到新法的適用、不可罰的事后行為、正當防衛、罪數、共犯與追訴時效等的認定處理,但主要涉及到的還是罪數、共犯及追訴時效的認定處理。正確確定犯罪形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如何區分
德國學者一般僅區分狀態犯(Zustandsdelikte)與繼續犯(Dauerdelikte),而日本學者與我國學者則區分即成犯、狀態犯與繼續犯。[11](330)
關于即成犯的概念,代表性的觀點有:①“即成犯,是指犯罪行為實行終了,犯罪即行完成的犯罪形態。它有兩種情況:一是犯罪實行終了,犯罪既遂成立,沒有不法狀態繼續的犯罪,例如,殺人罪。一是犯罪實行終了,仍有不法狀態繼續的犯罪,例如,盜竊罪。也有學者認為,第一種是即成犯,第二種是狀態犯。我們認為,從犯罪行為實行終了,犯罪即行完成這一特征來看,狀態犯也是具備的,所以將它作為即成犯的兩種情況之一,更符合實際。”[12](184?185)②“由于一定法益之侵害或侵害危險之發生,犯罪立即完成,或同時終了之犯罪類型。例如放火罪、殺人罪,刑法上大部分犯罪屬于即成犯。”[13](76)③“即成犯是指犯罪與法益的侵害同時結束。殺人罪就是典型的即成犯,一旦發生殺害了他人這一結果,由于不可能再一次殺害,其時犯罪也便終了。”[10](85)④“即成犯,是指一旦發生法益侵害結果,犯罪便同時終了,犯罪一終了法益就同時消滅的情況。故意殺人罪便是如此。”[14](171)
關于狀態犯的概念,代表性的觀點有:①“所謂的狀態犯,是指犯罪既遂以后,實行行為所導致的不法狀態處于持續之中的犯罪形態。”[15](388)②“情況犯(Zustandsdelikte或譯狀態犯)是指,特定情況的引發,犯罪就已結束。犯罪是否已經結束,與行為人的意志不再有關系,犯罪狀態不能被持續地實現。刑法所規定的犯罪類型,大多屬于情況犯,例如:殺人、傷害、毀損、重婚。殺人后,被害人死亡,犯罪狀態即已結束,行為人不可能對于一個死人,持續再加以傷害;犯罪人意志不能左右犯罪狀態是否持續。重婚者雖然持續利用自己所制造的違法情況,但無須反復實施重婚行為。至于竊盜,行為人將竊取的物品放回原處,已經無改財產監督權一度被侵犯的狀態,所以竊盜是情況犯。”[16](49)③“人們用狀態犯這一概念來表示這樣一些隨著造成一種確定的狀態(通常是結果犯意義上的結果)而結束的構成行為,也就是說,對這種狀態不能也不需要通過行為人來維持。經典的例子是殺人罪,但是,還有身體傷害和毀壞財產。人們還應當將重婚罪或者偽造身份這些行為過程計算在狀態犯之中。雖然行為人在這里繼續利用自己創設的這個狀態,但是在這里并不存在經常重復的重婚性結婚,并且在大多數案件中,也不存在對一次性完成的偽造身份的重復情況。”[11](330)④“對某種法益實施侵害之后,犯罪即告結束,但之后,由于行為人的干預,使對法益的不法侵害處于繼續狀態,但這種狀態并不構成新的犯罪的情況,盜竊罪就是適例。犯人在盜竊取財之后,即便又實施運輸、損壞、消費、銷贓等行為,這種行為只要是在當初的犯罪構成要件所預定的范圍之內,就不構成新的犯罪。”[17](128)⑤“狀態犯,是指一旦發生法益侵害結果,犯罪便同時終了,但法益受侵害的狀態仍在持續的情況。如盜竊罪。”[7](158)
關于繼續犯的概念,代表性的觀點有:①“所謂繼續犯,亦稱持續犯,是指犯罪行為自著手實行之時直至其構成既遂,且通常在既遂之后至犯罪行為終了的一定時間內該犯罪行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狀態同時處于持續過程中的犯罪形態。”[18](123)②“繼續犯是指違法行為著手實施后,在停止之前持續地侵害同一客體的犯罪……有人認為,繼續犯的本質特征,是行為與不法狀態同時繼續,如通說就是持這種觀點……所以,不能把非法拘禁行為對客體侵害的繼續等同于非法拘禁行為本身的繼續。”[19](145)③“繼續犯,是指實行行為以及法益侵害狀態在一定時間內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的情形。如非法拘禁罪,行為人采取一定的非法方法將他人的人身自由予以剝奪后,其犯罪行為在釋放被害人之前的時間內一直處于持續狀態。此外,綁架罪、重婚罪、遺棄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也屬于繼續犯。”[20]④繼續犯則比如像刑法第22條的監禁罪這樣的,由于發生了法益侵害等結果,犯罪就成立了,在法益侵害等結果持續期間,犯罪也持續地成立著……繼續犯在法益侵害等的結果持續期間持續地成立,這是因為持續地肯定了引起了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的法益侵害等的結果(由于具備了同等的侵害性),從而持續地肯定了構成要件該當性(構成要件該當性的繼續或持續的更新)。[21](47?48)⑤“繼續犯,是指在法益侵害的持續期間,實行行為或者構成要件符合性也在持續的情況。危險駕駛罪與非法拘禁罪是其適例。”[14](171)
如何區分即成犯、狀態犯與繼續犯,其實需要回答4個問題:①應否嚴格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 ②狀態犯是否必須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 ③繼續犯的本質特征是否在于行為與不法狀態同時在持續,或者說持續的是行為還是行為的效果? ④區分三種形態的規范性考量是什么?
首先,應否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 日本刑法理論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而德國刑法理論中只有狀態犯與繼續犯的區分,認為即成犯是能夠被狀態犯所包含的一種構成要件類型。[22](144)不過,日本學者山口厚指出,“由于即成犯與狀態犯無論何者都是由于法益侵害的發生而導致犯罪的成立并且終了,在此之后不過是法益侵害狀態在繼續,在這些點上是共通的,所以兩者在概念上加以區分的意義、并且這種區分是否可能,都是有疑問的。”[21](48)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從犯罪行為實行終了,犯罪即行完成這一特征來看,狀態犯也是具備的,所以將它作為即成犯的兩種情況之一,更符合實際。”[12](185)
的確,即成犯與狀態犯的共通之處在于,犯罪完成及既遂的同時,犯罪也隨之終了,不管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繼續,都不影響共犯、罪數的認定及追訴時效的起算。例如,承認即成犯與狀態犯的分類的學者公認,殺人罪和盜竊罪分別是即成犯與狀態犯的適例。[23](129)殺人罪與盜竊罪在共犯、罪數的認定與追訴時效的起算上并沒有區別。區別僅在于,殺人導致他人死亡后,法益即消滅,而盜竊導致他人喪失對財產的占有后,不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狀態或者說他人財產被剝奪的狀態還在持續,還可能通過追繳挽回損失(如后所述,盜電等即時消費型的盜竊犯罪既遂之時也是法益消滅之時),包括被害人在內的他人還可能通過正當防衛(例如剛剛離開現場)和自救行為挽回財產的損失,而且既然法益侵害狀態還在持續,他人事后參與的,還可能成立如贓物犯罪在內(傳統上的事后共犯)的其他犯罪。例如,故意殺人中,死亡結果的發生,意味著犯罪的完成與犯罪的既遂,也意味著他人生命法益的消滅。而一般盜竊罪,控制被害人的財物后雖然是盜竊犯罪的完成,同時意味著盜竊罪的既遂,也可謂盜竊犯罪的終了。但畢竟不法占有他人財產的這種狀態,即法益侵害的狀態還在持續,他人的財產法益并沒有消滅(盜電等即時消費的除外),除可能針對這種不法占有他人的財產的狀態實施正當防衛或自救行為外,他人事后參與窩藏、轉移贓物的,他人還單獨成立贓物犯罪,而且犯罪查獲后對于盜竊所得還能進行追繳,以消除這種法益侵害狀態。而這些對于故意殺人罪這種即成犯而言,顯然不會發生。又如,就拐賣婦女、兒童罪而言,出賣成功,將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交付給收買者,則意味著人不能被作為商品出售這種人格尊嚴法益已經受到侵害,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已由收買人接管,完全進入收買人的管轄領域,因此,不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繼續的情形,故可以認為拐賣婦女、兒童罪屬于即成犯。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雖然隨著收買行為的完成,也意味著犯罪的完成、既遂與終了,但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被非法控制的狀態還在持續,本人或者他人非法剝奪其人身自由的,還能另外構成非法拘禁罪。而且,既然法益侵害狀態還在持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負有解救的職責,收買人或者其他人阻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進行解救的,還能另外構成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或者妨害公務罪。同樣,就拐騙兒童罪而言,雖然隨著拐騙行為的完成,也意味著犯罪既遂與終了,但非法控制兒童的狀態還在持續,本人或者他人在拐騙之后非法剝奪其人身自由的,還能另外構成非法拘禁罪。而且,由于法益侵害狀態還在持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負有解救的職責,拐騙人或者其他人阻礙解救的,還能另外構成妨害公務罪。因此,相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這種即成犯而言,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屬于狀態犯(筆者反對認為屬于繼續犯的觀點)。
綜上,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旨在強調犯罪既遂之后法益侵害狀態是否還在持續,能否實施正當防衛與自救,是否存在贓物犯罪及其他犯罪的可能性,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負有結束法益侵害狀態的職責等。因此,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具有一定的意義,但由于這種區分通常并不直接涉及到共犯、罪數與追訴時效等問題,難以明確區分時,沒有必要強行進行區分。或者說,即成犯與狀態犯的區分,相對于狀態犯與繼續犯的區分,基本上僅具有觀念上的意義。
其次,主張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的學者通常認為,即成犯意味著犯罪完成的同時,犯罪即終了,法益亦消滅,不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而狀態犯均存在不法狀態的持續,即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繼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絕對。例如,他們認為殺人罪與放火罪屬于即成犯。[9](174)但是,殺人也未必意味著一蹴而就。假定行為人在為他人裝修房屋時,有意在墻中安裝一種揮發致癌性物質的材料,自然意義上的殺人行為已經結束,但直到被害人死亡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在被害人死亡之前也可謂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又如,國外刑法理論在放火罪既遂標準問題上,多數說主張獨立燃燒說。[24](371)按照獨立燃燒說,放火形成獨立燃燒狀態雖已既遂,但只要火勢還處于蔓延、公共危險還處于擴大狀態,就不能說犯罪已經終了、法益已經消滅。因此,即便是所謂典型的即成犯,也不能說就不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繼續的情形。再如,主張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的學者公認盜竊罪是狀態犯,但在盜電這種即時消費的場合(例如將他人家的電通過電線引入到自家的冰箱上使用),犯罪完成、既遂后,犯罪即終了,法益也隨之消滅,并不存在所謂法益侵害狀態的繼續。[4](29)因此,即便是典型的狀態犯,也未必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總之,即成犯存在法益侵害繼續的情形,狀態犯也存在法益隨之消滅的狀況。簡言之,犯罪終了后是法益隨之消滅還是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只是即成犯與狀態犯的一般性區別,并不是絕對性的區分標志。
再次,通常認為繼續犯的本質特征是不法行為與不法狀態的同時持續,[25](177)但持續的到底是行為本身還是僅為行為的效果,值得研究。就非法拘禁罪這種典型繼續犯而言,若認為非法拘禁行為一直在持續,假定國慶長假前圖書館管理者不小心將認真讀書的學生鎖在圖書館,過失非法拘禁顯然無罪,行為人鎖門之后立即回到鄉下老家,幾天后方才想起可能將學生鎖在圖書館了,這時因為無法與學校取得聯系,直到長途跋涉從老家返回后學生才得以解救(但已奄奄一息)。若認為繼續犯存在行為本身的繼續,則只要行為人中途意識到了非法拘禁他人的事實,就意味著不僅具有非法拘禁的行為,還具有非法拘禁的故意,即便此時并沒有釋放的可能性,也能成立非法拘禁罪,這恐怕存在疑問。對此,日本學者山口厚認為,繼續犯中所謂行為的繼續不過是擬制而已,實際上持續的只是行為的效果。上述設例中,在意識到把他人鎖在圖書館之后,是否構成犯罪,取決于是否具有作為的可能性,即屬于不作為犯的問題。由于沒有作為的可能性,當然不成立監禁罪。[21](48)國內也有學者認為,“不能把非法拘禁行為對客體侵害的繼續等同于非法拘禁行為本身的繼續。”[19](145)
筆者認為,反對行為本身的持續而主張只是行為效果的持續的觀點,的確值得傾聽。但非法拘禁中的行為并非鎖門、捆綁這類自然意義上的動作,而是規范性意義上的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狀態。在過失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場合,符合了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只是不具有有責性(不具有故意)而不成立犯罪,但在意識到非法拘禁他人事實后,由過失的先前行為引起了釋放被害人的作為義務,能釋放而不釋放的,才構成非法拘禁罪。也就是說,即便堅持行為繼續說,按照不作為犯來處理,也不至于不當擴大處罰范圍。因此,我們還是應堅持行為繼續說。
最后,進行這種區分,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或威脅法益,刑法的目的則是保護法益。[7](72)共犯的認定、罪數的處理及追訴時效起算時間的確定,無不與法益的保護有關。例如,盜竊后不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狀態在繼續,因而學界公認盜竊罪是狀態犯,而非法拘禁罪雖然罪質輕于盜竊罪(從法定刑上可以看出),學界卻公認非法拘禁罪是繼續犯,在非法拘禁后參與看管的可以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追訴時效不是從非法拘禁之日而是從被害人重獲自由之時,原因何在? 盜竊后雖然不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狀態在持續,一方面,在一般觀念上很難認為盜竊在持續(持續地侵害占有),另一方面,盜竊后本人處分盜得財物的行為,要么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如毀壞所盜竊的財物,或者因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任何犯罪,如轉移、窩藏、向知情者銷售贓物,要么本犯以外的人參與窩藏、轉移、銷售贓物的,可以贓物犯罪論處。而且,對于盜竊后不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狀態,在追訴時效的起算上也沒有必要從結束不法占有他人財產狀態之日起計算。質言之,將盜竊罪作為狀態犯對待,符合法益保護原則。而在非法拘禁狀態持續期間,他人的人身自由在持續性受到侵害,刑法不可能坐視不管,必須要求行為人立即釋放被害人。因而放任非法拘禁狀態繼續的,值得肯定持續性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追訴時效當然應從結束非法拘禁狀態之日起開始計算。他人參與看管的,由于繼續惡化法益的侵害,因而應當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否則,不利于有效保護法益。
又如,如果認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是繼續犯,則意味著收買后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行為,不能另定非法拘禁罪。這樣處理,既不利于保護法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僅為三年有期徒刑),也有違第241條第3、4款關于數罪并罰的規定。只有認為該罪屬于狀態犯,才能對在收買后非法剝奪自由的,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非法拘禁罪數罪并罰。而且,即便由于認為是狀態犯而導致追訴時效從收買之日起計算,如果收買后存在非法拘禁行為,同樣可以按照繼續犯來計算追訴時效,從而有效保護法益。
再如,之所以理論上認為持有型犯罪屬于繼續犯而不是狀態犯,[15](388)顯然是因為,在非法持有狀態持續期間,法益侵害在持續,構成要件符合性在持續性地得到肯定,中途參與的,應當認定為共犯,追訴時效也應從結束非法持有狀態之日起計算。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追訴時效只能從結束非法持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之日起計算,否則,不利于保護法益。
綜上,筆者認為,即成犯是指犯罪完成通常就意味著犯罪的終了、既遂及法益的消滅的一種犯罪形態。狀態犯是指犯罪完成、終了及既遂之后,通常還存在需要加以消除的持續性法益侵害狀態的犯罪形態。繼續犯是指犯罪完成、既遂之后,規范性意義上的行為與法益侵害狀態同時在持續,構成要件符合性在持續性地得到肯定的一種犯罪形態。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通常應看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狀態的持續;區分狀態犯與繼續犯,通常應看是否存在行為與法益侵害狀態的同時持續、能否持續性地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
三、具體分類
由于大多數犯罪屬于即成犯,[9](174)而且區分即成犯與狀態犯在觀念上的意義超過實際的意義,故犯罪形態區分的重點應放在繼續犯與狀態犯的區分,而繼續犯只有少數幾個罪名,因此只需辨析少數幾個典型的狀態犯與繼續犯罪名即可。
關于有哪些典型狀態犯與繼續犯罪名,國內代表性觀點有:①認為典型的繼續犯有非法拘禁罪、窩藏罪以及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遺棄罪、盜竊罪是典型的狀態犯。[12](183?184)②認為繼續犯常見的類型有侵犯自由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綁架罪,非法持有的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槍支罪,不作為犯如遺棄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但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脫逃罪不是繼續犯。[8](315)③認為非法拘禁罪、綁架罪、重婚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拐騙兒童罪屬于繼續犯。[26](73)④認為典型的繼續犯有非法拘禁罪、虐待罪、遺棄罪、重婚罪和持有型的犯罪。[15](388)⑤認為典型繼續犯有非法侵入住宅罪、虐待罪與非法拘禁罪。[27](136)⑥認為盜竊罪是典型的狀態犯,危險駕駛罪與非法拘禁罪是典型的繼續犯。[14](171)
筆者對上述主張評析如下:①重婚罪不應是繼續犯而是狀態犯。“雖然行為人持續性地利用自己所創設的重婚狀態,但是并不存在經常性重復的重婚性結婚。”[11](330)這是形式上的理由。實質理由是,由于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2年有期徒刑,若行為人維持重婚狀態超過5年以上,說明已經形成穩定性的婚姻關系,而婚姻的本質是感情的結合,“如果通過進行追訴或者執行刑罰來變更這種事實狀態,反而有損刑法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7](515)有違刑法設立時效制度的本旨。正因如此,域外刑法理論無可爭議地認為,重婚罪屬于狀態犯,而不是繼續犯。[27](15)②虐待罪是徐行犯而不是繼續犯。“繼續犯的行為必須持續地侵害某一直接客體。這種持續,必須是沒有間歇地持續。如果行為人經常以某種形式侵害某一直接客體或者把一個行為分解為許多細小的動作徐徐行之的,構成徐行犯,不構成繼續犯。如虐待罪以經常打罵、凍餓、有病不給醫治等行為逐漸地侵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19](145)③拐騙兒童罪應屬于狀態犯,而不是繼續犯。拐騙兒童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兒童的生命、身體的安全,而不是人身自由,若認為本罪的法益包括了兒童的人身自由,則意味著拐騙之后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不再另外構成非法拘禁罪。然而,拐騙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5年有期徒刑,而且沒有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作為繼續犯處理顯然不利于保護法益。而且,在他人拐騙之后參與撫養,沒有非法剝奪自由行為的,屬于降低法益風險的行為,若認為該罪是繼續犯,則必須認定為拐騙兒童罪的共犯,也顯然有悖常理。唯有認為該罪屬于狀態犯,拐騙之后非法剝奪自由的,以拐騙兒童罪與非法拘禁罪數罪并罰,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的,適用非法拘禁罪結果加重犯的規定,方能有效保護被拐騙兒童的人身自由。④綁架罪應屬于狀態犯,而不是繼續犯。對于日本刑法中規定的略取、誘拐罪,雖然理論通說認為是繼續犯,但判例認為以勒索贖金為目的誘拐后監禁被拐取者的,應當作為數罪并罰處理,說明判例采取狀態犯說。日本學者西田典之教授認為,“如果將被拐取者的身體安全置于重要地位,那么,將被拐取者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時,犯罪即告終了,此后是違法狀態的繼續,也可能認為本罪是狀態犯。刑法規定對事后的參與行為按收受(被拐取者)罪(第227條)獨立處罰,可以說是一種調和。”[28](75)山口厚教授也指出,“略取、誘拐罪達到既遂之后,再實施其他犯罪的,不將這二罪作為想象競合犯來處理,雖然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是將略取、誘拐罪作為狀態犯來處理,但是,首先,即便對被拐取者的實力支配可以繼續,但構成略取、誘拐行為的暴行、脅迫、欺騙、誘惑本身并未繼續;并且,另外還規定了收買、收受被略取、誘拐者的犯罪,因此,本書認為,將略取、誘拐犯罪理解為狀態犯要更為合理。”[29]在繼續犯說和狀態犯說之外,還有一種所謂二分說,認為“當被拐取者具有意識活動能力時,拐取行為侵害了其自由,因而本罪屬于繼續犯,但當被拐取者是沒有行動自由的嬰兒和高度的精神病患者時,則由于僅僅侵害了保護監督權,所以應為狀態犯。”[30](166)筆者認為,如果認為綁架罪屬于繼續犯,則意味著在他人綁架人質后,即便不知道他人具有綁架勒索的目的,只要事后參與看管人質的,也當然成立綁架罪的共犯,但這恐怕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由于綁架罪法定刑偏重,綁架后繼續非法剝奪人質人身自由的,無需再以非法拘禁罪進行評價,也就是說,綁架罪可以包容非法拘禁罪。只有認為綁架罪屬于狀態犯,在綁架既遂之后參與看管人質的,若不知悉他人具有勒索財物或者提出不法要求的目的,才能與綁架人在非法拘禁罪范圍內成立共犯,而不是成立綁架罪的共犯;若知悉他人的目的,則可以成立綁架罪的共犯(相當于利用事前狀態型綁架罪)。⑤不作為犯未必就是繼續犯。不作為犯分為真正不作為犯與不真正不作為犯。對于遺棄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拒不救援友鄰部隊罪以及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從產生作為義務之日起,在履行作為義務之前,通常可以持續性地肯定構成要件的成立。但對于故意殺人、放火這些不純正不作為犯而言,通常還是應該認為與作為方式實施時一樣屬于即成犯為妥。
[1] 張明楷. 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2] [日]高橋則夫, 以東研祐, 井田良, 杉田宗久. 刑法總論(第2版)[M]. 東京: 日本評論社, 2007.
[3] 林鈺雄. 新刑法總則[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4] [日]松原芳博. 繼續犯と狀態犯[C]. 刑法の爭點[M]. 東京:有斐閣, 2007.
[5] [日]大塚仁. 刑法概說(總論)(第四版)[M]. 東京: 有斐閣,2008.
[6] [日]井田良. 講義刑法學·總論[M]. 東京: 有斐閣, 2008.
[7] 張明楷. 刑法原理[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8] 阮齊林. 刑法學(第三版)[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9] [日]山中敬一. 刑法總論(第2版)[M]. 東京: 成文堂, 2008.
[10] [日]西田典之. 刑法總論(第二版)[M]. 東京: 弘文堂, 2010.
[11]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Ⅰ[M], 4.,Auflage, C. H. Beck München, 2006.
[12] 高銘暄, 馬克昌. 刑法學(第五版)[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3] 陳子平. 刑法總論(2008年增修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14] 張明楷. 刑法學(第四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15] 馮軍, 肖中華. 刑法總論(第二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16] [林東茂. 刑法綜覽(修訂五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17] [日]大谷實. 刑法講義總論(新版第3版)[M]. 東京: 成文堂,2009.
[18] 黃京平. 刑法學(第二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9] 王作富. 刑法(第五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0] 周光權. 刑法總論(第二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1] [日]山口厚. 刑法總論(第2版)[M]. 東京: 有斐閣, 2007.
[22] [韓]金日秀, 徐輔鶴. 韓國刑法總論[M]. 鄭軍男譯.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
[23] [日]淺田和茂. 刑法總論(補正版)[M]. 東京: 成文堂, 2007.
[24] [日]前田雅英. 刑法各論講義(第4版)[M].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07.
[25] 曲新久. 刑法學(第四版)[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26] 周光權. 刑法各論(第二版)[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7] 賈宇. 中國刑法(第2版)[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28] [德]約翰內斯·韋塞爾斯. 德國刑法總論[M]. 李昌珂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9] [日]西田典之. 刑法各論(第五版)[M]. 東京: 弘文堂, 2010.
[30] [日]山口厚. 刑法各論(第2版)[M]. 東京: 有斐閣, 2010.
Abstract:When defining a criminal pattern, the identifying of accomplice, quantity of crim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rting date of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are the main concern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scontinuing offense and state offense is of theoretical meaning, while differentiating discontinuing offense from state offense ha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en defining a criminal pattern,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 is still its normative consideration and examination. If a crime is of continued conformity of important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i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continuous crime; otherwise, it should be defined as discontinuing offense or state offense. Typical continuous crimes are as crime of false imprisonment, nonstandard criminal omission, crimes of unlawful possessing,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and crime of unlawfully intruding into the residence of another person. Crime of bigamy, crime of kidnapping,crime of buying abducted and trafficked, or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and crime of abducting children is state offenses, not continuous crimes.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s discontinuing offense, not continuous crim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atterns of crime of harboring a criminal and crimes related to booties or stolen good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specific criminal behaviors.
Key Words:discontinuing offense; state offense; continuous crime; legal interest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scontinuing Offense,State Offense and Continuous Crime
CHEN Hongbing
(School of Law,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D914
A
1672-3104(2012)03?0075?07
2012?02?22;
2012?03?16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陳洪兵(1970?),男,湖北荊門人,法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解釋學研究.
[編輯: 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