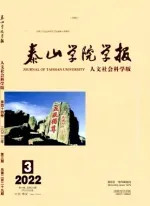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吃發球”一詞的意義及其形成機制
張延俊
(信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一、慣用語“吃發球”的意義
“吃發球”是近年來隨著體育比賽的廣播電視轉播而流行起來的一個詞語,使用頻率很高。該詞不只是用于口語,也常見于體育報道和體育著作。例如:
(1)第一局開始,塞弗連連吃發球,先以1∶4落后。(陳昭《“神拍”撼倒“大哥大”——男單丁松塞弗激戰紀實》,1995年5月12日《人民日報》)
(2)然而他被熊柯的臺內球控制得起不了板,又連吃發球。(劉小明《京城周末全民健身乒乓賽推出新內容,業余選手攻擂挑戰國手》,1995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
(3)在有遮擋發球的條件下,接發球一方由于看不清對方發球的旋轉變化而經常在比賽中直接“吃”發球。(吳敬平《乒乓球直板反膠打法訓練》,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頁)
可見,“吃發球”早已成為一個慣用語了。但這個詞語還未被《現代漢語詞典》收錄。它是什么意思?互聯網上有人如此作答:
就是你發球,對手沒有接住。
在你接上對方的發球后,對方沒能接上你的發球,這也可以說是吃發球。
所謂吃發球,就是您的對手發球,您沒有回過去(下網、出界、沒打中)。
就是接球的人沒接到球,讓對方直接發球得分了。
在接對方發球的過程中直接失誤,使對方依靠發球直接得分。
這些說法或者不正確,或者不準確。準確的解釋應該是“受制于對方發球(適用于乒乓球、排球和網球等比賽)”,或“遭受對方發球的制約(適用于乒乓球、排球和網球等比賽)”。
“吃發球”為什么應釋為“受制于對方發球(適用于乒乓球、排球和網球等比賽)”或“受到對方發球的制約(適用于乒乓球、排球和網球等比賽)”?這個意義的構成理據是什么?為什么其中會出現“受制”、“遭受”和“制約”這樣的意義成分?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吃”的意義為何會引申為“遭受”
首先探討“遭受”這個義素的來源。它來自“吃”字。江藍生認為“吃”有“遭受”義[1](P41-43),這是非常正確的。在“吃發球”中,關鍵成分“吃”的意義正是“遭受”。這個意義的形成經過了下面的過程:
(一)“吃”取代“食”
“吃飯”的“吃”是現代漢語中的一個基本詞匯,義為“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經過咀嚼咽下去”,繁體寫法為“喫”。根據目前所見文獻資料,這個意義的“吃”出現于漢代。例如:
(4)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賈誼《新書》第7卷)
(5)串數唐得,自用賑給,不畏防禁,飲食無極,吃酒嗜美。(后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凈平等覺經》第4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里也有少量用例,如:
(6)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
到唐代,“吃”字開始大量使用,僅在問世于初唐時期筆記小說《朝野僉載》中就可以見到數例。如:
(7)張公吃酒李公醉。(唐·張鷟《朝野僉載》卷1)
(8)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飽即鳴杖以驅之還。(同上卷4)
(9)老賊吃虎膽來,敢偷我物!(同上卷6)
(10)其肉乞緬吃卻。(乞:給。緬:人名。同上卷6)
到唐末五代時期,“吃”字終于取代了“食”字在口語中的地位。在《祖堂集》中,“食”只出現30余次,而“吃”則出現約130次。“吃”的“遭受”義就是在其“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經過咀嚼咽下去”義的基礎上形成的。
(二)修辭拈連與語法類推成就了“吃杖”這種異常的組合
沈家煊說:“為什么有的實詞經常虛化,有的實詞幾乎從不虛化?……這方面我們也知道很少。”[2](P13)的確,盡管一般虛詞都來自實詞,但是并非所有的實詞都會發生虛化。“吃”字是一個強性動作動詞,為什么會由主動的“把食品和飲料等放到嘴里咀嚼下咽”義變為被動的“遭受”義?它最初的虛化(或稱語法化)是如何引發的?
“吃”的意義之所以會從“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經過咀嚼咽下去”演變為“遭受”義,首先是因為當時的漢語中出現了“吃杖”這種異常的組合。在人類語言的句子中,成分與成分之間的搭配都不是隨意的,而是有一定語義選擇限制的。對于謂語動詞“吃”來說,它的施事者只能是人類或者動物,它的受事者只能是可供咀嚼、下咽的食品和飲料。然而在下面幾例中,“吃”的受事者卻是另外一種東西:
(11)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唐·張鷟《朝野僉載》卷5)
(12)于后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乞(吃)杖處。(同上卷6)
(13)但知免更吃杖,與他邪靡一束。(敦煌變文《燕子賦》)
(14)汝且為復怨恨阿誰,解事速說情由,不說眼看吃杖。(敦煌變文《盧山遠公話》)
在這些例子中,“吃”的受事成分是“杖”。“杖”就是“棍棒”。雖然從詞性上看,“杖”字可視為一個名詞,充任“吃”的賓語,但從詞義上看,“杖”不僅不可以“吃”,而且還會主動地對“吃”的原施事者進行傷害,可見這不是一種符合常規的搭配。
既然“杖”等不是可吃之物,那么為何會出現“吃杖”這樣的異常組合呢?筆者認為,其中有粘連和類化的因素存在。“拈連”是指當甲乙兩類事物連在一起敘述時,把本來適用于甲事物的詞語趁勢連用到乙事物上。比如某人本想得到一頓飯吃,結果卻被打了一頓杖,于是自嘲道“飯沒吃上,吃了一頓杖”,把適用于“飯”的“吃”字順勢用到了“杖”上。說它與語言的類化有關,是因為這個拈連與一般的拈連不同。一般的拈連,所關涉到的兩個事物之間,在語言上可以沒有任何聯系。而“杖”和“飯”不同,它們之間卻有一定的語法聯系,即它們都可以與量詞“頓”相結合。
“頓”作為量詞,最早用于“飯食”,表示正式飯食的次數,區別于“零食”的次數。“頓”作為表示“飯食”單位的量詞在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中已經出現,以后一直使用。例如:
(15)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
(16)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唐·張鷟《朝野僉載》第1卷)
(17)日常三頓飯,年恒兩覆衣。(唐·王梵志《任意隨流俗詩》)
除修飾飯食外,“頓”字也可以修飾其他事物(如《齊民要術》第8卷“然后凈淘米,炊為再餾,攤令冷,細擘麴破,勿令有塊子,一頓下釀,更不重投”),其中較為常見的是用于“杖刑”,實施一次“杖”的刑罰就叫“一頓杖”,而不管這次刑罰包括多少個具體的施杖動作(一般以量詞“下”為單位)。例如:
(18)有敕與一頓杖。(唐·張鷟《朝野僉載》卷3)
(19)門家告御史……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同上卷6)
可見,“飯”和“杖”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能與量詞“頓”結合,既可以說“一頓飯”,也可以說“一頓杖”,而正是這個共同點促成了“飯”對“杖”的類化,形成了“吃杖”這個組合。
(三)“杖”的動名詞二重性最終觸發了“吃”的意義引申
語義異常的組合只是“吃”字意義演變的基礎,本身還不能造成“吃”字意義的改變。“吃”字“遭受”義形成的關鍵因素在于,“吃”的賓語“杖”具有動詞和名詞二重性,也就是既可以用作名詞,又可以用作動詞。“遭受”義動詞與一般及物動詞的不同之處是,它的賓語中必有一個中心動詞,這個動詞在語義上對“遭受”義動詞的主語事物給以支配。如“我軍陣地遭受敵軍火力猛攻”,句子賓語中的“猛攻”就是這樣的動詞。也就是說,當“吃”的賓語是一個純粹的名詞時,“吃”的意義不會發生變化,仍然為“咀嚼下咽”,如果“吃”的賓語中含有支配主語事物的動詞,“吃”的意義就會轉變為“遭受”。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表格來表示:

本身語義 所帶賓語的特征吃(喫)咀嚼下咽 中心語為名詞遭受 中心語為可以支配主語事物的動作動詞
本身語義所帶賓語的特征吃(喫)咀嚼下咽中心語為名詞遭受中心語為可以支配主語事物的動作動詞。就“吃杖”來說,當我們聽到或者看到這個組合時,之所以會將其理解為“遭受棍棒擊打”,而不是“咀嚼下咽棍棒”,原因就是“杖”還具有動詞的用法。在漢語中,“杖”用作動詞的例子是很多的。如:
(20)惲大怒,乃呼州官棰以甲間構,將杖之。(唐·張鷟《朝野僉載》卷3)
(21)杰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同上卷5)
下面句子中的“杖”字也是如此:
(22)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
(23)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唐·張鷟《朝野僉載》第3卷)
(24)明朝早起過案,必是更著一頓。杖十已上關天,去死不過半寸。(《燕子賦》)
“吃杖”和“吃李日知杖”中的“杖”全是動詞,故其“吃”的意義全是“遭受”。在下面兩例中,“吃”字明顯已經演變為典型的“遭受”義動詞:
(25)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吃一跌,氣才一暴,則其心志便動了。(宋·《朱熹朱子語類》第52卷)
(26)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唬,因此不敢取來。(百回本《水滸傳》第42回)
三、“遭受”義動詞“吃”所帶賓語中心動詞的省略
“吃”的“遭受”義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賓語中心語必須是一個動詞。在“吃杖”中,如果“杖”不是一個動詞,那么“吃”的意義也就不可能變為“遭受”。然而在具體的言語實例中,我們卻常常會遇到“遭受”義動詞“吃”的賓語中只有名詞而沒有動詞的情況。如:
(27)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碾玉觀音》)
(28)口口聲聲叫我寶寶,要疼我要愛我,現在竟然說要打我,要給我吃巴掌。(現代漢語)
例中“吃”均為“遭受”義,而其所帶賓語“官司”(義為“訴訟”)、“巴掌”均為名詞。這是什么原因呢?
原來,“吃官司”和“吃巴掌”中都隱含掉了一個重要的動詞。“吃官司”本來應該是“吃官司懲處”,即帶有能夠支配“吃”的主語事物的動詞“懲處”。“吃巴掌”本來應該是“吃巴掌擊打”,即帶有能夠支配“吃”的主語事物的動詞“擊打”。而由于語言經濟性等方面的原因,說話者或寫作者并未將這個“懲處”和“擊打”明確表達出來。盡管“懲處”和“擊打”被省略或稱為隱含了,但是它們的意義還是不會消失的。這正是我們把“吃官司”和“吃巴掌”分別理解為“遭受官司懲處”和“遭受巴掌擊打”的原因所在。這種現象不只是表現在“吃××”短語中。如“很阿Q”,其中就省略了一個動詞“像”,“像”字雖被省略,但是其意義還是存在的,它被隱含在整個短語的結構之中。
在“吃發球”中,同樣內含一個重要動詞,這個動詞就是“制約”。“發球”雖是一個動詞性成分,但是在“吃”的賓語中它不是一個中心成分,它的身份與上文提到的“官司”和“巴掌”一樣,“制約”才是其中的中心成分。“制約”被隱含了,其意義卻仍然存在,這就是我們把“吃發球”理解為“遭受(對方)發球制約”,或者理解為“受制于(對方)發球”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吃”引申為“遭受”,起因于一個比較偶然的因素,即修辭上的粘連和語法上的類化,它導致了“吃杖”這種異常組合的出現。“杖”兼具名詞和動詞兩種性質,當它被視為動詞時,“吃杖”的語法結構就會發生轉化,“吃”的性質和意義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使之由一個強性動作動詞演變為一個弱性動作動詞,由“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經過咀嚼咽下去”義演變為“遭受”義。“吃發球”是“吃發球制約”的省略,“制約”雖未在字面上出現,但其意義仍被保留在整個短語之中。“吃發球”一詞的形成告訴我們,粘連和類化有時會造成句子成分之間語義關系的變化,詞類的不確定性會造成句法關系的變化,句法關系的變化可能會觸發詞義的引申,被省略或隱含詞語的意義會在句子中“陰魂不散”。
[1]江藍生.被動關系詞“吃”的來源初探[A].江藍生.近代漢語探源[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綜觀[A].吳福祥.漢語語法化研究[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