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光利一與機(jī)械時(shí)代
江玉嬌,奚皓暉
(浙江師范大學(xué)外國(guó)語學(xué)院,浙江金華321004)
一、《機(jī)械》的接受性
伊藤整曾在《新興藝術(shù)派和新心理主義文學(xué)》描述過短篇小說《機(jī)械》帶給他的沖擊:橫光利一在昭和五年(1930)突然發(fā)生了變化,我指的是在《改造》九月號(hào)登載的《機(jī)械》。恰逢與《尤利西斯》的譯本同時(shí)出現(xiàn),這明顯是來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響。我一邊步行在牛込區(qū)(現(xiàn)東京都新宿區(qū))的電車道上,一邊在剛買的雜志上讀到《機(jī)械》的時(shí)候,強(qiáng)烈的印象使我呼吸停頓。[1]518-519
上述有關(guān)伊藤氏“突變說”立論的直接來源,是指他在《新心理主義文學(xué)》(昭和七年)中對(duì)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發(fā)現(xiàn)。受到意識(shí)流小說的強(qiáng)烈刺激之后,它被視為昭和文學(xué)心理分析轉(zhuǎn)向的重要理論依據(jù):“那是一種與外在現(xiàn)實(shí)相對(duì)立的精神內(nèi)部的現(xiàn)實(shí)……,喬伊斯作為方法采用的意識(shí)流絕不僅限于表面的隱晦和眩奇,而從側(cè)面發(fā)現(xiàn)了重大的現(xiàn)實(shí)而將其置于絕對(duì)的位置……,在表現(xiàn)的同時(shí)明確地獲得了二元甚至多元的同時(shí)性。”[2]305-306
受到這種觀點(diǎn)的左右,長(zhǎng)期以來,以《機(jī)械》為分界,傳統(tǒng)的意見一致地把它當(dāng)作橫光利一從新感覺派到新心理主義轉(zhuǎn)型的標(biāo)志。“每個(gè)人都可以從這部作品看到新的嘗試,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作品的手法是嶄新的,完全嶄新的手法,同樣的例子在日本絕無僅有,在外國(guó)也絕無僅有”。[3]78小林秀雄指出其具有“古典的重量”,揭示了“人類的純粹和社會(huì)的約束之間的對(duì)決”。井上良雄則認(rèn)為:敘述者“私”作為“理論本身”,充當(dāng)了“謀劃不幸的敘事詩(shī)人”。從小說發(fā)表時(shí)的外部狀況看,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huì)正處于都市化轉(zhuǎn)型過程之中,工業(yè)化基本宣告完成,就業(yè)機(jī)會(huì)的增加伴隨著勞動(dòng)力的輸入。有資料顯示:東京人口的增長(zhǎng)率從大正六年(1917)開始,呈現(xiàn)出幾何級(jí)的趨勢(shì)(與過去1%的增長(zhǎng)率相比,在這一年達(dá)到了14~15%左右)。到昭和五年(1930)為止,東京人口已突破540萬。小說的主人公“私”離開“九州造船廠”進(jìn)入東京成為嶄新勞動(dòng)力的同時(shí),恰好是上述變化的反映。與之相對(duì)的是:貧富兩極分化的現(xiàn)象日趨明顯,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微觀意識(shí)中惶恐不安的情緒進(jìn)一步沉淀。橫光利一在這篇“轉(zhuǎn)型之作”中,不失時(shí)機(jī)地顯示出一位“外向型”小說家對(duì)上述社會(huì)局勢(shì)的敏銳感受。綜合以上兩點(diǎn)可以看出,《機(jī)械》在當(dāng)時(shí)受到文壇關(guān)注并非偶然,作為昭和初期的代表作之一也屬實(shí)至名歸。然而,與前期的一片激賞聲音相對(duì),戰(zhàn)后的評(píng)價(jià)逐漸呈現(xiàn)出分化的趨勢(shì)。進(jìn)入70年代,關(guān)于《機(jī)械》的微觀研究逐步成為日本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一方面意識(shí)到以往對(duì)《機(jī)械》的評(píng)價(jià)稍顯過高,忽視了小說原本存在的符號(hào)化缺點(diǎn)。另一方面卻認(rèn)為小說別具一格的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中存在著超越當(dāng)下歷史語境的現(xiàn)代人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危機(jī)。這兩種對(duì)立的評(píng)價(jià)成為了隨后《機(jī)械》研究聚訟的焦點(diǎn)。就橫光利一而言,以獨(dú)特的觀念結(jié)構(gòu)開掘“自我意識(shí)”背后的危機(jī),是他執(zhí)著探求的主題。這在他1935年發(fā)表的《純粹小說論》中得到集大成的體現(xiàn)。其中,尤其是在全知視角(第三人稱客觀視角)導(dǎo)演下使小說敘述者第一人稱化的第四人稱敘述策略,可以說是受到了上述寫作背景的觸動(dòng)。而借助這種理論,不失為理解《機(jī)械》的一把鑰匙,事實(shí)上也為橫光利一的小說創(chuàng)作論提供了一個(gè)可以闡釋的范例。
二、雙重視角的闡釋
以上,從小說《機(jī)械》的接受性分析入手,分別論述了伊藤整對(duì)西方意識(shí)流小說的引入及其后續(xù)評(píng)價(jià)。我認(rèn)為,方法論的嘗試在作家“轉(zhuǎn)型”的諸因素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這一嘗試的體現(xiàn),首先是在敘述模式上對(duì)私小說的“凝固的第一人稱”進(jìn)行改造。昭和三十七年,中村真一郎在他的《純粹小說論再讀》中,點(diǎn)出橫光利一小說方法論的關(guān)鍵“恐怕要數(shù)第四人稱的設(shè)置”。即在“全知視角下使小說敘述者第一人稱化”的方法。試圖貫通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者使之合二為一的策略。然而,這一看似新鮮的小說理念,與其把它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規(guī)范展開實(shí)踐,還不如說是為了直面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不景氣而作的有感而發(fā)。不過,這一嘗試的性質(zhì)稱得上是超越了以往新感覺主義單純停留于技巧表面的創(chuàng)新,而具備了更加值得注目的緣故。在小說方法論的背后,體現(xiàn)的是橫光對(duì)于現(xiàn)代性的反思,這才是《純粹小說論》真正值得注目的關(guān)鍵所在。為什么這么說呢?證據(jù)之一,是川端康成早在它發(fā)表的當(dāng)年,即《〈純粹小說論〉的反響》(1935)這篇論文當(dāng)中,較早地對(duì)問題的性質(zhì)給出判定,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純粹小說的要旨在于如何把握、處理自我意識(shí)這種不安的精神。離開相關(guān)于此的實(shí)踐論,便無法批判橫光氏的純粹小說論,亦無權(quán)批評(píng)橫光的近作”。[4]14
不過,在大多數(shù)小說家看來,這種理論幾乎從未產(chǎn)生效用。問題在于,實(shí)現(xiàn)這一設(shè)計(jì)在技術(shù)上存在諸多困難之處。首先它需要一個(gè)“功能完善”的敘述者,并且是一顆同時(shí)具備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心靈。確定了這一前提,把焦點(diǎn)聚集到這兩種光線之上,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全知和限知的并置。在已有此類敘述者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在情節(jié)展開的過程中,“加上每人各自的自我意識(shí)(關(guān)注自我的自我)作一并考慮”。[5]這樣一來,“被觀察的個(gè)體的視點(diǎn)(自我意識(shí))”就呈現(xiàn)出不斷更新的狀態(tài)。我以為,從讀者接受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對(duì)意識(shí)狀態(tài)發(fā)生變化的“私”的敘述存在以下三種可能。(1)自我意識(shí)發(fā)生變化的“私”完全沒有喚起對(duì)自我的不信任感,始終維持同一不變的自我;(2)自我意識(shí)發(fā)生變化的“私”盡管在敘述中主動(dòng)袒露自我變化的意識(shí),但是堅(jiān)持維持同一的自我;(3)自我意識(shí)發(fā)生變化的“私”在敘述中主動(dòng)袒露自我變化的意識(shí),但是在敘述中積極地煽動(dòng)著對(duì)自我的懷疑。
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這一設(shè)計(jì)顯而易見是為橫光利—特定的小說主題服務(wù)的,超出了這一界限,就再無所謂的“雙重視角”小說。事實(shí)上,前面所列出的(3)最為切近橫光利一的小說模式,留到下文中詳細(xì)考察。先考慮上述的另一方面,即社會(huì)性的視角。這一向度主要呈現(xiàn)的不僅是個(gè)體意識(shí),還有與之相伴的“人際關(guān)系”分化和重組。由于關(guān)系世界的錯(cuò)綜復(fù)雜,個(gè)體與群體的關(guān)系不斷改變,意識(shí)世界的交鋒和對(duì)話使“被著重表現(xiàn)的人物A的意識(shí)仿佛正在轉(zhuǎn)變成人物B的意識(shí)”。因而,第一人稱不再由單數(shù)出現(xiàn)而呈復(fù)數(shù)狀態(tài)。個(gè)體的意識(shí)既超出原有的經(jīng)驗(yàn)區(qū)域,同時(shí)也模糊了過去自我的界限。換言之,個(gè)體的意識(shí)不再屬于個(gè)體本身,而作為“多數(shù)第一人稱的并列”而存在。以下,筆者將分別論述這兩種敘述聲音在《機(jī)械》中的表現(xiàn),并通過二者的對(duì)比和交匯,以此為基點(diǎn)窺入橫光利一文學(xué)精神內(nèi)核之所在。
三、《機(jī)械》中第一人稱視角的實(shí)踐
《機(jī)械》的開頭,“私”的聲音是以游離于自我之外的方式出現(xiàn)的:“起先我時(shí)常認(rèn)為我的老板很有可能是個(gè)瘋子”。[6]295
盡管站在第一人稱的視角上講述,但是評(píng)價(jià)的對(duì)象卻指向第三人稱的老板。“私”一方面處于情節(jié)之內(nèi),但又試圖以跳出故事進(jìn)程之外的角度展開對(duì)過去的回?cái)ⅰW晕覍?duì)象化的傾向使“私”同時(shí)呈現(xiàn)出觀察者和敘述者的雙重身份。有關(guān)“私”的來歷和動(dòng)機(jī)出現(xiàn)在接下來的一個(gè)段落中:“其實(shí)我原本是從九州造船廠出來的。只是在中途的火車上和一個(gè)婦女偶然相遇便成為我這段生活的開始”。[6]295
隨著回?cái)⒌倪M(jìn)一步導(dǎo)入,“私”的意識(shí)開始向“主人”的接近,一種象征性的動(dòng)作成為“私”新的自我意識(shí)的起點(diǎn):“有一天我正在工地干活老板娘來了。因?yàn)槔习逡ベ?gòu)買金屬材料所以吩咐我跟著同去并且一定要由我拿著老板的錢。這是由于假如是老板拿著錢的話就幾乎一定會(huì)在途中弄丟因此老板娘出于小心決不能把錢交給老板這是第一要緊的事情。到現(xiàn)在為此這個(gè)家庭的悲劇大部分實(shí)際上都是因?yàn)閮舫鲞@種蠢事但是盡管如此為什么老板會(huì)這樣一再地丟錢誰也不知道。到底是我們不能想像這個(gè)拿了錢就丟的四十歲男人究竟是何許人也”。[6]298
然而隨后,這種迷惑不解就變成了反常的崇拜:“總之主人是變了,把錢不當(dāng)錢諸如此類的話是用來形容富人的。可是像老板這種窮得像癟三一樣拿著五分錢的鎳幣去鉆公共澡堂的簾子的人花掉了原本要買自家的金屬材料的錢而渾然不知這可就教人頭疼了。能做出這種事情來的恐怕只有過去的仙人了。不過,和仙人在一起的人是絕對(duì)不必有所顧忌的”。[6]298
金錢是將可變資本(“私”為代表的廉價(jià)勞動(dòng)力)轉(zhuǎn)化為商業(yè)利潤(rùn)的必要前提,日本式經(jīng)營(yíng)的一大優(yōu)點(diǎn)在于它把純粹的雇傭關(guān)系與其特有的共同體(會(huì)社)生產(chǎn)有效組合,使利潤(rùn)最大化的一種經(jīng)營(yíng)模式。而使“私”對(duì)老板產(chǎn)生興趣的誘因卻是由于老板“丟錢”的反常行為。正因?yàn)槔习暹@種無法理解的錯(cuò)誤所暴露出來的愚蠢,使“私”加倍感到智力上的優(yōu)越。進(jìn)而在這一點(diǎn)上“戰(zhàn)勝”老板:“我不禁把老板想成至多只是個(gè)五歲的男孩卻以四十歲的面目出現(xiàn)在我面前”。[6]299
這樣一來,就起到了淡化原本雇傭關(guān)系的作用。因此,對(duì)“私”來說,這一發(fā)現(xiàn),稱得上是一種意外的解放。然而,這個(gè)情節(jié)動(dòng)作本身卻暗示出另一種反諷的意味:在“私”的意識(shí)進(jìn)一步發(fā)展中,卻把老板違背常理的“神經(jīng)錯(cuò)亂”看作一種“仙人”風(fēng)范的非凡之舉。此刻,人的無知和愚蠢在“私”的理解當(dāng)中以一種悖逆的方式獲得了提升,“私”不由自主地對(duì)老板產(chǎn)生了直覺上的親近。
“有一天,老板突然把我叫到暗室。一邊用涂了苯胺染料的銅板放在酒精爐上加熱一邊對(duì)我說要使金屬板顏色變化最需要注意的是加熱時(shí)顏色的變化。現(xiàn)在這塊金屬板是紫色但是漸漸就要變成黑褐色不久就要變成黑色,變成黑色后就不會(huì)和三氯化鐵發(fā)生化學(xué)作用。因此他教我著色時(shí)一定要掌握顏色變化中段時(shí)火候的控制并要我當(dāng)場(chǎng)使用盡可能多的試劑進(jìn)行燃燒試驗(yàn)。從此我對(duì)試驗(yàn)化合物和元素之間的有機(jī)關(guān)系越來越感興趣。因?yàn)榕d趣越大越能領(lǐng)會(huì)過去不知道的無機(jī)物內(nèi)部實(shí)際包含著微妙的有機(jī)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鍵。現(xiàn)在我注意到任何小事情上都有機(jī)械那樣的法則成為系數(shù)計(jì)算著實(shí)體這成為我心靈覺醒的第一步。”6[301]
由于老板的信任,我不僅獲準(zhǔn)進(jìn)入“暗室”,而且還獲得了和主人一起研究赤色銅板的“特許權(quán)”;我對(duì)老板進(jìn)一步產(chǎn)生了“仰慕之情”。“也就是說我像體會(huì)暗示的信徒那樣被老板的身體放射出的光芒射穿……從此以后我像輕部那樣死心塌地?zé)o論如何萬事都以老板為第一”。[6]302此刻,包含《機(jī)械》象征性命題的隱喻突顯出來。有關(guān)“化學(xué)反應(yīng)”的悖論性情節(jié)既作為“私”意識(shí)“重建”的關(guān)鍵,同時(shí)也是“私”的意識(shí)遭受“腐蝕”的隱喻。“無機(jī)物”作為喻體,即原本被忽視且難以把握的“人際關(guān)系”本身。正是通過意識(shí)到它的存在,“私”才得以閱讀對(duì)應(yīng)著喻本的“人情世故”。化合物和基本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則成為連接喻體和喻本兩者之間的“催化劑”。“私”對(duì)機(jī)械運(yùn)動(dòng)法則的發(fā)現(xiàn):“無機(jī)物內(nèi)部包含著微妙的有機(jī)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鍵”,指的就是人際關(guān)系中把握人類心理的關(guān)鍵秘訣,它已經(jīng)被這個(gè)隱喻間接地透露出來了。但意識(shí)到這一秘訣的同時(shí),自我發(fā)現(xiàn)的悖論也由此浮現(xiàn):心靈覺醒的同時(shí)也意味著個(gè)體的意識(shí)消融在化學(xué)方程之中;性格的各個(gè)組成部分在等式中被隨機(jī)組合,依照相對(duì)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化學(xué)反應(yīng)。這似乎暗示著“人際關(guān)系”雖然可以通過自我預(yù)先設(shè)定的精確計(jì)算來推定,但人的自我卻在這種計(jì)算中漸漸隱覓于無形了。至此,人性的奧秘不再漂浮于空氣之中,而成為可以被測(cè)算的儀器。接下來的情節(jié)“私”進(jìn)一步陷入這種化學(xué)公式般的計(jì)算中無法自拔,在對(duì)他人意圖的揣測(cè)中揣測(cè)自我,最后在自我分裂的虛空中耗盡了自我。
因果關(guān)系作為“化學(xué)反應(yīng)”的基本邏輯,在《機(jī)械》中成為小說中人物相互“懷疑的循環(huán)”。它不僅成功主宰了人物之間的基本關(guān)系,而且成了推進(jìn)情節(jié)的基本關(guān)系。在情節(jié)展開的過程中,主客關(guān)系的“逆轉(zhuǎn)”開始出現(xiàn):隨著機(jī)械性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人性的主導(dǎo)和控制,包括“私”在內(nèi)的人格結(jié)構(gòu)開始從穩(wěn)定態(tài)向亞穩(wěn)定態(tài)推移;非主體的主體性進(jìn)而占據(jù)了人類自我意識(shí)的核心。而自我意識(shí)的主體性則伴隨意識(shí)感受機(jī)制的“自動(dòng)化”過程同步消解。在激起輕部“暴力傾向”的誘因當(dāng)中,認(rèn)為“私”取得老板的信任和“私”企圖竊取老板的秘密之間存在著因果關(guān)系。而按幾乎同樣的邏輯,“私”把輕部對(duì)“私”的懷疑,轉(zhuǎn)化為對(duì)輕部同樣的懷疑。隨著臨時(shí)雇傭的幫手屋敷的加入,這種懷疑在三人之中循環(huán)往復(fù)。輕部對(duì)屋敷的主動(dòng)接近成為阻止“私”進(jìn)一步接近老板“秘密”的手段。而“私”盡管努力否認(rèn)竊取老板“秘密”動(dòng)機(jī)的存在,但是在隱約的無意識(shí)中也試圖拉攏屋敷以便阻止輕部的下一步行動(dòng)。直到小說結(jié)局屋敷的死亡才宣告了這種無休止懷疑的終結(jié),但“私”卻因此滑入了自我懷疑的深淵。從因果關(guān)系的推論出發(fā),擁有毒死屋敷動(dòng)機(jī)的人表面上只有輕部,因?yàn)槲莘笤谝估餄撊肜习迮P室的曖昧行徑激起了輕部的懷疑。莫非老板的秘密已經(jīng)被此人覺察到了?所以,他在這一問題上憎恨屋敷甚至殺人滅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受到同一因果率的支配,“私”自己也無法成功排除無意識(shí)下“毒死”屋敷的可能性,因?yàn)槲莘蟠竽懙摹皾撊胄袆?dòng)”同樣使“私”感到難以容忍,它涉及到“私”與老板共同研究的“秘密”方程式是不是會(huì)因此暴露的問題。就這樣,圍繞老板的“秘密”方程式,人物的意識(shí)均不由自主地受到牽引。在這種無窮無盡因果關(guān)系的循環(huán)中,“私”的意識(shí)在人物A(輕部)和人物B(屋敷)之間來回穿梭,最后在相對(duì)關(guān)系的旋渦中歸于虛空。
四、《機(jī)械》中第三人稱視角的實(shí)踐
盡管終其一生都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經(jīng)歷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探索,但在橫光利一的小說模式中,自始至終都存在一種內(nèi)在的連貫性。這里所謂的連貫性,如果從具體的方法著眼,從大正十三年《文藝時(shí)代》創(chuàng)刊號(hào)登載的《頭與腹》到昭和二年《改造》連載的《機(jī)械》,其繼承關(guān)系并不難發(fā)現(xiàn)。通常以自然—社會(huì)的二元對(duì)立延伸出相互的作用力,隨著結(jié)尾主客關(guān)系的“逆轉(zhuǎn)”使人警醒。以下是在過去被反復(fù)援引《頭與腹》的開頭描寫。
正午。特別快速列車滿載乘客全速奔馳。沿線的小站像石頭一樣被拋向身后。[6]233
由機(jī)械文明推動(dòng)的加速度以一種超然外物的方式凌駕于蕓蕓眾生之上。橫光利一在最初的嘗試中,重點(diǎn)突出了新感覺派強(qiáng)調(diào)的感官印象,相反卻凸顯出對(duì)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的漠視。除“特別快速列車”以外,其余的人物僅以模糊的影像出現(xiàn),成為“團(tuán)塊狀”描寫中的凌亂碎片。相反,非人的、原本只作為背景出現(xiàn)的“特別快速列車”憑借現(xiàn)代化賦予的高速度,儼然已成為主導(dǎo)人類日常生活的“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但是,它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標(biāo)志性“成果”,除了引起象征的符號(hào)化以外,左右人類思維和行動(dòng)的力量畢竟有限;即便是因?yàn)槿剂喜蛔愣V共磺埃祟惾匀豢梢詰{借自己的意志有所選擇。但在小說《機(jī)械》中,這種看不見的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者不僅超然于客觀背景之上,而且成為一種無孔不入的活生生力量傳入內(nèi)心。這在小說的破題處就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了。
這個(gè)金屬板制造廠里必須要接觸化學(xué)試劑的工作中只有我的工作,這里充斥著特別多的劇毒化學(xué)品好像是特意引誘沒用的人掉進(jìn)去而挖的陷阱。一旦掉進(jìn)這個(gè)陷阱能夠腐蝕金屬的氯化鐵會(huì)將人的衣服和皮膚逐漸侵蝕殆盡因?yàn)槌羲氐拇碳?huì)破壞人的喉嚨不僅夜里無法入睡大腦的組織也會(huì)發(fā)生變異甚至連視力也會(huì)下降。這樣危險(xiǎn)的陷阱有本事的人是決無掉下去的可能的。我的老板也是在年輕的時(shí)候?qū)W會(huì)了別人不可能干的行當(dāng)所以一定是和我一樣沒用的人。[6]301
在這里,有關(guān)“腐蝕”的主題首次出現(xiàn)。“氯化鐵(FeCl3)”的意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diǎn)。它對(duì)人的肌體由外到內(nèi)產(chǎn)生無孔不入的腐蝕,甚至連“大腦的組織也會(huì)發(fā)生變異”。此時(shí),個(gè)體的神經(jīng)中樞喪失了正常活動(dòng)能力,而向非正常過渡的狀態(tài)恰好是“nameplate制造所”內(nèi)所有人物的共同癥狀。其中,老板“丟錢”的反常行為典型地暗示出意識(shí)中某種重要邏輯聯(lián)系的中斷隨之產(chǎn)生的“癥狀”。受到老板的影響,這種邏輯中斷的癥狀接下來從輕部—“私”—屋敷依次傳染。不僅如此,“腐蝕”的力量還繼續(xù)從意識(shí)外—意識(shí)內(nèi)深入;在意識(shí)與意識(shí)的交叉感染中,小說中的人物均陷入“相對(duì)關(guān)系”之中;圍繞老板的“秘密”,即與化合物相關(guān)的“方程式”帶來的因果循環(huán)論中各自懷疑對(duì)方因而難以自拔。篇末,屋敷的死亡意味著“腐蝕”最終從意識(shí)內(nèi)——無意識(shí)達(dá)成,也即腐蝕主題最后階段。死因是由于喝下了滲有重鉻酸銨((NH4)2Cr2O7)的水。在這里,重鉻酸銨作為“氯化鐵”的另一個(gè)補(bǔ)充意象,已不再單純意味著《機(jī)械》中“腐蝕”主題的同義反復(fù);同時(shí)還象征著受腐蝕的動(dòng)機(jī)從“意識(shí)模擬”向“操作實(shí)踐”(實(shí)際殺人)的完成。“如果說是平時(shí)的想法在喝醉后無意識(shí)地起了作用,而促使輕部讓屋敷喝下重鉻酸銨的話,那么,根據(jù)同樣的理由,讓屋敷喝下那玩意兒的,也許就是我”。[6]301在“私”的無意識(shí)動(dòng)機(jī)中,“正在研究的關(guān)于鉍(Bi)和硅酸鋯(Zr(SiO4))的方程式”是引起不安的動(dòng)因。它與氯化鐵以及重鉻酸銨在內(nèi)的其他化合物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了“私”意識(shí)中賴以感受的“方程式”。而處于各種化學(xué)反應(yīng)中的“無機(jī)物內(nèi)部包含微妙的有機(jī)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鍵”,正是通過無數(shù)個(gè)“方程式”的擴(kuò)展和延伸,最終指向小說“腐蝕”的源頭。作者借屋敷之口暗示出:“你得先到方圓一里內(nèi)草木全枯死了的氯化鐵工廠去看一遭,萬事都要從此開始”。

圖1 《機(jī)械》結(jié)構(gòu)示意圖
《機(jī)械》中的人物關(guān)系如圖1所示,“Nameplate制造所”在這里其實(shí)已經(jīng)取代了個(gè)體的價(jià)值觀和行為基準(zhǔn)。作為利潤(rùn)產(chǎn)生的源頭,直接作用于老板的意識(shí),繼而通過老板與雇工的“相對(duì)關(guān)系”,進(jìn)一步成為吸引包括“私”在內(nèi)人物意識(shí)的“磁場(chǎng)”。之所以稱之為“磁場(chǎng)”,是因?yàn)樗摹案g”作用對(duì)周圍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盡管表面上處于“私”敘述之外但又同時(shí)存在于小說中所有人物的意識(shí)之中,并最終成為主宰小說情節(jié)的“中心”。與情節(jié)或是人物關(guān)系的中心不同,這個(gè)“中心”內(nèi)部不存在任何實(shí)體,而是完全寄生于“人際關(guān)系”互為因果的旋渦之中,產(chǎn)生無形的破壞力。而正因?yàn)闊o形,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凌駕于“私”和其他人物之上無言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借助這種視角,橫光利一對(duì)近代標(biāo)志性成果之一的“都市化”進(jìn)行了反諷式的觀照,從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世界中抽象出“現(xiàn)代人的不安定性”。
五、《機(jī)械》中第四人稱的位置
綜上所述,小說《機(jī)械》以“私”的自我意識(shí)為中心的第一人稱敘述揭示了自我在現(xiàn)實(shí)世界被相對(duì)化的過程,最后喪失自我的悲劇命運(yùn)。而以“Nameplate制造所”為第三人稱的敘述者則進(jìn)一步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文明繁榮背后無所不在的“腐蝕”源頭。現(xiàn)在,我們嘗試把這兩個(gè)部分結(jié)合到一起,以便考察兩種敘述方式的重疊現(xiàn)象,以及最后訴諸的效果。
和大多數(shù)維持開放性結(jié)局的小說一樣,橫光利一在面對(duì)“誰是真兇”的疑問上選擇了沉默。而以自我意識(shí)分裂的“私”在喃喃自語中結(jié)束:“到底我來這里做了什么即便問我我也是不可能知道的”。短短的一句話中竟出現(xiàn)了三個(gè)“我”,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我”?連“我”自己都無法辨別。當(dāng)意識(shí)已經(jīng)衰退到不能把握存在的境地時(shí),就意味著分裂已經(jīng)超出了自我理解本身。從另一角度看,這種分裂盡管在“私”的意識(shí)內(nèi)部展開,但同時(shí)也可以認(rèn)為是自我與外部世界關(guān)系的一種內(nèi)在化。以人作為媒介,不斷加速商品化的進(jìn)程是歷史的必然。商品的制造、流通、利潤(rùn)獲取使個(gè)體陷入相互依賴的境地。此時(shí),自我與其說是作為認(rèn)知的主體,還不如說是被規(guī)定的媒介。無限的方程式計(jì)算將盲目的科學(xué)主義和技術(shù)主義的負(fù)面無限暴露,消泯了啟蒙主義誕生以來賦予個(gè)人的倫理價(jià)值和理性價(jià)值。與之相對(duì),超出個(gè)體之外的“機(jī)械”居高臨下俯視著這一切,使人成為喪失自我意識(shí),被規(guī)定性的存在,好比是漂浮在真空中的碎片。用“他動(dòng)性”來表現(xiàn)這一特性無疑再恰當(dāng)不過。因此,盡管“私”揮動(dòng)“心理分析的利刃,妄圖與現(xiàn)實(shí)作殊死一搏。但是,由于自我內(nèi)心的封閉,反而在意識(shí)世界的動(dòng)蕩中將自己切成碎片”。[7]“私”即便已經(jīng)感覺到自我意識(shí)受“腐蝕”所造成的恐怖,企圖通過內(nèi)心的努力重新修復(fù)過去的自我,但不以人的意志為左右的“現(xiàn)代性”使他已無法重新回到過去。不僅是“私”,對(duì)于我們自己來說,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腐蝕性已經(jīng)侵入到每個(gè)人的意識(shí)深處,成為各自內(nèi)心無法擺脫的夢(mèng)魘。要想擺脫這一夢(mèng)魘必須直面這個(gè)疑問:存在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難道真的難以調(diào)和嗎?在現(xiàn)代化成為不可阻擋的鐵的事實(shí)面前,個(gè)體倘若不選擇放棄完整的自我,轉(zhuǎn)而接受自我相對(duì)化的結(jié)局,就難以擺脫分裂的命運(yùn)嗎?四人稱視角最終的指向正是上述兩種視角的交匯。代表自我的第一人稱和代表他者的第三人稱相互作用,兩者的“相對(duì)關(guān)系”構(gòu)成了小說《機(jī)械》的終極命題。這種“相對(duì)關(guān)系”可以用一種四元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把握。
1.現(xiàn)代型文明之下人類與機(jī)械的關(guān)系:能動(dòng)化和自動(dòng)化之間的關(guān)系;
2.現(xiàn)代型文明之下人類與人類的關(guān)系:主體性和包容性之間的關(guān)系;
3.現(xiàn)代型文明之下人類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接受主體和對(duì)象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
4.現(xiàn)代型文明之下人類自我與自我的關(guān)系:絕對(duì)自我和相對(duì)自我的關(guān)系。
除非可以克服時(shí)間的一維性,否則現(xiàn)代人就必須被迫委身于這四種“相對(duì)關(guān)系”以謀求生存之道。小說中“私”保持“純粹”的客觀前提,首先應(yīng)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徹底的全面的相互信任的基礎(chǔ)之上。而與社會(huì)共同體的日益成熟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日益走向崩潰的精神共同體已不復(fù)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私”自我意識(shí)的一部分仍固執(zhí)地處在現(xiàn)有價(jià)值基準(zhǔn)的真空狀態(tài);另一部分又處在固有價(jià)值基準(zhǔn)喪失的失重狀態(tài)。所以隨著“人際關(guān)系”的更新和變化,“私”的意識(shí)不斷機(jī)械地受他人的意識(shí)的轉(zhuǎn)移,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自我意識(shí)喪失了判斷和自我判斷。小說的結(jié)尾,隨著“因果關(guān)系”鏈條的斷裂(屋敷的死亡),主人公“私”承認(rèn)自己陷入了混亂:“難道我的大腦像老板的大腦一樣從一開始就被氯化鐵侵入了嗎?我已經(jīng)不認(rèn)識(shí)我自己了,我只覺得機(jī)械的鋒利尖端逐漸向我逼近”。[6]316在這里,主體離心化是主人公自我意識(shí)危機(jī)的根源,這和自我成長(zhǎng)初期的不完滿有關(guān);加上氯化鐵的腐蝕作用,每個(gè)人物像鏡面反射一般,刺激——反應(yīng)式的心理機(jī)制顯示出正常人類思維的退化。對(duì)外在事物而言,倘若僅以元素周期表里化學(xué)分子的方式存在,這無疑是自我意識(shí)的災(zāi)難。但是主體性確立的同時(shí)就意味著自我的真正確立嗎?就“私”的意識(shí)結(jié)構(gòu)而言,自我意識(shí)的確立過程本身即意味著一種矛盾。在相互對(duì)立的兩種價(jià)值基準(zhǔn)錯(cuò)位當(dāng)中,隱藏在自我意識(shí)深處的沖突就會(huì)變得不可避免。因?yàn)閭€(gè)體畢竟存在于社會(huì)共同體的影響之下,無時(shí)無刻地置身于他者的關(guān)系之中。既成的個(gè)性也好,人格也罷,抽象的觀念難免受到他者的影響和支配。因而橫光所表現(xiàn)的“純粹意識(shí)”似乎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固有的自我”更是從中派生出來的遙遠(yuǎn)神話。倘要如芥川龍之介那樣堅(jiān)持這種神話,反而更近乎一種自虐。因?yàn)榧幢阒黧w的自我意識(shí)是高度純粹的,但在理解過程中純粹意識(shí)就已不復(fù)存在了,轉(zhuǎn)而屈服于對(duì)象的“不純性”。假如完美的理想的“人際關(guān)系”要借助完美的純粹的自我真誠(chéng)地相互理解來實(shí)現(xiàn),那么,這種理解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到的是,從《上海》到《旅愁》,橫光利一正朝著悲觀主義漸行漸遠(yuǎn),在這一問題上,芥川龍之介的自殺對(duì)他帶有決定性的影響。以他為代表的“失敗的文學(xué)”昭示著一種探索已經(jīng)走到盡頭,并成為自虐式人格的笑話。“不用裝模作樣也能生活下去的人,除了瘋子以外還能有誰呢?”[8]正如這一聲嘆息所昭示的那樣,《純粹小說論》及其實(shí)踐所針對(duì)的痛苦事實(shí)也開始浮現(xiàn)。當(dāng)作為個(gè)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需要“經(jīng)常性的感動(dòng)”就足以茍全性命的話,那么重復(fù)現(xiàn)成的、外在性的規(guī)范就成為每個(gè)自我理所當(dāng)然的選擇。如果這個(gè)要求對(duì)于普羅大眾顯得過高,那么對(duì)于日本的純文學(xué)作家來說是否仍然過高呢?從解釋“四人稱”這樣看似晦澀的小說觀念就足以看出危機(jī)的征兆:純文學(xué)的探索已走向式微,日本的純文學(xué)作家已經(jīng)很難再誕生一流的作品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其中的緣由并不使人費(fèi)解。正如“私”的自我意識(shí)所經(jīng)歷的那樣,當(dāng)人對(duì)外在性的機(jī)緣越來越倚重,那么要求高度適應(yīng)、重復(fù)性的機(jī)能必然催生人腦的機(jī)械運(yùn)動(dòng)。由此可見,橫光滑向國(guó)語服從時(shí)代的同時(shí),也不可避免地滑向現(xiàn)代化的服從時(shí)代。此時(shí)此刻,當(dāng)人們目送橫光苦澀的背影離去的時(shí)候,不禁會(huì)留下無盡的凄涼。但是,只要我們各自的內(nèi)心仍保有一絲光亮,就足以使日益枯瘠的自我免于毀滅。讓我們小心地將它封存起來,等待時(shí)機(jī),并為它們的重生默默祈禱。
六、結(jié)論
昭和初期新心理主義文學(xué)轉(zhuǎn)向除了延續(xù)新感覺派語言革命所帶來的沖擊外,也同樣顯示出方法論上與世界文學(xué)建立同時(shí)性的意識(shí)。因此從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影響研究的角度分析橫光利一文學(xué)的接受性,并以這種方式來解釋橫光利一在1930年前后“突變”的原因,就難免存在模糊作者前后期小說共通特質(zhì)的可能。而《機(jī)械》對(duì)私小說敘述中自我觀照因素的接受性是難以忽略的。長(zhǎng)期以來,“一體化”烙印明顯的日本社會(huì)對(duì)個(gè)人訴求的抑制并未真正消除。和普遍語境下的“我”不同,日本文學(xué)中的“私”在習(xí)慣勢(shì)力的夾縫中上下求索。自我的封閉實(shí)屬一種被逼無奈,而封閉中對(duì)自我的質(zhì)詢更加尖銳。《破戒》的主人公丑村通過自我的“身份追認(rèn)”,跳出偏見,最終迎來了“破滅后的黎明”,但仍然是對(duì)傳統(tǒng)勢(shì)力部分妥協(xié)下的結(jié)果。妥協(xié)的結(jié)果也未必時(shí)常如意,個(gè)體的意識(shí)總是擺脫不了懺悔和頹廢,兩種意識(shí)相互絞纏,成為“私”意識(shí)內(nèi)部的基本結(jié)構(gòu)。而通過對(duì)小說《機(jī)械》的細(xì)節(jié)考察,將這種掙扎放置到更廣闊的社會(huì)性主題中,深入不同背景下“私”的意識(shí)結(jié)構(gòu),從自我—自我到自我—社會(huì)的對(duì)立當(dāng)中,現(xiàn)代型文明中相對(duì)關(guān)系下主體失位的癥狀呈現(xiàn)的是不變的風(fēng)景。以此為起點(diǎn),透過《純粹小說論》中構(gòu)成的諸要素來分析橫光利一文學(xué)后期的表現(xiàn)意識(shí)及可能性;在更高層面上衡量橫光利一文學(xué)的普世價(jià)值顯得尤為必要,其在世界文學(xué)中的位置不應(yīng)受到忽視。而關(guān)于“形式主義論爭(zhēng)”的內(nèi)在價(jià)值,也同樣不僅局限于日本文學(xué),同時(shí)應(yīng)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水準(zhǔn)上進(jìn)行廣泛的探討。
[1]伊藤整.新興藝術(shù)派と新心理主義文學(xué)[M].新潮社,1973.
[2]伊藤整.新しき小説の心理的方法[M].新潮社,1973.
[3]小林秀雄.橫光利一.小林秀雄全集1巻[M].新潮社,1978.
[4]佐佐木基一.昭和文學(xué)論.現(xiàn)代日本小説[M].和光社,1954.
[5]教誓悠人.橫光利一機(jī)械における〈四人稱〉の問題:「語り」の方法として[J].近代文學(xué)試論,2007,(45).
[6]橫光利一.橫光利一集[M].新潮社,1965.
[7]神谷忠孝.橫光利一における象徴意識(shí)の変遷[J].帯広大谷大學(xué)紀(jì)要,1968,(6).
[8]田口律男.橫光利一機(jī)械論:ある都市流入者の末路[J].近代文學(xué)試論,198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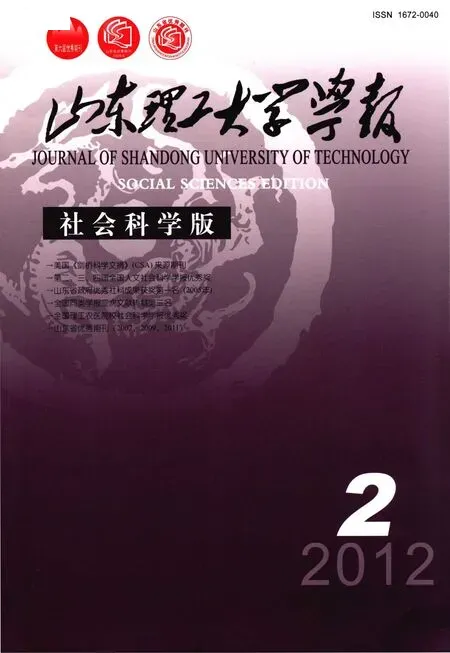 山東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年2期
山東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年2期
- 山東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了解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和綠色物流業(yè)發(fā)展的力作——讀《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與發(fā)展綠色物流研究》有感
- 認(rèn)識(shí)當(dāng)代中國(guó)政治改革的獨(dú)特視角——《當(dāng)代中國(guó)政治改革的制度經(jīng)濟(jì)分析》評(píng)介
- 家庭教育新理念——從西方家庭治療理論談起
- 關(guān)于語文教學(xué)類期刊發(fā)展策略的若干思考
- 《鹽鐵論》話語傳播的文化蘊(yùn)涵初探
- 英語廣告中的模因現(xiàn)象及其修辭效應(yī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