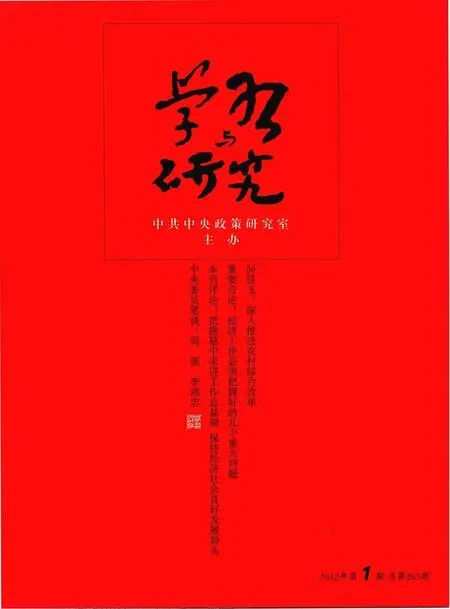從孫中山的追隨者到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戰(zhàn)士──對(duì)曾祖父莊禹梅先生生平事跡的一些回憶
莊爭(zhēng)爭(zhēng)
(北京智達(dá)行廣告公司,北京 100000)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lái)臨之際,我敬愛(ài)的曾祖父——一位辛亥革命的見(jiàn)證者和親歷人,一生追求真理的革命老人,莊禹梅先生傳奇的革命經(jīng)歷和他家庭生活的片段,象塵封已久的老照片,又一次被打開(kāi),一幀一幀地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
傳奇而坎坷的一生
曾祖父莊禹梅,本名莊繼良,1885年出生于寧波鎮(zhèn)海莊市的一個(gè)書(shū)香人家,祖上可謂世代書(shū)香門(mén)第,但生活一直很貧困。曾祖父的父母早亡,他從小是由他的祖父母撫養(yǎng)成人的。曾祖父少年時(shí)代,一直跟著他的叔父讀書(shū)。曾祖父的叔父名叫莊賡思,是個(gè)舉人,他向往仕途,認(rèn)為舉人哪有不當(dāng)官的當(dāng)一個(gè)知縣總沒(méi)有問(wèn)題吧?可是由于家里窮,沒(méi)有錢(qián)活動(dòng),他一直到死也沒(méi)有當(dāng)上官。曾祖父的叔父對(duì)他的侄子要求很?chē)?yán),寫(xiě)字要端正,因此曾祖父的小楷字練成象鉛印字體一樣;讀書(shū)不離四書(shū)五經(jīng),而且要背得滾瓜爛熟。但曾祖父卻不喜歡讀這些書(shū),而喜歡看一些所謂“閑書(shū)”,很欣賞黃梨洲等反清文章和帶有唯物主義思想的作品。第一次赴考秀才時(shí),曾祖父的叔父再三囑咐他要名列前茅,但是曾祖父對(duì)科舉不感興趣,認(rèn)為考上舉人也不過(guò)如此,所以在考場(chǎng)上為人捉刀,用替別人考上秀才得到的報(bào)酬供大家吃喝玩樂(lè)一番后,回轉(zhuǎn)家來(lái)。曾祖父的叔父為此大發(fā)脾氣,不許他離開(kāi)家門(mén)一步。后來(lái)考上了秀才第一名,這才寬恕了他。
曾祖父的叔父死后,一家重?fù)?dān)由曾祖父挑起來(lái),他只好做館(設(shè)私塾)或外出教書(shū),后來(lái)在上海辦了一所函授學(xué)校,想以此維持生活,由于他書(shū)生氣十足,根本不會(huì)經(jīng)營(yíng),反而賠了很多錢(qián),把家里有限的田地都賣(mài)了。于是他開(kāi)始用"莊病骸"的名字寫(xiě)章回體武俠小說(shuō),以賣(mài)稿為生。1915年他為上海國(guó)華書(shū)局等寫(xiě)稿,出版過(guò)很多俠客小說(shuō)。由于曾祖父是秀才,又出過(guò)許多武俠小說(shuō),他在家鄉(xiāng)也因此出名。現(xiàn)代著名文學(xué)家唐弢先生的父親和曾祖父是世交。唐弢在給巴人(王任叔)《點(diǎn)滴集》寫(xiě)的序言中,曾經(jīng)有過(guò)這樣的敘述:“我父親不識(shí)字,卻很佩服莊禹梅(繼良)的為人,常常‘繼良先生長(zhǎng),繼良先生短’的談到他,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有學(xué)問(wèn)的人,有了學(xué)問(wèn)就不受人欺侮。他不顧人家嘲笑和譏刺,借債典屋的讓我上學(xué),勉勵(lì)我要以莊禹梅為榜樣,好好讀書(shū)……我呢,,那時(shí)讀過(guò)以‘蛟川莊病骸’署名的武俠小說(shuō),以為寫(xiě)俠客的人,一定自己也是俠客。”其實(shí)曾祖父的武俠小說(shuō),無(wú)非是幻想由武俠一類(lèi)人物來(lái)鏟除人間的一切不平和冤屈。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從紹興至寧波,曾祖父曾一度當(dāng)過(guò)孫中山先生的私人秘書(shū)。他非常崇拜孫中山先生,以后還專(zhuān)門(mén)收集了許多有關(guān)孫中山先生的資料,為上海環(huán)球書(shū)局寫(xiě)了一部四大冊(cè)的章回體小說(shuō)《孫中山演義》(該書(shū)后又多次出版過(guò)不同的版本,最近的兩次分別于1996年由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唐弢先生作了序言,稱(chēng)譽(yù)此書(shū)為“寫(xiě)孫中山的小說(shuō)中寫(xiě)得最好的一部”。2011年,為紀(jì)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州出版社又再次出版了這部小說(shuō))。
曾祖父喜歡做新聞工作,他的后半生差不多一直搞報(bào)紙。1923年在寧波的《時(shí)事公報(bào)》當(dāng)編輯時(shí),鎮(zhèn)海縣署抓獲一名盜匪。經(jīng)查,乃是鎮(zhèn)海炮臺(tái)司令張伯岐部下的士兵。曾祖父為此寫(xiě)了一篇短評(píng),文中說(shuō):“兵化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短評(píng)刊出后,引起小軍閥張伯岐的惱怒,要寧波鎮(zhèn)守使王桂林查緝,王桂林就把曾祖父和《時(shí)事公報(bào)》社長(zhǎng)金臻庠一同逮捕起來(lái),約拘留了一個(gè)月,后經(jīng)各方面營(yíng)救,才得保釋。這是曾祖父第一次坐牢。這一時(shí)期,他開(kāi)始認(rèn)識(shí)到軍閥制度必須要推翻。1925年他經(jīng)陳國(guó)詠介紹,加入了改組后的國(guó)民黨。1926年11月被選為國(guó)民黨寧波市黨部商民部長(zhǎng)。第二年3月任寧波《民國(guó)日?qǐng)?bào)》社社長(zhǎng)。
1927年4月,蔣介石要公開(kāi)叛變革命。寧波《民國(guó)日?qǐng)?bào)》首先對(duì)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開(kāi)火,刊登了該報(bào)編輯倪毓水寫(xiě)的《蔣介石猶效軍閥故伎耶》、《王俊十大罪狀》這兩篇文章,引起了蔣的親信、寧臺(tái)溫防守司令王俊的大怒。4月10日,王俊派了一個(gè)副官把社長(zhǎng)莊禹梅傳了去,問(wèn)他對(duì)這兩篇文章負(fù)責(zé)不負(fù)責(zé)他毫不推托,承認(rèn)社長(zhǎng)應(yīng)該負(fù)責(zé)。于是王俊把他禁閉起來(lái)。
曾祖父被捕的消息一傳出,國(guó)民黨市黨部當(dāng)即召開(kāi)緊急會(huì)議,商量對(duì)策,并推黨部常委楊眉山(共產(chǎn)黨員)和寧波市總工會(huì)委員長(zhǎng)王鯤(共產(chǎn)黨員),邀同寧波民主人士張申之、俞佐庭到司令部去質(zhì)問(wèn):莊禹梅為什么被捕?殊不知這是王俊有計(jì)劃有預(yù)謀的行動(dòng)。楊眉山、王鯤是寧波著名的共產(chǎn)黨員,王俊正要逮捕他們,這下來(lái)得正好。鑒于張申之和俞佐庭是本地紳士,王俊客氣一番后,便把張、俞兩人送走,而把楊、王兩人扣留了。隨即把楊、王兩同志和曾祖父關(guān)在一起。
曾祖父和楊眉山、王鯤關(guān)在監(jiān)房里,朝夕相處兩個(gè)多月,耳濡目染受到了革命思想和共產(chǎn)主義的啟蒙教育。后來(lái)這兩位同志犧牲了,但他們的高尚品德,對(duì)曾祖父教育很深。
在獄中還有共產(chǎn)黨員王任叔,對(duì)曾祖父也很有影響。他是楊眉山、王鯤二位烈士犧牲后的第二天被捕的,也和曾祖父同監(jiān)牢。王任叔曾經(jīng)懷著憤怒的心情寫(xiě)了一首詩(shī):“翻手作云覆手雨,屠夫得意上青天;而今百物皆昂貴,唯有頭顱不值錢(qián)!”曾祖父受他們的教育和影響,在獄中也始終表現(xiàn)得很堅(jiān)強(qiáng)。據(jù)曾祖母講,她到模范監(jiān)獄去探監(jiān),看到曾祖父背上被打得血跡斑斑,沒(méi)有一塊完好的肉。
1929年3月間,由于寧波士紳和寧波旅滬同鄉(xiāng)會(huì)會(huì)長(zhǎng)虞洽卿的疏通,曾祖父的案子得到重新審理,并宣判無(wú)罪釋放。這是曾祖父第二次坐牢。二十個(gè)月的獄中生活,是曾祖父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點(diǎn)。以前他是個(gè)窮秀才,從此他堅(jiān)定地跟著共產(chǎn)黨干革命了。5月間就找到中共寧波特支組織部長(zhǎng)張旦輝(張子叟),并經(jīng)張介紹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從此他在黨領(lǐng)導(dǎo)下從事報(bào)紙工作。
1934年冬天,我的爺爺在上海左翼作家聯(lián)盟閘北區(qū)委作宣傳工作。一天接到從親戚家轉(zhuǎn)來(lái)曾祖父的一封信,說(shuō)他又被捕了。這是曾祖父第三次入獄。不過(guò)這次敵人沒(méi)有任何證據(jù),無(wú)法起訴,曾祖父很快就被釋放了。
從1934年到抗戰(zhàn)爆發(fā),曾祖父一直在寧波幾家報(bào)紙當(dāng)編輯。1936年10月他任寧波《商情日?qǐng)?bào)》編輯主任時(shí),由于報(bào)紙積極宣傳抗日,抨擊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因而引起當(dāng)局的痛恨,1937年1月將該報(bào)社社長(zhǎng)、曾祖父,還有兩個(gè)編輯逮捕入獄,報(bào)社被封。反動(dòng)當(dāng)局根據(jù)所謂“危害民國(guó)緊急治罪法”,對(duì)他們四人分別判處徒刑五年。他們不服,據(jù)理力爭(zhēng),并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訴。這已是1937年秋天的事了。這時(shí),抗戰(zhàn)已全面展開(kāi),所謂“危害民國(guó)緊急治罪法”被迫廢除了。因此,南京最高法院只得撤銷(xiāo)對(duì)他們的原判,交保釋放。這是曾祖父第四次入獄。
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曾祖父留在家鄉(xiāng)參加中共浙東臨時(shí)特委領(lǐng)導(dǎo)下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在這段時(shí)間,他做過(guò)統(tǒng)戰(zhàn)工作,編輯過(guò)共產(chǎn)黨員學(xué)習(xí)文件,接觸過(guò)從解放區(qū)進(jìn)入敵戰(zhàn)區(qū)工作的同志和地下工作者。
1945年1月應(yīng)浙東區(qū)黨委城工委書(shū)記王文祥之召,曾祖父到了四明山解放區(qū)。這里有一批新聞工作者,他們熱烈歡迎這位老報(bào)人的到來(lái)。在解放區(qū)辦自己的報(bào)紙,這對(duì)曾祖父確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情,也是他一生所夢(mèng)想的事業(yè)。他在那里大約工作了十個(gè)多月,日本軍國(guó)主義投降了。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后,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想蠶食和并吞我們解放區(qū)。為了集中力量,中央決定主動(dòng)撤出浙東根據(jù)地,干部和軍隊(duì)主力迅速北上,凡是能就地隱蔽的,就隱蔽堅(jiān)持下來(lái)。因此,組織決定讓曾祖父回到莊市。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的黨組織關(guān)系由中共浙東臨委轉(zhuǎn)給了在寧波負(fù)責(zé)搞文化界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徐朗(筆名徐吹)同志;他作為特別黨員,由徐朗同志單線聯(lián)系。1947年他重進(jìn)《時(shí)事公報(bào)》社,任副刊“四明山”主編。他針砭時(shí)弊,寫(xiě)出了不少魯迅風(fēng)格的雜文,被譽(yù)為“寧波魯迅”。徐朗同志每隔兩周走訪他,傳達(dá)黨的有關(guān)文件和方針、政策。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他團(tuán)結(jié)了一批進(jìn)步的文化界人士,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一批進(jìn)步青年作者。1948年初,為配合解放戰(zhàn)爭(zhēng)和國(guó)統(tǒng)區(qū)的反蔣運(yùn)動(dòng),曾祖父籌建了“寧波文藝協(xié)會(huì)”,任理事長(zhǎng)。1948年4月30日,徐朗同志被當(dāng)局逮捕,曾祖父隨之失去了黨的聯(lián)系。
解放后,寧波黨政領(lǐng)導(dǎo)對(duì)曾祖父非常關(guān)心和重視。他先后擔(dān)任過(guò)六屆寧波市政協(xié)副主席,三屆寧波市民革主委,并被選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huì)代表。由于寧波黨組織在臨解放前遭到過(guò)較嚴(yán)重的破壞,加之他是特別黨員的身份,對(duì)他的黨籍,一直沒(méi)有進(jìn)行調(diào)查解決。但是他一直誠(chéng)誠(chéng)懇懇、艱苦地工作著,晚年,還完成了《中國(guó)古代史析疑》和《古書(shū)新考》兩部著作。
在十年動(dòng)亂中,曾祖父遭受了殘酷的迫害,于1970年6月23日含冤去世。1979年1月18日,在曾祖父逝世后九年,黨實(shí)事求是地為他平反昭雪,召開(kāi)了追悼大會(huì)。1986年5月30日,由寧波市政協(xié)副主席陳阿翠護(hù)送曾祖父部分遺物骨灰盒安放在鄞縣樟村烈士公墓。至此,曾祖父坎坷而又傳奇的一生被畫(huà)上了一個(gè)圓滿的句號(hào)。
2010年12月,寧波市政府對(duì)樟村烈士陵園進(jìn)行了重新規(guī)劃擴(kuò)建,使先烈們的骨灰從原來(lái)的安息堂遷到了生態(tài)墓地。新擴(kuò)建的陵園墓地很開(kāi)闊,依山傍水,風(fēng)景秀麗。我代表我們莊家健在的長(zhǎng)輩們前去辦理遷墓事宜。當(dāng)時(shí)又恰逢為籌備紀(jì)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民革寧波市委、寧波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huì)和寧波市江北區(qū)新四軍歷史研究會(huì)共同編印出版了《莊禹梅紀(jì)念文集》。民革寧波市委的領(lǐng)導(dǎo)對(duì)這次遷墳非常重視,全程由專(zhuān)人陪同我落實(shí)遷葬事宜。并在12月18日遷墳的當(dāng)天,舉行了一個(gè)簡(jiǎn)單而隆重的儀式,參加儀式的有民革寧波市委的領(lǐng)導(dǎo)和同志們,寧波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huì)的胡春和王泰棟兩位老前輩,還有曾祖父生前最喜愛(ài)的鄰居小朋友張志平先生。民革主委王建康同志在儀式上講了話,高度褒獎(jiǎng)了曾祖父革命奮斗的一生。民革黨員代表,同時(shí)也是《莊禹梅紀(jì)念文集》的編輯之一的王一羽老師,將文集鄭重地放入墓穴中。我代表我們的家人也在儀式上講了話,并將1996年重新出版的《孫中山演義》放入了墓穴。有這兩部書(shū)陪伴在曾祖父的身邊,對(duì)曾祖父應(yīng)該是莫大的安慰,組織沒(méi)有忘記他,他的后人更在紀(jì)念他。老人家如果在九泉下有知,一定會(huì)含笑釋?xiě)训摹?/p>
我所了解的曾祖父
很遺憾我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曾祖父,他在世時(shí)我還很小,我們分別生活在北京和寧波一南一北兩個(gè)地方,遙遠(yuǎn)的距離、不太便利的交通,最主要的是文革時(shí)的動(dòng)蕩阻隔了我們的相見(jiàn)。對(duì)他的了解多是從家里的長(zhǎng)輩那里聽(tīng)說(shuō)的。
由于歷史原因,曾祖父一生有過(guò)三次事實(shí)婚姻,我的曾祖母吳珠梅,我們稱(chēng)呼她“太太”,是家里包辦的明媒正娶的夫人,與曾祖父先后生過(guò)三男一女四個(gè)孩子,但只有第二個(gè)兒子,也就是我的爺爺莊啟東和最小的女兒,我的大姑婆莊霞(又名莊斐卿)存活了下來(lái)。他與第二任夫人樂(lè)菱香太婆生有一個(gè)女兒,即我的二姑婆莊蟾影,他和第任三人夫人朱碧心太婆沒(méi)有子女。
曾祖父祖輩幾代娶的媳婦都是有文化的,只有曾祖父娶的是個(gè)例外。我的“太太”出身于商人家庭,很小的時(shí)候母親就去世了,而父親又忙于生計(jì),她就過(guò)早地承擔(dān)了家庭的生活,因而沒(méi)有讀過(guò)書(shū),不識(shí)字,婚后,曾祖父與她也就沒(méi)有更多的共同語(yǔ)言。但“太太”一生非常勤勞,堅(jiān)強(qiáng),樂(lè)善好施,與人為善。曾祖父一介書(shū)生,一生清貧,沒(méi)有足夠的錢(qián)來(lái)養(yǎng)家,太太也是巧婦難為無(wú)米之炊,精打細(xì)算難以維持一家的生活,帶過(guò)來(lái)的嫁妝也不得不變賣(mài)。這樣不免為生計(jì)而抱怨,為此與曾祖父時(shí)有爭(zhēng)吵。但太太同時(shí)又是一個(gè)明事理的人,對(duì)丈夫的所做的事情都積極地予以支持。書(shū)香門(mén)第,都是嗜書(shū)如命,祖上留下來(lái)的所謂值錢(qián)的東西,也就是書(shū)了。據(jù)爺爺后來(lái)講,家里的許多藏書(shū)都是珍本,善本,還有不是很全的四庫(kù)全書(shū)。曾祖父愛(ài)書(shū),從不在藏書(shū)上簽自己的名字或加蓋收藏章。這些藏書(shū)在當(dāng)時(shí)就已經(jīng)很值錢(qián)了,但家里即使再窮,誰(shuí)都沒(méi)有動(dòng)過(guò)用書(shū)去換錢(qián)的念頭。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當(dāng)年為了營(yíng)救獄中的曾祖父,萬(wàn)般無(wú)奈的“太太”隨便拿了一部書(shū)就去賣(mài)了,收購(gòu)書(shū)的人,看她是一個(gè)沒(méi)有文化的婦道人家,給了她八百塊大洋,太太就是用了這筆錢(qián)去活動(dòng)打點(diǎn)營(yíng)救曾祖父的。曾祖父出獄后得知此事非常痛惜,還抱怨過(guò)太太。
我的爺爺作為曾祖父唯一的兒子,同時(shí)也是他同輩中唯一的男孩子,從小受家里祖輩極大的關(guān)愛(ài)。我的“太太”不識(shí)字,爺爺?shù)膯⒚山逃怯伤脑婺福簿褪俏以娓傅淖婺搁_(kāi)啟的。曾祖父由于從小受到他的叔父過(guò)于嚴(yán)厲的管教,不希望再以這種方式來(lái)教育自己的兒子,他從不強(qiáng)迫爺爺只學(xué)習(xí)“四書(shū)五經(jīng)”,鼓勵(lì)爺爺多學(xué)習(xí)白話文及現(xiàn)代知識(shí),所以爺爺古文的基礎(chǔ)打得不像曾祖父那么堅(jiān)實(shí)。受曾祖父進(jìn)步思想的影響,爺爺還在上中學(xué)時(shí)就積極參加進(jìn)步組織,看一些進(jìn)步書(shū)籍。1927年,17歲的爺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8年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1933年?duì)敔斣谏虾=Y(jié)識(shí)了同為地下工作者的奶奶,兩人從此牽手一起風(fēng)風(fēng)雨雨走過(guò)了60余年的革命道路。
1934年10月,我的爸爸——曾祖父唯一的孫子在上海出生了,曾祖父給他取名英翹。這也是爺爺奶奶唯一的一個(gè)孩子。爸爸出生后,爺爺從寧波把“太太”和大姑婆一起接出來(lái),與他們一起生活,從此“太太”再也沒(méi)有回過(guò)寧波,也再?zèng)]有與曾祖父見(jiàn)過(guò)面,她跟隨爺爺、奶奶轉(zhuǎn)戰(zhàn)南北,抗日戰(zhàn)爭(zhēng)逃難,一路上還要照顧未成年的大姑婆和幼小的爸爸,歷盡千辛萬(wàn)苦。1939年?duì)敔斈棠滔绕趤?lái)到延安,1940年?duì)敔攺难影渤霭l(fā)到重慶把“太太”、大姑婆和爸爸一起接到延安,一家人終于又相聚在一起了。大姑婆上了延安的俄文專(zhuān)科學(xué)校(現(xiàn)在的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前身),由此參加革命,直到離休。“太太”到延安見(jiàn)到的是革命的隊(duì)伍和同志,大家都顯得很親切。“太太”在延安積極參加“大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她紡的線因?yàn)橘|(zhì)量好,邊區(qū)政府還特為此頒發(fā)了獎(jiǎng)狀。這份獎(jiǎng)狀太太一直珍藏著。后來(lái)因?yàn)槟甏茫?jiǎng)狀都不完整了。“太太”1979年去世后,于八十年代后期,爺爺、奶奶將殘存的獎(jiǎng)狀捐贈(zèng)給了北京抗日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館保存。
“延安整風(fēng)運(yùn)動(dòng)”后,“太太”又跟著爺爺、奶奶來(lái)到了綏德,后又離開(kāi)綏德先后到了東北的哈爾濱、沈陽(yáng)。東北解放后,1952年?duì)敔敗⒛棠虖纳蜿?yáng)調(diào)到北京工作,“太太”也跟隨著到了北京。
爸爸沒(méi)有跟隨爺爺、奶奶和太太一起到北京,他在東北也參加了革命隊(duì)伍。東北解放后,他先后在哈爾濱和沈陽(yáng)繼續(xù)讀書(shū),1960年畢業(yè)于長(zhǎng)春地質(zhì)學(xué)院。在長(zhǎng)春地質(zhì)學(xué)院學(xué)習(xí)的同時(shí)也收獲了愛(ài)情,他與我的媽媽在學(xué)校相識(shí)、相知、相戀,畢業(yè)后結(jié)婚,又雙雙留校教學(xué)。同年,因國(guó)防建設(shè)的需要,兩人一起作為原子彈核試驗(yàn)的尖端人才被總參工程兵部隊(duì)選拔上,入伍到了北京。1962,1963年哥哥和我先后在北京出生了。我的大姑婆這時(shí)也是五個(gè)孩子的媽媽了,他們家也在五十年代中期從天津調(diào)到北京工作,這樣我們這個(gè)以“太太”為長(zhǎng)輩的一大家人就在北京扎根了。
曾祖父這時(shí)已在寧波擔(dān)任了民革寧波市委的主委,和寧波市政協(xié)副主席,和他一起生活的是第三任夫人,朱太婆。盡管他人在寧波,但他還是很記掛我們這一家的。爺爺、奶奶經(jīng)常會(huì)與曾祖父通信問(wèn)候,并定期將全家福照片寄給他,哥哥和我的出生更是引發(fā)了他對(duì)重孫子女的舔犢之情。記得我不滿周歲時(shí),全家又照了一張全家福寄給他,曾祖父看后回信借用了唐代詩(shī)人王維的一句詩(shī)“遍插茱萸少一人”,來(lái)表達(dá)他的思念之情。由于曾祖父當(dāng)時(shí)的婚姻狀況,他沒(méi)能實(shí)現(xiàn)到北京與家人團(tuán)聚的愿望,但他一直希望看看哥哥和我,他的兩個(gè)僅有的重孫子、女,并想要我和哥哥兩個(gè)人中的任何一個(gè),送給他和朱太婆來(lái)?yè)狃B(yǎng)。這樣,家里決定由爸爸、媽媽?zhuān)瑤е液透绺缛ヒ惶藢幉ǎ盐覀儙Ыo曾祖父看看。臨行前,因?yàn)槭嵌欤紤]到寧波的房子不像北京的房子有暖氣,所以特地做了兩件漂亮的小棉袍,準(zhǔn)備到寧波去穿。但最終還是出于我們還太小,當(dāng)時(shí)的交通工具不像現(xiàn)在這樣便利等因素的考慮,還是放棄了這次的行程。沒(méi)能在他有生之年,直接感受到他老人家的愛(ài)撫和教誨,現(xiàn)在想起來(lái)非常遺憾。這兩件小棉襖成了唯一的紀(jì)念,從幼兒時(shí)期的小棉袍穿成了小學(xué)時(shí)代的小棉襖,在我們懂事以后,每年冬天準(zhǔn)備拿出來(lái)穿時(shí),總會(huì)聽(tīng)到“太太”或是奶奶說(shuō)起這件小棉袍的來(lái)歷。記得我小的時(shí)候,遇到不懂的問(wèn)題問(wèn)到“太太”,凡是她回答不上來(lái)時(shí),總會(huì)帶著仰視和遺憾的表情說(shuō)一句:“要是你的太公在就好了,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懂。”可見(jiàn)她是很敬佩曾祖父的才學(xué)的。
平靜而又幸福的生活被1966年開(kāi)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同千百萬(wàn)個(gè)遭遇不幸的家庭一樣,我們的家也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磨難。先是爺爺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批斗,家也被抄了。爸爸、媽媽由于所在的大西北的核試驗(yàn)基地是高度保密單位,當(dāng)初派去的技術(shù)干部都是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的政審,必須是根正苗紅的。所以他們很快受到爺爺所謂“叛徒問(wèn)題”的牽連,在部隊(duì)也被要求揭發(fā)爺爺?shù)膯?wèn)題,并且隨之受到開(kāi)除軍籍,按戰(zhàn)士復(fù)員處理,回到長(zhǎng)春當(dāng)了工廠的工人。爺爺也被發(fā)配去了干校勞動(dòng)改造。北京只剩下“太太”、奶奶、哥哥和我這一家老少。爺爺工資也被扣發(fā)了,每月只發(fā)20元生活費(fèi),奶奶被要求下工廠車(chē)間勞動(dòng),工資按60%發(fā)放,一家人四分五裂,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奶奶的母親在浙江老家生病需要錢(qián),奶奶拿不出足夠的錢(qián),因?yàn)榧依锏拇婵钜脖汇y行凍結(jié)了。
這個(gè)時(shí)候,曾祖父在寧波的日子也不好過(guò)。他多次受到批斗,造反派責(zé)問(wèn)曾祖父:“1927年4月,你被王俊逮捕,與楊眉山、王鯤同關(guān)一籠,為什么楊眉山、王鯤被殺了頭,你卻活著出來(lái)!”在他們眼中,曾祖父是“叛徒”已“鐵證如山”不容“狡辯”了。他被一再勒令交代罪行,被迫多次寫(xiě)出“交代材料”。備受迫害的曾祖父終于病倒了,又得不到及時(shí)治療,搶救,以致不起。1970年6月23日,他帶著極大的遺憾,含冤離世,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凄慘的走向另一個(gè)世界。這時(shí),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也正在經(jīng)歷著磨難,沒(méi)能回去奔喪。他的靈柩是用水泥澆注的一個(gè)匣子,在一個(gè)大雨天由我們的一位遠(yuǎn)房親戚用板車(chē)艱難地拉到鄉(xiāng)下老家,草草下葬在鎮(zhèn)海大同公墓。曾祖父彌留之際,我的二姑婆從上海趕到了他的身邊,他對(duì)二姑婆講:“我不愿就死,我要看看(文革)到底怎樣下場(chǎng)。”由此看來(lái),曾祖父對(duì)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的前途和命運(yùn)是有信心的,他堅(jiān)信文革一定會(huì)結(jié)束。
曾祖父去世后,爺爺奶奶沒(méi)有把這個(gè)消息及時(shí)告訴“太太”,怕她老人家在當(dāng)時(shí)特定的環(huán)境下,過(guò)于悲傷,過(guò)了大概一年左右,她不知從什么渠道得知的消息,在家里她手捧曾祖父的照片,嚎啕大哭,一邊哭一邊操著濃重的寧波話,數(shù)落著曾祖父,內(nèi)心充滿著對(duì)曾祖父愛(ài)恨交加的復(fù)雜心態(tài)。
隨著“四人幫”倒臺(tái),文革的結(jié)束,我們一家也開(kāi)始恢復(fù)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爺爺、奶奶被落實(shí)政策,恢復(fù)工作,爸爸、媽媽也調(diào)回北京工作重新回歸了干部、科技人員的隊(duì)伍,從此以后的生活按照正常的軌跡進(jìn)行著。
曾祖父一生甘于清貧,專(zhuān)注事業(yè),不畏權(quán)勢(shì),堅(jiān)持真理,一身傲骨的精神永遠(yuǎn)激勵(lì)著我們后代努力學(xué)習(xí),不斷進(jìn)取,作一個(gè)對(duì)社會(huì)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