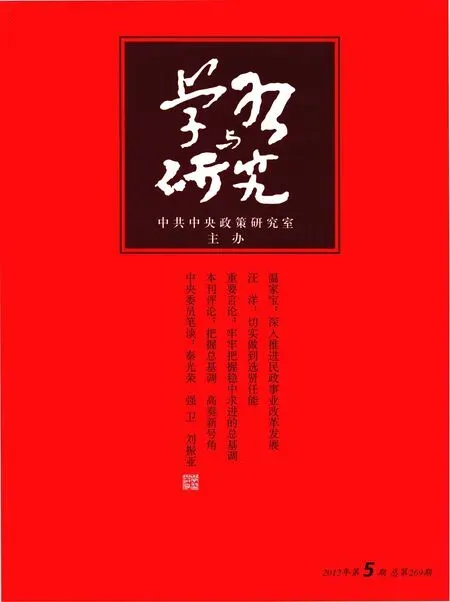農民合作:類型與對策探討
常偉
農民合作:類型與對策探討
常偉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安徽合肥230039)
合作可區分為自發型合作、自愿型合作、動員型合作與強制型合作,本文從合作預期收益、合作意愿、合作發動者、合作機制以及抑制搭便車的約束性安排比較了不同類型的合作,并在此基礎上繼而討論了社會經濟轉型與農民合作的關系,最后就政府能力建設、組織制度創新和道德建設等促進農民合作等對策做了相關探討。
農民合作;類型與對策;社會轉型
農民合作是個經典話題,也是個世紀性命題(賀雪峰、魏華偉,2010),更是一個迄今沒有解決好的難題。本文擬結合現實對于不同類型的農民合作進行分析,并就促進農民合作的現實途徑和對策進行進一步研究和討論。
一、合作的類型
農民合作均表現為農民協調一致的共同行動,根據合作意愿以及推動合作的外部力量而言,可以把合作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如羅興佐(2004)將合作區分為外生型合作與自治型合作,邱夢華(2008)將合作區分為社會交換式合作與集體行動式合作。在筆者看來,根據合作意愿以及推動合作的力量,可以將合作區分為自發型合作、自愿型合作、動員型合作與強制型合作。當人們意識到合作會帶來很大收益,且具有強烈的愿望通過合作改善自己處境時,他們主動發起并采取集體行動進行合作,這種合作便屬于自發型合作。有時人們盡管不主動發起合作,但當別人組織發起合作,他們一般均積極響應參與,這種合作屬于自愿型合作。有時人們合作意愿不強烈,只是在外部力量動員下才參與合作,這種合作可以被認定為動員型合作。當彼此合作意愿較淡薄,搭便車心理普遍存在,個別人甚至對于合作持抵觸態度,只是通過外部強制力量,合作或集體行為才得以實現,這種合作可以被認為是強制型合作。
按照上述區分,農村鄰里之間的自愿相互幫忙,“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顯然屬于自發型合作行為;農村中威望較高的人們組織發起筑路修橋等公益行為,村民們紛紛積極響應,則屬于自愿型合作;同樣是修路架橋,一部分村民起初不愿意參加,但在反復動員勸說下最后也參加了,這樣憑借動員說服得以推進的合作,則是動員型合作行為;至于過去人民公社時期,由生產隊組織的大規模集體勞動,則可以被認定為是強制型合作。它們對于農業和農村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但又存在著較大差別。以下本文結合合作條件分析它們的異同。
二、農民合作的條件
關于農民合作的條件,國內學者多有論述,如宋圭武(2005)認為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其并不必然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鐘云華(2011)認為國家介入是農民合作的外部條件,農村精英參與和組織載體是農民合作的內部條件。如果我們結合本文上述分類來看,除農村大規模集體行動外,農村中的一些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與國家介入、農村精英參與關系并不是太大。但成功的合作均應具備預期合作收益、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推動者等條件,長期成功的合作還需具備相應的合作機制以及對于“搭便車”的約束性制度安排,相關條件不同也導致了自發型合作、自愿型合作、動員型合作與強制型合作等不同的合作形式。
(一)合作預期收益
人們很早注意到,合作會帶來收益。相對于投入成本,當且僅當合作存在著巨大的預期收益時,人們才意識到有必要通過合作行為獲取這種收益,這是任何一種合作活動得以發生的前提。以農村水利建設為例,水利設施改善會帶來農作物產量增加,并且有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這種可以預見的,由于水利設施的改善而帶來的產量和收入的增加,也就是人們在合作修繕水利設施中的合作預期收益。
預期收益大小會影響人們對合作的態度。預期收益大,則人們會通過自發型合作或者自愿型合作以促進獲取彼此利益的改善,預期收益分配較少則可能導致動員型合作,預期收益分配不公的情況下則很難實現合作,即使實現也只能是在強大外力介入下的強制型合作。這里要指出的是,這種合作預期收益是指當事人的預期收益。有時盡管在外界人士看來,合作會帶來較大收益,但在當事人看來卻未必如此(吳思,2001)。如賀雪峰曾提到荊門一村民小組因為農戶不愿出畝均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平減產20%的例子(賀雪峰,2003)。按照當地畝均水稻1500斤的產量,20%即畝均減產約300斤,按0.5元/斤計算,畝均減少150元純收入。在外人看來,如能實現合作,那么農民只需每畝出10元錢便可以使自己每畝收益增加150元,合作凈收益高達每畝140元!但對于當事人來說,由于很難合作在他們預期之內,合作凈收益在當事人看來可能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高。如果當事人普遍預期收益較低,那么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就很難實現。
(二)合作意愿
預期收益是合作的前提,但它并不必然導致合作行為產生,這里就涉及到合作意愿。合作意愿是人們進行合作的愿望,它有名義與真實之分,前者如人民公社時的大規模集體勞動,“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陽”,盡管農田基本建設等搞得很好,但集體大田地的產量和經濟效益均與自留地相差甚遠,原因就在于這種合作意愿并非人們意愿的真實表達。
合作愿望有強弱之分,其強弱與合作收益有關。收益巨大則合作意愿強烈,有助于實現合作。反之,如果合作收益有限,或者盡管合作收益巨大,但由于收益分配不均,致使多數成員收益有限,則有可能削弱或抑制合作意愿。預期收益大的人們有更強的愿望和動機去推動或參與合作,預期收益有限的人們則愿望和動機不會太強,預期利益受損的人們甚至會對合作持抵制態度。合作意愿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合作的具體形式。如果人們普遍合作意愿強烈,則有可能形成自發型合作或者自愿型合作;如果某一部分人合作意愿強烈,另一部分人意愿不強,則有可能形成動員型合作;如果大部分人合作意愿不強,個別人甚至抵制合作,那么合作就很難實現,即便實現合作也只能是強制型合作。
(三)合作發起者
合作發起者對于合作很重要,就自發型合作而言,合作發起人不固定,參與人均有可能充當發起人推動合作,自愿型合作大多由動員組織力量較強的個人或者組織發起。由于人們合作意愿較強,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對于發起者的組織動員能力要求并不嚴格。對于動員型合作而言,發起者的組織動員能力十分重要,甚至可以決定其成敗與否。合作發起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組織。他們或具有較高的威望和公益心,或者發現了合作所蘊含的潛在巨大利益,因此有著強烈的動機和愿望甘冒風險實現它。大凡可以通過農民相互合作,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鄉村,大都離不開這樣的個人或群體。有的即便經濟狀況不佳,也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有著極好的表現。有些經濟狀況較好、農民收入較高的村莊,由于缺乏合作發起者,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往往不盡如人意。至于強制型合作,大多由政府或者政府部門發起,這不僅僅是因為政府有著強大的財力和動員能力,它還可以通過合法強制力的行使來克服搭便車現象,有時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夠確保強制型合作的實現。
(四)合作機制
合作機制可以區分為合作中的信息傳導機制、利益沖突協調機制、組織動員機制、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機制以及對于搭便車行為的約束懲罰機制等。一些專業經濟合作組織,以合作開始,以解體散伙結束,原因大多與合作機制有關。因此,通過必要的制度安排協調各方之間的利益關系,解決合作中的相關矛盾,是確保合作長期進行下去的必要保障。以上述三種不同類型的合作為例,如要長期持續下去,均需要相應的合作機制作為支持。但由于其在主體和具體組織形式等方面有著很大區別,對于合作機制也有著不同的要求。
自發型合作由于范圍小,參與主體彼此了解,合作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利益協調問題。與自發型合作相比,自愿型合作能否長期維系的關鍵取決于參與者的合作意愿。而參與者的合作意愿又取決于他們對于相關信息的了解與把握,信息傳導機制對于自愿型合作尤為重要。動員型合作由于參與主體相對較多,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千差萬別,甚至利益之間存在沖突。這種合作對于合作的組織實施機制有著較高要求,它要求合作的發起者有著較高的要求。如果發起者具有較高的威望和較大影響,深得大家信任,并且具有很強的組織協調能力,則有助于動員型合作的達成,反之則不易形成動員式合作。強制型合作一般涉及到政府或者政府部門,政府的公信力十分重要,如果干群關系較好,干部能力較強作風過硬,政府能夠有效地說服和組織群眾,則可以實現強制型合作,否則強制型合作有可能引發政府與群眾的矛盾甚至沖突。而政府的公信力只能在政府與群眾的良性互動中形成,因而強制型合作對于政府群眾的互動機制提出了較高要求。
(五)抑制“搭便車”的約束性安排
無論何種類型的合作,均要面對“搭便車”問題。“搭便車”是指在非排他性的產品生產和消費中,那些期望他人付費而自己不愿付費的行為。現實一些公益心較強的人們“學雷鋒”,付出很多,另外一些人卻趁機撿便宜。那些“學雷鋒”的人們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感激和尊敬,卻被視為“傻子”、“精神不正常”,結果“好心沒有好報”,成為“搭便車”行為的最終受害者。很顯然,如果找不到相應的解決辦法,抑制或克服搭便車行為,任何制度安排最終都要走向解體。從某種意義上講,“搭便車”也是“農民善分不善合”的重要原因。
在自發型合作中和自愿型合作中,人們以自己的愿望清楚表明了他們對于“搭便車”的態度。動員式合作多通過發起者的動員說服來解決“搭便車”問題,強制型合作則通過一些懲罰性措施,例如罰款的方式來解決(羅澤爾,李建光,1992)。當前農村也存在一些對于“搭便車”行為的約束機制。如皖北泗縣某村在修建農村公路過程中,村里威信較高的老人們組成了修路理事會,并動員村民捐資修路,絕大部分村民在動員說服之下也都捐了。但有一戶村民無論怎么動員也不愿意捐資修路。老人們沒辦法了,就問他:“難道你以后不走這條路了?”那戶村民說:“我以后不走這條路。”老人們又問:“你家父母老了(去世了)可能不走條路?”那戶村民表示即便老人老了也不走這條路。老人們拿這戶極端不合作的村民也實在沒辦法,這戶村民始終沒有捐資。但路修好后不到一個月,這戶村民的父親去世了。結果老人們堵在了這戶村民門口,堅決不讓使用這條其他人捐資修建的公路。筆者調研中也注意到那些習慣“搭便車”的人們在地方上大多聲譽不佳,大家不愿意和他們來往。
三、社會經濟轉型與農民合作
無論承認與否,自農村改革以來的30多年間,以合作形式出現的農村大規模集體行動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這種減少原因何在?社會學家給出的回答是由于經濟市場化所導致農民“行為原子化“所致。這種看法有其道理,但又不盡然。下面筆者結合30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分析農民合作能力下降相關原因。
(一)經濟體制改革與農民合作能力下降
農村改革30多年經濟體制最大的變化當屬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并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使得強制型合作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則意味著農民重獲生產經營自主權,這兩者對于農民合作能力均產生了重大影響。就前者而言,過去30多年農村經濟體制從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到統分結合、雙重經營,再到農村集體經濟的崩潰。這一制度變遷歷程使得政府和鄉村集體對于農民經濟行為失去了強制能力。從而瓦解了農村強制型合作的經濟基礎,削弱了農村強制型合作的組織基礎,并給農村動員型合作帶來了一定困難。但生產經營自主權向農戶家庭的回歸,又使得農民具備了獨立從事生產經營等家庭經濟活動,并承擔由此產生的經濟后果,這又為農村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農村活躍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農村內部的自發型合作并沒有因此減少,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視角來看,應該說農民合作能力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這種下降主要表現為強制型合作和動員型合作行為的減少。我們也注意到,那些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等,農民在基礎設施、農技推廣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成功合作并獲得了較好回報,這可能意味著農民合作能力下降應該是經濟轉型特定階段所出現的現象。
(二)農村政治行政體制變遷與農民合作能力下降
在過去30多年間,鄉村治理制度最大的變化當屬村民自治制度的確立,并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與生產隊分別為鄉鎮政府、行政村和村民小組所取代。在農村改革之前,農民財產權利和人身自由均受到限制,甚至就連去趕集、走親戚也要向生產隊請假。對于農民而言,他們之所以接受人民公社并留在人民公社之內,是因為他們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盡管對于農民和鄉村干部而言,這一制度存在著約束和激勵不足問題,但在以人民公社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嚴密控制下,他們只有接受高層的宣傳教育,從而形成了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偏好,并在政治運動壓力下被動員起來。就組織大規模集體行動的能力而言,人民公社有著極為強大的動員能力,并可以通過政治運動的形式,對于持抵制態度的人們采取強制措施,因而具備了推進動員型合作和強制型合作的巨大能力。
與人民公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農村改革后形成的村民自治體制下,農民可以通過制度性渠道參與農村公共事務,并且可以表達相關意見與看法。這也為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礎。但在村民自治框架下,動員型合作的組織基礎盡管存在,但也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和限制。鄉村干部惟有反復向群眾說清楚利害關系,才有可能動員農民從事動員型合作行為。但由于村民與鄉村干部之間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加之鄉村干部的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鄉村干部的威信和動員能力在農村改革后有所下降。至于強制型合作,隨著農村傳統體制的瓦解,這種形式的合作已經很難實現。
農村政治行政運行機制轉變也對農民的合作能力產生了影響。農村改革前我國農村政治行政運行機制為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它以集體經濟為基礎,以行政控制為控制手段,并依靠思想政治動員進行。它盡管為公共設施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還低成本地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強大的輿論氛圍和精神支持(羅興佐,2006),但它抑制了農民的創造熱情,并且增加了國家的控制成本(于建嶸,2007)。由于這一體制與統購統銷制度存在著共時關聯關系,在農村改革中逐漸為壓力型政治承包制所取代。壓力型政治承包制,是指地方政府為實現有關目標,而采取的將任務數量化分解,承包落實到本級黨委政府部門和下級黨委政府,并責令其在規定期限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狀況進行相關獎懲的目標管理實施機制(常偉,2011)。對于農民而言,它既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民負擔問題。壓力性政治承包制取代了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意味著強制型合作和動員型合作組織運行機制的瓦解,在新型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組織運行機制發育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主要表現為“農民善分不善合”。
(三)農村社會結構變化
自上世紀90年代后,大量農民離開家鄉,遠赴大都市或東部沿海打工。據《人民日報》2011年2月14日報道:2010年我國農民工總數已達2.42億。這種農民工的大規模外出瓦解了農村“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方式。但由于戶籍、住房、教育等制度約束,加之生活成本過高,許多農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農村,自己在城市闖蕩。農村形成了一個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體的留守群體。據一項調查,我國農村有4700萬留守婦女,5800萬留守兒童和4000萬留守老人,其中65歲以上農村留守老人達2000萬。
農民工大規模外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農村社會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民的合作困難,并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帶來消極影響。據中央電視臺2006年6月18日《新聞30分》報道:2004年國家要求把糧食種植補貼資金直接發放到種糧農民手中,而安徽省碭山縣權集鄉權集村的農民三年中卻沒有領到過一分錢的種糧補貼款。后據筆者調查:碭山縣里要修一條縣道,2006年當年造價為每公里13萬元,其中縣里每公里補貼10萬元,鄉鎮需配套3萬,由于農民大規模外出打工,“一事一議”已經不可能。該村以黨員代表會議形式決定“一事一議”,將12元糧食直補款扣除后,每人再交納3元。由于農民工大規模外出,不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甚至就連鄉村治理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社會價值觀的變化
在一個沒有發展、交通不便的鄉土社會,民風相對純樸,更容易出現利他主義行為(文建東、李欲曉,2004),更有利于合作行為的出現。農村改革前的農村顯然是一個相對封閉,民風純樸的鄉村社會,有著互助合作的傳統。經過長期思想政治灌輸教育,農村甚至形成了一種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充分尊重和維護個人的正當利益,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倡導“把國家、集體利益放在首位”,并強調“當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利益”。它降低了計劃經濟實施的制度成本,有助于動員農民參加農村大規模集體行動,也有利于動員型合作和強制型合作的推進。而那些個人利益取向的行為和做法,則時常遭到整肅和批判,個人合理利益和訴求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正視和重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壓制。隨著改革推進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這種過于強調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逐漸受到了來自現實的嚴峻挑戰。
與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相比,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利己主義,并肯定追求個人利益的正當合理性,在這一過程中,個人利益訴求得到強化,甚至極度膨脹起來。盡管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并以誠信為基礎,但其從未離開過欺詐、造假等機會主義行為。在農村改革進程中,隨著經濟活動范圍的擴大,極端機會主義做法得以大行其道,致使傳統價值觀逐漸趨向瓦解,并導致了村民聯系的迅速減少、農民行為原子化和傳統組織的衰落。這不僅使得農村動員型合作和強制型合作變得更加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自發型合作和自愿型合作難以實現。而這種社會價值觀層面的沖突,也是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
四、促進農民合作的對策討論
綜上所述,當前促進農民合作的相關對策基本上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因應社會經濟生活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直面農民大規模外出的現實,通過政府能力建設、組織制度建設和文化資源建設克服農民合作困境,從而改變農民的合作預期,激發農民的合作意愿,增強農民的合作能力,具體來說如下:
首先,以政府能力建設促進農民合作。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階段,隨著農業稅的廢除和大量惠農政策的出臺,農民與國家利益沖突的體制性原因已經基本消除。但政府公信力相對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并給農村合作帶來一定消極影響。鄉村干部能力不足,隊伍老化,觀念滯后,個別人甚至存在一定的經濟問題,這不利于甚至是阻礙了農民合作能力的提升。因此,著眼于提高政府,尤其是鄉鎮的公信力,增強其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對于促進農民合作能力提升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次,以組織資源建設促進農民合作。除了村兩委和農村能人之外,農村還有一些德高望重、公益心強的老黨員、老教師、老退伍軍人、老村干、老村民“五老”人員。如果把他們組織發動起來,將會大大增強農民的合作能力。以安徽省宿州市大營鎮為例,作為一個農業型鄉鎮,該鎮也曾同樣面臨公益事業停滯,農民生產生活不便等現實問題。自農村稅費改革后,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自2006年秋起,鎮委鎮政府充分發動“五老”人員,調動群眾積極性,成立了16個農民修路協會,并很快籌集到了修筑公路所需要的資金。這表明,即使是那些經濟不發達、財政極端拮據的地區,仍有很多辦法促成農民合作。
最后,注重道德文化建設,增強農民合作的文化基礎。市場經濟強調利己,但也注重互惠。當前應結合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大力倡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新型集體主義價值觀,以文化道德建設約束“經濟人”行為,特別是機會主義行為。盡管強制型合作可以降低組織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是社會治理的必要手段,但在道德建設基礎上,使合作成為人們的自發行為和資源行為,則可以實現社會經濟更為協調的發展。
[1]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2]常偉.鄉鎮政府轉型:基于農村公路建設視角[M].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3]賀雪峰,魏華偉.中國農民合作的正途和捷徑[J],探索與爭鳴,2010,(2).
[4]羅興佐.農民合作的類型與基礎[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
[5]羅興佐.治水:國家介入與農民合作[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6]羅澤爾,李建光.中國經濟改革中村干部的經濟行為[M].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
[7]邱夢華.中國農民合作的研究述評——簡論農民合作的定義與分類[J].調研世界,2008,(8).
[8]宋圭武.合作與中國農民合作[J].調研世界,2005,(2).
[9]文建東,李欲曉.市場經濟與利他主義、利己主義的界限[J].中國軟科學,2004,(2).
[10]吳思.中國農民何以“不善合”[J].讀書,2001,(10).
[11]于建嶸.人民公社動員體制的利益機制和實現手段[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
[12]趙蓓蓓.給我國4700萬留守婦女一個支點[N].人民日報,2010-7-13.
[13]鐘云華.農民合作的條件:岳陽井塘灌區個案[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責任編輯:楊黎源
F321.4
A
1008-4479(2012)05-0053-06
2012-07-04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政府主導型農地大規模流轉問題研究”(12CJY052)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湖南省農村公共產品非政府供給研究(2011225B)”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受到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Scott Rozelle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的啟發,作者感謝安徽大學張德元教授、潘林老師的所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但文責自負。
常偉(1974-),男,安徽碭山人,管理學博士,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農村發展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