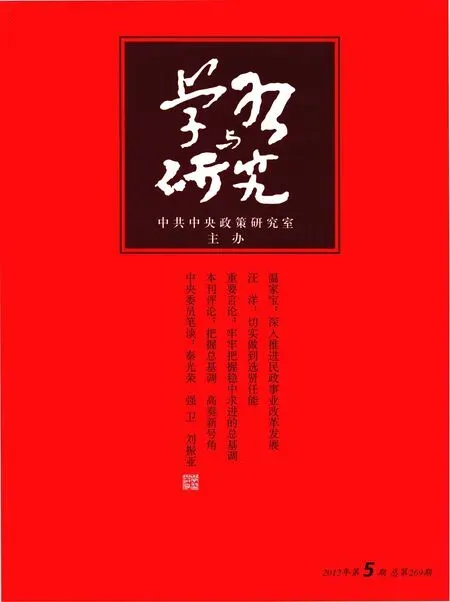材料、事實與反思:有關沈光文的“一樁文化史公案”——兼與潘承玉先生商榷
樂承耀
(寧波市行政學院,浙江 寧波 315012)
沈光文在臺灣傳播中華文化的歷史地位,早已被海峽兩岸的學者所認同。紹興文理學院的潘承玉教授在2005年“海峽兩岸越文化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中,提交過《越地三哲與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論文中提出“沈光文:中華文化在臺灣系統傳播的開創者”的觀點。時隔二三年,潘先生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和《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相繼發表了《神話的消解:詩史互證澄清一樁文化史公案》、《真相、遮蔽與反思——關于一樁文化史公案的后續考察》,一反其原來的觀點,說沈光文是“卑卑無足道的人物”,在臺20年中除了罵鄭氏政權外,就是想“投誠清廷”,晚年“極為熱心和賣力地充當滿清‘赤子’的角色”,是一個“半路投清的變節遺民”。他還認為,三百年來之所以把沈光文推到“臺灣文獻初祖”的地位,是由于全祖望的“回護”,另外的原因是“同鄉情節和政治關懷”,正是這些原因,出現了沈光文的“造神”運動。事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對一些是非曲直應該怎樣認識?本文談一些看法,以與潘承玉先生商榷。2012年是沈光文誕辰400周年紀念,筆者謹以此文紀念這位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作出重大貢獻的先人。
一、沈光文在臺是“二十余年”,還是“三十余年”?
沈光文到臺的時間,在臺灣文化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海峽兩岸學者對此做過研究。沈光文在臺二十余年還是三十余年,是早于還是晚于鄭成功到達臺灣?潘承玉先生將此作為“澄清一樁文化史公案”的重要內容來看待。他認為沈光文到達臺灣的時間是康熙元年(1662年),按此推算沈光文在臺灣20余年,“沈光文絕沒有早于鄭成功收復臺灣前十年左右即到臺灣”。他在“康熙元年底因投誠清廷發生意外到臺灣,未曾早于鄭成功收復臺灣前十年左右到臺灣,已斷無半點可疑。”“沈光文到達的準確時間在臺灣已為明鄭所有的康熙元年(底),而且是因為向清廷投誠生意外的結果。”浙東史學名家全祖望則“采信了‘鄭成功收復臺灣后與沈光文相見’為正確,而把‘康熙元年壬寅沈光文到臺灣’判定為錯誤”。并提出沈光文在辛卯(1651年)或壬辰(1652年)到達臺灣,其目的是“對沈光文回應招降之舉的曲為回護”。
綜觀上述引文,可見潘先生有三層意思:一是沈光文在康熙元年(1662年)到臺灣,是鄭成功收復臺灣以后。二是沈光文因投誠清廷發生意外而到臺灣。三是全祖望的《沈太仆傳》是沈光文先于鄭成功十年左右到達臺灣的依據所在,其目的是為沈光文投誠清廷“回護”。
對于潘先生的上述觀點,筆者不敢茍同。在此,就有關史實談點看法。
研究歷史人物要實事求是,這就要從事實出發,詳細占有材料,從事實中形成觀點。對于這點,潘先生在他的文中也有提到。他說:“從事古代文史研究必須一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將感情和政治考慮擯棄在外,否則即使出于‘善意’考慮,也將在嚴重歪曲歷史的同時大違‘善意’之初衷。”看來,潘先生盡管提到從事古代文史研究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但他自己并沒有這樣做。只要考察有關文獻,我們能夠看出潘先生的說法是違背客觀事實的。
按潘先生的說法,沈光文到達臺灣的時間是“康熙元年”(1662年),是“在鄭成功攻占臺灣后第二年”,在臺二十年余。但有關史料否定了這種說法。這在沈光文的《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及其好友季麒光的《沈斯庵詩序》中有答案。這兩篇序刊在季麒光的《蓉洲詩文稿》之中。該書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卷首有沈光文等人所作序文。沈光文《序》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沈光文在《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中說:“先生與余海外交也。憶余飄泊臺灣三十余載,苦趣交集,則托之于詩。”明確表明作者在臺灣30余年。季麒光,字圣昭,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臺灣府諸羅縣縣令,是沈光文的“海外知己”,他的《蓉洲詩文稿》中,詩與沈光文“倡和過半”。沈光文的這位“海外知己”在他的《〈沈斯庵詩〉敘》中也云:“余自甲子冬月渡海,僦居僧舍,即晤斯菴先生。見其修髯古貌,骨勁神越,雖野服僧冠,自非風塵物色。叩之,知為四明舊冏卿,當酉戍以后播遷鎖尾,卒乃遁跡海外,以寄其去國之孤蹤者也。與之言,則咳吐風生,議論云發,如霏玉屑,如瀉瓶水。當是時也,焚撞燈熒,雨窗煙冷,坐對午夜,若遇素交,及各出所著詩文相指示,并縱談宗旨內典、諸家外史,多所證可。在斯庵三十年來飄零番島,故人凋謝,地無同志,以余非聾非瞽,能伸紙濡毫,略知古今遺事,遂不我遐棄,忘年締好。”“冏卿”指太仆寺卿。因沈光文曾任太仆寺少卿,故稱之外“舊冏卿”。酉戍指乙酉、丙戌年(即順治二、三年,1645~1646年)。季麒光在“敘”中,除敘述兩人交往及詩文的切磨以外,也明確提到“斯庵三十年來飄零番島”。“斯庵”為沈光文號;“番島”即指臺灣島。季麒光與沈光文是同時代人,且有詩文交往,是為直接材料。沈光文本人及季麒光的《序》都明明白白地說沈光文在臺三十余年,應該是可信的,也是最權威的說法。
潘先生之所以提出沈光文在臺二十年余的說法,可能是沒有看過季麒光的《蓉洲詩文稿》。據《蓉洲詩文稿選輯》出版說明記述,季麒光的著述流傳并不廣,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著作逐漸佚失。乾隆十七年,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時,包括季麒光的《臺灣雜記》、《蓉洲文稿》、《山川考略》、《海外集》等在內的38種著作已被列為“邑無藏版,亦少懸簽,年代未遙,散失過半”的圖書之列。20世紀六十年代,臺灣著名學者、編輯出版家吳幅員先生,在《臺灣輿地匯鈔》一書的《弁言》中也指出,除季麒光的《臺灣雜記》外,其他的《臺灣郡志稿》6卷、《山川考略》1卷、《海外集》1卷、《蓉洲文稿》1卷,“惜均已佚”。至今,季麒光的相關著作,諸如《蓉洲詩文稿》僅在上海圖書館可以看到,另外廈門市圖書館有《蓉洲文稿》的手抄本,2005年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李祖基研究員作了編輯整理,并由香港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潘先生在沒有見到季麒光的《蓉洲詩文稿》的情況下,就匆忙提出沈光文在臺二十年的觀點,這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如果潘先生讀過沈光文《題梁溪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后,體會一下沈光文本人“憶余飄泊臺灣三十余載”說法,我想他是不會輕易提出沈光文在臺二十余年說法。
如果筆者上述論點成立,余下的兩個問題,應能迎刃而解。既然沈光文在臺30多年,那么康熙元年(1662年)到臺灣的說法是不可能的。沈光文作《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的時間為“康熙丁卯”。“康熙丁卯”,為康熙二十六年,即西歷1687年,按此計算,減去30多年的話,應該是1657年(順治十四年)以前,一般認為是辛卯(順治八年)或壬辰(順治九年),即西歷1651年或1652年。這里已經十分明確說明,沈光文是先于鄭成功十年左右到臺灣,在荷人統治下艱辛地傳播中華文化,其他的不少資料都有記載,沈氏確在鄭氏到臺之前已在臺灣。
潘先生在文中也多次引所謂沈光文的《東吟社序》:“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蘋至斯”,因此認為“沈光文乃在康熙元年底因投誠清廷發生意外到臺灣,未曾早于鄭成功收復臺灣前十年左右到臺灣,已斷無半點可疑”。《東吟社序》刊在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二十二《藝文三》之中。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纂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離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的“康熙丁卯”(1687年)近60年時間。沈光文與季麒光的《序》為直接材料,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且康熙間的《蓉洲文稿》等文獻并沒有《東吟社序》的記載;而近60年后的《東吟社序》,盡管序沈光文之名,其史料價值就低了,因為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畢竟是乾隆時的史料。對于《東吟社序》,臺灣的不少學者,諸如臺灣大學教授盛成就有疑問,盛成認為《東吟社序》“極其澆亂”、“酌改過甚”,“略潤太多”,“似乎值不得作為研究沈光文之直接材料”。當然,一些學者還認為“壬寅“為”壬辰“之誤。高一萍就說:“今所見‘壬寅’,乃‘壬辰’之誤。因辛卯后當為壬辰也(即永歷六年)”。
至于全祖望《沈太仆傳》中提到的“公居三十余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和“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的說法,隨著沈光文在臺30余年的命題成立,可以肯定沒有錯。其實,全祖望曾托人去臺取過沈光文詩文,他在《沈太仆傳》中說:“會鄞人有游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他在《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詩集序》中亦說:“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也,為予言太仆之后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于東寧,乃以太仆詩集為屬,則果抄以來,予大喜,為南向酹于太仆之靈。”這表明全祖望見過沈光文的詩,可能也見過沈光文的《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序》,因此有“公居臺三十余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說法。他在《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詩集序》中亦有“太仆居海外者四十余年,竟卒于島”的說法,這里的四十余年是包括在金門等地的10余年及在臺的30余年。全祖望的沈光文在臺30余年說法,與沈光文的本人及其友人季麒光說法一致,應該是可信的,而潘先生對全氏的指責,極不可取。
二、沈光文是“變節遺民”,還是順乎歷史?
潘先生認為沈光文是“向清廷投誠”者,“極為熱心和賣力充當起了滿清新朝‘赤子’的角色”。是“一個半路投清的變節遺民”。筆者認為這個觀點也值得商榷。
沈光文的晚年,處于康熙的中期。康熙皇帝是政風卓越的政治家,為形成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高峰“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基礎。清朝初期,中國的版圖之所以能得以最后奠定,康熙帝功不可沒。此外,康熙借鑒歷代王朝的興亡盛衰的經驗和教訓,勵精圖治,廣納賢才,發展生產,振興文化,崇尚儒學,使得社會經濟發展,民心安定,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特別是收復臺灣,振興中華文化更是名垂千古的佳話。
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一個部分。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他所實行的和大陸一致的典章制度和府縣制政治統治以及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鄭成功據守臺灣所打的旗號是“反清復明”,而事實上則保持著一時的割據局面,鄭成功去世后,其子鄭經、其孫鄭克塽保持其割據局面,海峽兩岸的對峙,阻礙了大陸與臺灣的聯系。當時,在全國統一已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情況下,鄭氏集團想“復明”實際上已是不可能。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任何“反清復明”的名義所進行的活動是不實際的,這種分裂、對峙的局面已經不適時宜,只能日益成為全國統一的障礙。統一臺灣,是正義、進步之舉措。一些有愛國之心的士人,都會順應時代潮流,支持康熙帝統一臺灣決策。而康熙帝統一臺灣后,即于次年開海禁,這一政策措施,有利于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和發展,有利于臺灣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臺灣商人開始向福建、廣東等地輸出糧食,向寧波、蘇州、上海、天津、盛京等地輸出蔗糖。
康熙中期前后,清廷的文化政策也有調整。康熙帝大力提倡漢族的傳統文化,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賢之學,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紛紛仿效。為加強思想領域的控制,康熙帝于康熙十三年(1673年)起使用懷柔政策,以科舉考試辦法,網羅江南的知識分子,還以“特種”政策,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開“博學鴻儒科”,以羅致江南漢族知識分子,其中“名儒”朱彝尊、湯斌、毛奇齡等,分別授以編修、檢討等官職。康熙十八年修明史,開局于內東華門外。在此背景下,明史監修徐元文,邀萬斯同和萬言北上修史。
面對變化了的形勢,富有良知、愛國之心的知識分子必定會與時俱進,順乎歷史潮流,希望祖國繁榮富強,融入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從傳承中華文化出發,支持康熙帝文化活動。曾經持節不仕的一些明遺民開始轉變其對清廷的原來看法,參加了清廷組織的一些文化活動,諸如朱彝尊、毛奇齡、黃宗羲、萬斯同。比如,浙東的著名學者黃宗羲、萬斯同對清廷的態度有所改變,萬斯同以“布衣”參與修明史。黃宗羲云:“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給。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誠不朽之盛事也。”黃宗羲對清廷修明史是贊同的,他雖拒絕朝廷詔聘,不入史局,但也采取靈活方式,在行動上表現出對清廷修史舉措的理解與支持,把其父黃尊素所著的明朝《大事記》、《時略》和他自己所作的《三史鈔》、《續時略》以作修史之用。黃宗羲還肯定危素修《元史》。危素為元遺民,元亡后,原打算以身殉國,僧大梓勸阻危素要忍辱負重,編修《元史》。黃宗羲為此說:“元之亡也,危素趨赴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黃宗羲肯定危素的做法以道出其內心深處的想法。并以此支持萬斯同修明史。“及明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梁啟超十分理解黃氏的想法。他說:“前明遺獻,大率皆惓惓于國史,梨洲這條話,足見其感慨之深。他雖不應史館之聘,然館員都是他的后學,每有疑難問題,都是咨詢他取決。”黃炳垕在《黃梨洲先生年譜》中亦說:“公長于史學,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有《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于公。”上述事例表明,康熙開《明史》館是成功的。梁啟超說:“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的成功。因為許多學者,對于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只得勉強將就了。”
作為江南士人,沈光文同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他體驗了明亡的痛苦和悲哀,于是懷念故國故君,他的詩作中不少是思念故國的,帶有強烈的思明情懷。明末遺民常以月為明之半壁江山,以“思月”、“聽月”為思明的象征。比如,沈光文的《望月》、《中秋夜坐》等。還有一些是直接懷念祖國的,他的《葛衣吟》就表達這種情感:“歲月復相從,中原起戰烽,難違昔日志,未能一時蹤。故國山河在,他鄉幽恨重,葛衣寧最棄,有遜魯家傭。”沈光文服明衣冠,行明禮儀,都表明對故國的思念。在當時的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都具有所謂愛國和捍衛傳統文明的氣節。
但從康熙中期起,隨著臺灣復歸,國家統一的進一步鞏固和康熙帝的懷柔政策實施及文化政策的調整,作為遺民故老的沈光文,他的愛國情感內涵有所變化。面對現實,他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毅然放棄傳統的對“一家一姓”的愚忠原則,對清廷的態度也有所變化,支持康熙的統一臺灣等政策。不僅不反對同道出仕為官,而且對一些清代官吏保持良好關系,和施瑯、姚啟圣等人有所交往,與諸羅縣令季麒光、臺灣鎮標左營濟南韓有琦等詩人有所唱和。他曾給季麒光較高評價。說他奉調赴臺任諸羅縣令后“往來籌劃,日無停晷”,“凡民間利弊有所指劃,不為強力者少屈,以一宰而綜三邑之煩賾,條議詳明,為臺灣定億萬年之規劃”。為此,沈光文以季麒光為“海外知己”。并對康熙帝統一臺灣更有所認識,因此稱康熙帝為“圣天子聲靈赫濯”,使“島上效吳越之歸誠,使從前未通之疆域,悉入版圖,設立郡縣”。自臺歸入版圖后,沈光文除肯定了康熙統一臺灣的業績,所寫文章也用“康熙”年號,這與黃宗羲有相似之處。在《東吟社序》最后,沈光文題啟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梅月、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庵氏題,時年七十有四”。康熙二十四年,即公歷1685年。他的《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中,其題啟為“康熙丁卯孟夏望日,甬上年家教弟沈光文題,時年七十有六也。”康熙丁卯為康熙二十六年,即公歷1687年。用康熙的年號,表明沈光文承認清統治的合法性。這些都說明沈光文是順乎歷史潮流的。
對于沈光文晚年的所作所為,必須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考慮,不應該把是否支持新朝作為裁決是非的依據,應該看其是否順乎歷史潮流,是否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否有利于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沈光文在早期對清廷持反抗態度,直到晚年,在不仕前提下對朝廷采取了靈活的姿態,他對康熙帝統一臺灣加以肯定,參與創辦“東吟詩社”和臺灣的文化建設,不但不能對他拋棄原有的立場加以指責,而且應該肯定其順應歷史發展,融入祖國大家庭的行為。潘先生說沈光文“投誠清朝”,是“半路投清的變節遺民”,這種說法是不足取的,也違背歷史事實。如果因此而對沈光文加以否定,那么,當時江南漢族知識分子都應該被否定。黃宗羲、萬斯同支持清廷的《明史》編纂難道是“晚節有疵”?這似乎是一種苛求。既然黃宗羲、萬斯同對清廷的修《明史》的支持能得到理解,為什么對沈光文支持康熙統一臺灣,與諸羅縣令季麒光等清朝官吏創辦“東吟社”就要苛求?筆者認為,沈光文經歷反清復明到康熙帝的政績和清政府執政的合法性認定和支持,這絕不是“投誠清朝”,是“半路投清的變節遺民”,而恰恰是沈光文是面對變化了的實際所作出的明智與正確的選擇,是順乎歷史潮流,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
這一點,可與潘先生對待紹興籍的姚啟圣的平臺及其事奉“新朝”的認識相比較。同樣是事奉“新朝”,但潘先生認為,姚啟圣結束兩岸對峙,有利于造福民生,實現國家在文化教育上的大統一,應該“大書特書”。潘先生還認為,鄭成功及其后裔在臺灣的統治,只是個“割據的分裂的地方政權”。其理由是:其時,已經完成了明清易代的轉變,完成了明代萬歷以后,女真貴族的漢化過程,從關外“野蠻”的“異族”轉變為一個相當“正常”的中原大一統政權。潘先生還從地理正統觀和道德正統觀的視角出發,認為“三藩之亂”前后,清王朝“已成為中國正統所在,成為中華文化的合法繼承者和當代象征”。那些曾經持節不仕的明代遺民,諸如朱彝尊、陳維崧、屈大均、顧炎武等,紛紛放棄當初的立場。這些都“反映了清廷正統的地位的被接受與社會歷史的變動和人們所向”。正因為如此,潘承玉先生說:“在民族矛盾已經不再成為最迫切的社會問題的時代,明鄭勢力以反抗民族壓迫為借口繼續存在,使兩岸人民繼續‘不遑寧處’,這種分裂對峙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合時宜。姚啟圣順歷史適時地結束了這一局面,也幫助臺灣和中華文化母體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大團聚。”筆者認為,潘先生這一立論原則,應該同樣適用于沈光文,而不能徇私偏曲而隨意割裂。
既然清朝在當時是“中國正統所在,成為中華文化的合法繼承者和當代象征”,姚啟圣事奉“新朝”是合符情理的事,他為清廷平定臺灣,結束兩岸對峙局面是“順應歷史”,是“中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那么沈光文在晚年對清廷的支持,歌頌康熙帝平定臺灣是“圣主”,用清代的年號,結交施瑯、姚啟圣、季麒光等清廷官吏,為何卻“不適合時宜”?如果說沈光文是“變質遺民”,那么,與他處在同一社會背景,且其行為取向極為相似的姚啟圣又算什么呢?潘先生用雙重的標準來看待同一時代的歷史人物,這決不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以歷史的態度考察人物,應將歷史的人物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之下,以客觀事實作為其依據,客觀地、具體地、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給予功過評述,切不能主觀臆斷,進行無端的指責和貶低。
三、肯定沈光文地位,是“造神”還是符合實際?
沈光文在臺30余年,傳播中華文化富有業績。他播下愛國精神種子,推行大陸教育制度,進行漢語教育,給臺灣留下了一批漢文文獻,被推崇為“海東文獻初祖”,并以杰出才藝、參與首創詩社,成為臺灣文學始祖。對于他在臺灣系統傳播中華文化和對臺灣文化建設開拓性的貢獻,自康熙以來,一直得到肯定。潘承玉教授也曾在其論文中,也認為沈光文“給臺灣留下了第一批漢文文獻”,“數十年實際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是第一個比較系統、比較全面地將中華文化播到底層原住民者”,由于他的“雄于詞賦”的杰出才藝,而“成為臺灣文學的始祖”,為“蠻荒的臺灣帶來中國文學的曙光和芬香”,是“傳播中華文化事業取得了臺島第一人的成就”。當時,潘先生曾給沈光文戴上一頂頂桂冠。但時隔二年卻把沈光文說成“變節遺民”、“卑卑無足道的人物”。并認為把沈光文推許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的第一個播種者”、“臺灣孔子”,這是“一個天大的謬誤”,而且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是由于“造神運動”,除“學風不夠嚴謹”外,其另外原因是“同鄉情節與政治關懷”。筆者對此不甘茍同。
對于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的業績,許多文章都有闡述,潘先生在他的《越地三哲與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中也有記述。其主要論點,上面已有引用。這些都是客觀事實。由于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中的貢獻,獲得了人們的贊揚和謳歌。事實表明,這一舉動是符合實際的,并不是什么“造神”。其實,說沈光文與鄭成功“同垂千古”,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種子散播在臺灣島上第一人”、“臺灣文化的啟明導師”、“臺灣孔子”,見仁見智,是學術上的問題,或者是民間的說法。正像潘先生說沈光文是“卑卑無足道的人物”、“變節遺民”一樣,這也是他的自由。奇怪的是潘先生在二年左右時間內,在同樣材料的基礎上又沒有新的材料占有,更無令人信服的分析,竟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南轅北轍的觀點,使人感到納悶:這究竟是為什么?
提出沈光文是“現代孔子”的是臺南善化鎮(古為加溜灣社)民。他們的目的是肯定沈光文在善化教育業績,是為了紀念,因為沈光文長期在善化從事教育,造福于善化民眾。臺灣《中國時報》記者陳炎生就提到:“你聽過‘臺灣孔子’的故事嗎?明末遺臣沈光文在荷蘭據臺時期飄海來臺,歷經荷蘭、明鄭及滿清三個時期,也曾因作詩寫賦得罪鄭經而不得不隱性埋名在善化鎮教導生蕃漢文,這位在連橫所著《臺灣通史》書中有臺灣文獻鼻祖的文人的文人個性,也將他升格為神。”“在善化百年老廟慶安宮的后殿,沈光文也被善化鎮民尊奉為‘臺灣孔子’及文神,每年進入考試季節,總有大批善化子弟將準考證影本擺放在其神像前膜拜,祈望庇佑金榜題名”。為紀念這位偉人,因此,每逢中秋節,善化鎮民總以具有鄉土風味的“牛車之旅”、沈公詩詞朗誦及征文比賽等形式紀念這位“臺灣孔子”,就是因為沈光文“后半生與善化結緣,因此善化鎮為紀念他,將他去世地點附近的一條道路為光文路,也設有光文里及光文橋”。明確指出善化民眾對沈光文神格化的認識應該“見仁見智”。他認為“沈光文升格為神是否適當也見仁見智,尤其臺南市延平郡王祠也供奉太仆寺卿沈光文的牌位,因此,沈公神格化僅是供后人追思崇拜而已。”這些事實表明,提出“臺灣孔子”觀點的是臺南善化民眾的民間行為,潘先生無須吹毛求疵,嚴苛推究。
潘先生還認為,對沈光文的“無限神化”,其主要原因是“同鄉情節”與“政治關系”。他說:“考察沈光文神話建構的不同歷史階段,我們會發現,同鄉情節和政治關懷確是其中貫穿始終的兩大因素;正是在自覺不自覺地虛美鄉賢和滿足政治需要的雙重作用中,或雙管齊下,或合二而一,沈光文‘臺灣孔子’的神話才被建構而成。”潘先生的說法不完全對。我們試作分析。
最早推崇沈光文的不是寧波同鄉,而是他的好友季麒光。季麒光,字圣昭,江蘇無錫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康熙二十三年,臺灣設立1府3縣,隸福建省,季麒光任諸羅縣令,與沈光文為“海外知己”,他的著作《蓉洲詩文稿》中詩,與沈光文“倡和過半”。作為沈光文好友季麒光十分了解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中的貢獻,他在《跋沈斯庵雜記詩》中,把沈光文寓臺灣,比作杜甫去巴蜀,柳宗元謫嶺南,并且說:“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又始有文矣。”其中可能有些過譽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出沈光文在當時臺灣文壇、詩壇的地位以及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中的貢獻。
對于沈光文業績加以推崇的還有鄧傳安、連橫等人,他們也不是寧波鄉賢。鄧傳宗為江西浮梁人,曾任鹿仔港(今屬彰化)同知,道光八年升任臺灣知府,動員民眾歷經四年建成書院,以“文開”為名。他在《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中云:“傳安前以沈太仆表德名書院,已為從祀朱子權輿;況宜卒葬俱在臺,子孫又家于臺,今雖未見《詩庵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概然慕焉”。連橫在他《臺灣通史》中亦云:“光文居臺三十余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于兵火,惟光文獨保天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為初祖。”鄧傳安、連橫都不是寧波同鄉,他們同樣給沈光文文化建設成就、地位給予較高評價,怎么能說是同鄉“造神”呢?
至于說到“同鄉情節”,推崇沈光文的成就和業績,并無不可。悠久深厚、意韻豐富的浙江文化傳統,是歷來賜予浙江的寶貴財物,也是開拓未來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近年來,浙江及全省各地,都在搞文化研究工程,弘揚浙江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一個重大項目是“名人研究”,比如,“浙江名商研究”。難道研究、推崇浙江的歷史人物也是在“造神”?
寧波、紹興同樣如此。這兩個城市是我國首批被命名為歷史名城,在中國歷史上涌現出一大批名人。正因為如此,寧波文化工程中就有“歷史名人研究”項目,沈光文也在其中。寧波鄉賢歷來重視對沈光文的研究和資料搜集。清乾隆年間,全祖望就托人到臺搜集沈光文的詩27首,編入《續甬上耆舊詩》卷十五《從亡諸公》之二中。并寫《沈太仆傳》和《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詩集序》。在《沈太仆傳》中贊揚沈光文“海東文獻,推為初祖”。上世紀50年代后,寧波旅臺同鄉會十分重視對沈光文的研究。臺北寧波同鄉會理事王善卿于1953年發表《同鄉旅臺之鼻祖——斯庵先生傳略》。臺北寧波同鄉會在廣泛搜集沈光文事跡和遺著的基礎上,編寫了《臺灣文獻初祖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于1977年由臺北寧波同鄉月刊社出版。在寧波同鄉會關心下,經過地方人士熱心奔波,于1979年建立了沈光文紀念碑。自90年代起,臺北寧波同鄉會及沈光文后裔到故鄉寧波尋根。寧波當地也掀起研究沈光文熱潮,1992年還召開了沈光文誕辰38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臺灣文化初祖沈光文》、《開發臺灣、名垂青史——紀念沈光文誕辰380周年》、《臺灣文學拓荒者沈光文》等文章。寧波鄉賢研究沈光文,不但是肯定其臺灣文化建設中貢獻,更重要的是弘揚浙東的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寧波城市品質。這怎么能說是把沈光文“無限神格化”,是“造神運動”呢?對此,作為學人應該有寬闊的胸懷和視野,要以寬松、寬容的態度,來理解和對待歷史人物。
紹興是具有2500年歷史的歷史名城。自古以來,名人輩出,名流薈萃。為提高紹興的城市品位,紹興多次召開越文化學術研討會,對紹興城市和紹興名人進行研究,諸如陸游、章學誠、蔡元培研究等,這不能當作“造神”吧?也因此,潘承玉先生身處紹興,開展紹興名人研究,高推紹興籍人士如姚啟圣,這也無足為怪。姚啟圣,字熙止,號憂庵,明清間紹興會稽馬山姚家棣人,生于明天啟四年(1624年),十三歲中秀才,后歸清,于康熙十年,晉福建總督。康熙二十年,鄭克塽繼位,姚上疏以為收復臺灣時不可失,薦施瑯為水師提督平臺。潘先生認為,“文武雙全”的姚啟圣在清朝收復臺灣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更認為:“康熙皇帝和施瑯,前者是決策者,后者是這一軍事行動的直接指揮者。”但是“姚啟圣的作用可能更為重要。他是亙立他們二人之后、之間的一個人物,是清朝收復臺灣的提倡者、策劃準備者和兩位主要軍事統帥之一,是臺灣與中華文化母體首次正式團聚的設計師。”姚啟圣“促成臺灣歸于中原大一統政權是中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某種程度上比鄭成功收復臺灣還重要。”潘先生以為,姚啟圣的作用遠遠超過鄭成功和康熙帝,這就把姚啟圣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用他自己的原則來衡量,這豈非也成了“造神”?
潘先生還認為,對沈光文的“政治關懷”是導致沈光文“無限神格化”另一個原因。他說:“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臺灣而言,與遷臺國民黨政府高層多為浙江人,甚至最高領導人為沈光文寧波同鄉有關”。這一點,需要具體分析。
所謂“政治關懷”,應從季麒光說起。清初的季麒光對沈光文的評述,是鑒于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和地位,或者是兩人間的友情;同樣,作為地方官吏,這也是清統治者的執政需要。邀請沈光文參與清初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活動,這是季麒光執行康熙帝的文化政策,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同樣,20世紀50年代后所出現的研究沈光文,也與當時實際情況有關。
歷史記載,1894年的清廷甲午戰爭失敗和次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祖國寶島臺灣割讓給日本,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日本殖民者的統治,使臺灣人民受到剝削、壓迫和凌辱長達半個世紀。1945年,臺灣重歸于中國主權的管轄下,但光復的臺灣面臨著一系列問題。戰后的臺灣經濟文化必須進行重建。“在文化上,一方面對殖民主義文化進行掃蕩、摒除,一方面則著手恢復和重建中華傳統文化。”1945年11月18日,臺灣省籍知識分子游彌堅、許乃昌、楊云萍等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其目的是“鏟除殖民地統治所遺留下來的遺毒,創造民主的臺灣新文化”。開展促進國語運動,宣傳祖國文化,努力肅清日本殖民文化的殘余。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居臺灣。為進一步清除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影響,揭穿少數搞臺灣獨立的民族敗類的陰謀,臺灣當局于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進行所謂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70年代初達到高潮,為保存傳播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做了一些工作,使臺灣出現了重視傳統、回歸傳統的趨勢。比如,請托一批愛國學者,以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周憲文教授為首,組織了臺灣研究學者、專家,自1957年至1972年歷經15年時間,先后有1000余名專家參與了編輯《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深刻揭示臺灣歷史發展變遷,特別是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血緣關系和不可分割的文化淵源關系。叢刊編者楊亮功曾在“跋語”中說:“從本刊整個資料中,更可看出臺灣對于祖國在民族歷史上、文化上、政治上實有不可分割之關系。”另一位主要編纂者吳幅員也說:“臺灣之于大陸,不論從地緣以至血緣,都屬一體,雖先后遭受異族侵凌的影響,而這種‘血濃于水’的相互關系,永難磨。”推崇臺灣文獻的初祖沈光文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沈光文作為開發臺灣的早期人物之一,且在臺灣留下了詩文,對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及對臺灣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對于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中”必定會有一定的地位。沈光文傳等5篇被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8輯、第162種之中。這一時期,臺灣的一些學者也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如臺大教授楊云萍1954年發表了《臺灣的寓賢沈光文》,另一位臺大教授盛成也在1960年至1961年先后發表《沈光文自薦詩文中自述》、《史乘與方志中的沈光文資料》、《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傳》和《沈光文公年表及明清時代有關史實》等。通過對沈光文在臺灣弘揚中華文化的記述,這正好證明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血緣關系和不可分割的文化淵源關系。這就表明,對沈光文的文化成就的宣傳,是符合當時保存、傳播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并不是當時臺灣當局最高領導人的“政治關懷”,更不是“最高領導人為沈光文同鄉相關”。
潘承玉先生還說:“當我們高唱沈光文是‘臺灣文化的啟明導師’,是‘臺灣孔子’,以證明臺灣與中華文化的緊密關系時,有沒有想到,這實際上極大地縮短了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史,從而實際上極大割裂了臺灣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呢?”這可能是潘先生的善意推測。沈光文在臺灣文化建設中的貢獻對于社會發展起過某種進步作用,正好說明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淵源關系,正是體現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史,其個人作用絕對不能否認。其實,我們在講沈光文的臺灣文化建設中作用時,也并沒有否定其他人在文化建設上貢獻。至于有學者提出沈光文是“臺灣文化啟明導師”和民間所說的“臺灣孔子”,這是個人的看法,也沒有必要過于較勁。
[注釋]
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匯編》第642頁,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年。(民國)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諸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