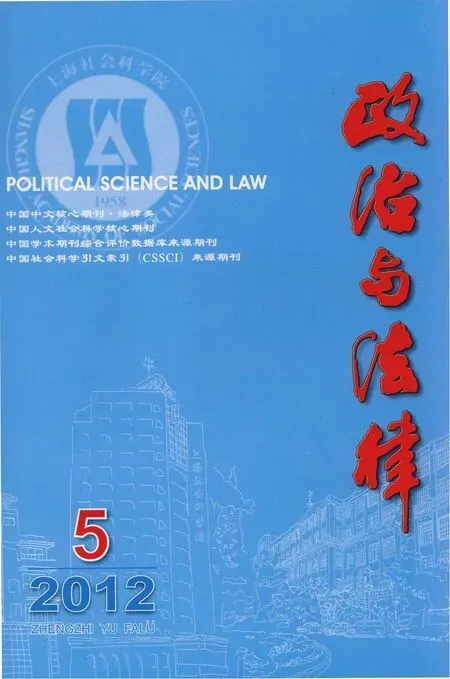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品格證據之比較研究
宋洨沙
品格證據是英美證據法中一個非常重要又極為復雜的問題。品格證據排除規則從產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其內容不斷得以補充、擴展,普通法與制定法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例外情況,但總體來說,英美證據法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品格證據的適用還是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除非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否則不得在庭審中提出與被告人品格相關的證據,以此作為證明其有罪的理由。1在大陸法系國家,幾乎很難找到被告人品格證據適用的規定,但這并不意味歐陸國家刑事司法中沒有涉及這一范疇。大陸法系國家通常很少刻意回避關于被告人的品行特征的證據材料,并非表示其認同品格能夠用來證明犯罪,也不是在有意識忽略可能對被告人產生不公平偏見的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兩大法系對待品格證據的不同態度不僅僅源于不同的訴訟理念與制度,更是植根于其不同的社會背景與傳統。例如,在作為大陸法系發源地的法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與被告人品格相似的內容體現在其對“人格調查”的規定中。在此,本文基于法律移植必須關注其背后隱含的深層次因素的視角,擬以英美法系的品格證據規則與法國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人格調查的具體適用規則為例,對兩大法系國家對待這類證據的不同觀念進行比較分析,以期梳理其背后存在的深層次原因。
一、概念梳理:品格(Character)與人格(Personnalité)
品格證據一詞來源于英美法中的“characterevidence”,也有學者稱之為“品行證據”、“品性證據”、“性格證據”。但是,無論漢語的品格、品行還是性格,都無法與英美普通法與制定法中的character完全對應。從詞源上看,character出自希臘文,本意為雕刻。根據《心理學大詞典》的記載,最早使用character的古希臘科學家兼哲學家C.theophratus從對人的日常生活觀察中發現,個體的character與社會道德相聯系,于是從道德角度理解和使用character的做法就一直沿用下來。2猶太教哲學家布貝爾認為,品格一詞的希臘文原意是烙印,作為一種特殊紐帶連接一個人本質與他的外表,是介于他為人的統一性與他的系統行為模式、處事態度之間的這種特殊聯系。換言之,品格就是在個體與外部世界發生相互作用時,對人的行為和態度起到穩定、持續支配作用的一種內在的精神或道德品行。3
在英美法系國家,無論普通法還是制定法都沒有對品格證據這一概念作出明確、具體的界定。在關于品格證據的種種說法中,有的定義重點在于闡述品格的含義,如在布萊克法律詞典中,品格證據被定義為“關于某人一般的人格特質或傾向性以及在一定社區范圍內公眾對個人人品、道德方面評價的證據”。4有的定義以英美證據法中運用品格的相關規定為基礎,如依據某人的品格或行為傾向來證明他在特定場合以特定方式行事為目的的證言或文書。還有的按照品格證據的內容進行界定,如著名英國證據法學家Murphy認為,品格證據中“品格”有三種含義:其一,某人在其所在社區環境中具有的名聲、聲譽(reputation);其二,某人以特定方式實施某種行為的傾向性(disposition);其三,某人過去曾經經歷的特定事件,如曾被定罪等(previousconvictions)。5目前,這種界定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
在法國刑事訴訟程序中,雖然有與被告人品格相關的證據規定,但通常并不使用這一表述,而以人格來表達相似的含義。當然,這里的人格并不等同于倫理學中以道德規范標準來評價人的品格高尚或低下。而與英美法系品格證據的范圍相比,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人格調查所包含的內容更加廣泛,不僅僅涉及被告人品格特征、處事風格、行為傾向,還涵蓋其個人經歷、家庭生活、教育情況等客觀方面的因素。例如,法國預審法官對被告人進行的人格調查,包括其業余嗜好、習慣、生活經歷、前科等。
雖然“品格”與“人格”不完全等同,但兩者的實質性核心內容是相通的。法語中的人格personnalité一詞由拉丁文persona演化而來,后者是伊特魯立亞語或古希臘語的派生詞,本意為面具,即在戲劇中為了表現不同人物的角色與身份,應劇情需要繪制的臉譜。6從其詞源來看,人既有外在向他人表現出來的特點,亦有一些深藏于內、未顯露于人的特點,這就是人格基于“面具”的理解。著名人格理論家SalvatorMaddi將人格定義為,一個穩定的特性和傾向系列,它決定著人們的心理行為,包括思想、情感、行為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并且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從心理學角度,人格是個體在各種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內在動力組織和相應行為模式的統一體。7柴爾德(Child)認為,人格使個體的行為在相似情境下區別于其他個體行為,并且在時間上保持一致性的比較穩定的內部因素。對于這種界定,漢普森(Hampson)指出,柴爾德的定義中有四個尤為重要的關鍵詞:穩定的、內部的、一致性和區別于。當我們提及某人的人格時,我們假設此人的人格理所當然地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在關于人格的種種理論中,有一點很重要,即大部分觀點都認為人格存在于個體內部,個體的行為部分由其人格所決定。8因此,人格是由較為穩定的、內在的因素構成的,這些因素影響著個體的行為,使之在大致上保持始終如一,與個體的行為獨特性、傾向性息息相關。簡而言之,人格可以說是個體獨特的、有異于他人的特質模式及行為傾向的整合體,表現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持續性的思維、情感和行為方式。鑒于人格與一定的行為傾向性的關系,通常認為,可借此來預測人在一定情境中的待人接物、為人處事的風格。
經過梳理,不難看出,品格與人格在基本特性方面有其相似之處,主要在于:其一,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個體表現出與他人相區別的獨特性,如思維方式或行為風格等;其二,這兩者都可以被視作一個人內在本質與他的行為之間的聯系;其三,兩者都具有相對持續穩定性,但并不否認其可發展性;其四,雖然個體的品格或人格是在人的自然生物特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影響著個體的發展道路和方式,但對個體發展方向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正是由于個體的品格或人格具有上述特性,才使一個人的心理面貌與行為特質的形成與發展有跡可循。個體與生俱來的先天特征,受到后天環境因素累積的影響,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獨特的、有別于他人的內在與外在特質,這種內在的心理特質與外在的行為傾向在個體中是有機統一的。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逐步積累經驗與常識,一個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德性品格的反映。換言之,個體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往往是比較穩定的。這樣,品格或人格與個體外在表現出的某種行為方式的傾向性的關系,就成為人們對個體進行分析判斷的基礎。因此,品格與人格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盡管如此,由于文化傳統的差異,英美法系的品格證據規則與法國刑事司法中人格調查的具體適用存在極大差異。
二、樣本考略一:英美法系的品格證據規則
英美證據法規定了在刑事審判中排除被告人品格證據的一般性原則。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與被告人品格有關的證據仍然可以在法庭中提出,立法和判例中都存在一些例外情況。對此,已有諸多論著。在此,筆者僅以品格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為樣本,說明英美法系對被告人品格證據的謹慎態度。
從歷史上來看,在普通法證據規則形成的較早階段,品格證據規則的雛形就已經存在。訴訟一方不得將對方的其他不良行為作為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這是一個古老的普通法原則。17世紀,英國的Hampden案件與Harrison案件被視為品格證據規則產生的起點。在這兩個案件中,法官都拒絕采納被告人以前的不良行為作為證據,正如其中一個法庭所陳述:“我們不能忍受任何侵入人們的生活軌道,以尋找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回答的證據的行為。”9在廢除星法院(StarChamber)專斷獨行的糾問式程序的改革中,1695年英國《叛國法令》(TheTreasonAct)提出了禁止控方對沒有列在起訴書中的被告人的其他犯罪提出指控的條款:為了避免犯人因為需要當場回答各種問題而感到吃驚或混亂,對任何人都不得采納或考慮起訴書中沒有明確提出的外部行為的任何證據。1762年福斯特(Foster)就叛國罪討論了外部行為證據排除這一話題,他對于這一情況所作的論述在隨后被多次用來引證:在刑事訴訟中與爭議事實無關的各式各樣證據的排除規則,是基于合理的邏輯與普遍正義而建立的。任何人都沒有義務冒著生命或自由、財產或名譽的危險,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立即回答與他生活相關的每個情節……也許在這種情況下不必要再次做出明確的規定,因為普通法基于自然正義原則,已經使得類似的規定在其他情況得以體現。10隨著立法與司法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關注,該法令確立的原則逐漸擴展為這樣一種規則:即不得使用具體行為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的犯罪傾向。英國刑事司法早期案例指出,傾向性證據規則的存在意義在于保護被告人避免遭受過去犯罪證據帶來的嚴重偏見影響。11但是,在這一時期,盡管人們已經意識到應當對被告人品格證據適用采取審慎的態度,法官在庭審中仍然可以對品格是否具有證據價值作出自己的判斷。
直至19世紀初期,品格證據規則才正式在普通法中得到完整確立。1814年,法庭在Rexv.Cole一案中用現代術語陳述了品格排除規則:在對一項聲名狼藉的犯罪進行起訴時,被告人承認他曾經與其他人實施過這類犯罪,或者他具有實施這種行為的傾向性的供述,不得采納為證據。1894年Makinv.AttorneyGeneralforNewSouthWales一案中,法官對有關被告人品格證據的采納規則作出經典論述,在以后的許多案件中經常被引用。該案赫塞爾法官(Herschell)認為,雖然在這個案件中相似事實證據具有可采性,但作為基本原則,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相似情況的證據不可采。赫塞爾法官對過去相似事實證據的一般規則作出了論述:毫無疑問,控方不得提出表明被告人過去曾犯有起訴書指控之罪以外的犯罪的證據,以得出“被告的品格與過去犯罪行為證明正是他可能實施了正在被審判的這一犯罪”的結論。排除這類證據的原因主要在于,過去所發生的事實不一定與現在有關,并且,采納這種證明實施犯罪的傾向性的證據可能造成不公正之判決。因此,傾向性證據的證明力必須達到能夠使事實裁判者認定是故意犯罪還是偶發事件的程度,才能避免對被告人造成的不公。
美國的品格證據規則最初是基于英國當時既有的實踐經驗發展起來的。如果說英國對品格的禁用是出于“一個人應該因其行為受到審判,而不是因為他是誰”的傳統根源,那么,在美國早期排除品格證據的案例是出自“陪審團可能僅僅依據被告人以往不良行為將其定罪”的擔憂。在美國普通法中,關于品格證據一個重要的判例是Peoplev.Molineux一案。紐約上訴法院對被告人未被指控的不良行為的證據效力做出說明:根據適用于刑事審判的一般規則,國家不得證明被告人犯有起訴書以外的任何犯罪,無論是作為單獨處罰的依據,還是作為被告人在當前被指控的犯罪中有罪的證據。12而在另一經典的闡述普通法傾向性證據規則及其重要原理的Michelsonv.UnitedStates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追隨普通法傳統的法院幾乎一致同意,不允許控方憑借任何類型的關于被告人劣行品格的證據來確立其有罪的蓋然性。13控方不得展示被告人過去的法律糾紛、具體犯罪行為或者在其鄰里中的壞名聲,即使這類事實可能在邏輯上具有說服力,能表明從習性來看被告很有可能就是實施犯罪的那個人。排除這種調查并非由于品格不具有相關性,相反它能對陪審團產生巨大影響并可能強行說服陪審團對擁有不良品格記錄者預先作出判斷,拒絕給予其一個公平的機會為被指控的事實作出辯護。
隨著成文法的逐漸發展,英美法系國家開始出現一些成文法律來規范品格證據的關聯性與可采性問題。最早在制定法中對品格證據加以規定的是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依據該法,當被告人按照本法成為證人時,不得對其提出任何傾向于表明被告人以前實施了被指控犯罪之外的罪行,或者曾經因此被指控、定罪,或者是證明其不良品格的問題,即使提出該問題,被告人可拒絕回答。14英國2003年《刑事司法法》對品格證據的規定更加詳細。該法第101條規定了被告人不良品格的可采情況,并明確除法律列舉的情況外,其他不良品格的證據均應排除。15即使在法律規定可采的范圍內,如果法院根據被告人的排除證據申請,認為采納某一項證據將會對訴訟程序的公正性產生不利的影響,應當將其排除時,法院不得因該證據與控辯雙方爭議中的一項重要事實有關或被告人對其他人的品格進行攻擊而采納該證據。在制定法中,最有典型意義的是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04條關于被告人品格特征、犯罪或其它行為的規定。該條明確規定,某人的品格或其品格特征的證據被用以證明此人在特定場合下會實施與其品格或特征相符的行為時,不具有可采性。16法律之所以在刑事審判定罪階段排除品格證據,并不是由于這類證據不具有實質上的關聯性,而是在將品格證據的證明價值和其他價值因素相比較后,權衡不同利益考量得出的結果:即在多數情況下,品格的證明價值較小,而它所帶來的不公正的偏見、混淆爭議點、誤導陪審團、不當拖延、浪費時間的危險性更大。
當然,在普通法與制定法中也存在品格排除規則的例外情況。例如,在下列情況下,法律允許控方提出證據對被告人的品格進行質疑:被告人自己主動提出證明自身品格特征的證據,或者被告人攻擊控方、控方證人、被害人的品格,或者攻擊同一案件中的其他共同被告人。17對上述情形例外規定可以采納被告人品格證據是因為那些情形等于將品格置于爭議之中,它將會引起法庭對其品格的交叉詢問,即為控方提出相應的品格證據予以反駁打開大門,這就是所謂的“開門原則”。在此情形下并不會導致訴訟程序的不公正。
同時,這些品格證據可以采納的例外情況亦受到嚴格的限制,即控方即使可以提出被告人具有不良品格的證據,也必須遵守諸多規則,不能超出法律限定的范圍。而這種對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質疑,也只能在極為有限的目的下發揮作用。假設在故意傷害罪中,被告人提出被害人暴虐品格的證據以表明被害人是尋釁者,則控方可以提出被告人有暴力傾向的證據予以反擊。但控方反駁被告人的證據受到明確限制,他只能提出被告人“同一性質”品格特征的證據。例如,如果被告人指出被害人具有暴力品性特征,控方就只能提出證明被告人有暴虐性格的證據,而不得使用沒有責任感、不誠實之類的品格證據來反駁被告人。
另外,在品格證據排除規則的例外中,普通法與制定法亦對證明一個人品格的方式作出嚴格的限定,而不允許在庭審中自由地對被告人的品行加以評述。傳統上,根據女王訴羅頓一案(Rv.Rowton),只能使用名聲形式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的品格,其后才逐漸將意見證據及被告人在其他場合特殊行為證據納入證明方式之中。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05條規定,如果關于某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被允許采納,可以用名聲或意見證言的形式予以證明。在對品格證人進行交叉詢問時,法庭可以準許對相關的某人特定行為的具體實例進行詢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辯方決定傳喚品格證人證明被告人的良好品行,控方在對其進行交叉詢問時,證人所作出的證言只能以他了解被告人的名聲為目的,而不得用來證明被告人在目前正在被審理的案件中有罪,或者證明被告人還犯有其他罪名。控方對特定行為的詢問需要遵守兩個限制性條件:其一,對于要詢問的特定事項必須存在一定的事實基礎;其二,這些特定事項必須與案件中存在爭議的品格特質相關。因此,即使控方在交叉詢問品格證人時提及被告人的特定不良行為,也不得用來證明被告人在特定場合會依照這種品格行事的傾向性,而只能驗證證人的可信性。法官可能會對陪審團作出限制性指示,提醒陪審員控方對品格證人詢問時提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品格,其唯一目的是為了評估該證人是否真正了解被告人的名聲,陪審員只得在此目的下考慮這種證據。18
綜上,在英美法系國家,如果沒有普通法與制定法規定的例外情況,原則上被告人的品格特征、行為方式、前科或其他特定具體行為的證據在定罪階段是不應當出現在事實裁判者面前的。即使在特殊的例外情況下,普通法與制定法也都謹慎地對這類證據適用的范圍和方式作出限制,旨在時刻提醒裁判者對品格證據保持警惕的態度。
三、樣本考略二:法國的人格調查
由于傳統原因,大陸法系國家在證據立法上與英美法系國家有很大不同,一般沒有關于證據制度獨立、專門的法典。英美法系對品格證據、前科惡行的證據或者某人以往生活中相似信息的證據進行排除的規定,也很難在大陸法系的法律中找到。通常認為,大陸法系的證據制度只關注信息的證明價值,對待被告人品格證據的態度也是如此。證據如果有證明價值,理所當然可以采納。有學者認為,大陸法系對待這類信息的態度,表明其缺乏對“個人習性信息的證明價值與導致不公平的偏見”的平衡的考慮。19事實上,這種批評也許有失公允。以發現案件真相為基本出發點的大陸法系國家,側重于通過證據的調查和收集程序判斷證據是否有證據資格。因此,通常證據的證明價值不是由立法者而是由法庭來決定的,從這點來看,似乎法官對被告人人格的調查也就無可厚非了。
在法國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中,“人格”(personnalité)一詞頻頻出現,貫穿了刑事程序的始終。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第81條,在審前程序中,預審法官依法進行其認為有益于查明事實真相的一切偵查活動。為此目的,預審法官可親自或者委托司法警察,或者委派任何有資格的人對受審查人的人格、家庭狀況、物質與社會狀況進行調查。但在輕罪案件中,調查不具有強制性。并且,預審法官應命令對當事人進行醫療檢查或醫療(心理)檢查,這也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可通過說明理由的書面請求要求進行檢查或采取其他有益措施。在審判程序中,刑事訴訟法第331條及第444條分別對重罪法院、輕罪法院庭審中與被告人品格相關的證據問題作出規定,證人可對被告人受到指控的事實、被告人人格及品格道德提供證言。
即使在一些快速處理程序中,人格也是必不可少的調查因素。如在以筆錄進行傳喚通知與立即出庭程序中,被告人或其律師可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97-1條,請求法庭命令進行任何其認為有益于查明被指控的案件事實及其人格的偵查行動,法庭拒絕這一請求時,應當作出說明理由的裁定。如果檢察機關決定實行簡易程序,對被告人人格充分查明是必要的前提條件。20如被告人在事先承認犯罪的情況下出庭,法官也要依據犯罪行為人的人格認可檢察官提議的刑罰。21另外,法國對性犯罪行為人與暴力犯罪行為人實行信息化處理的全國犯罪記錄,在考慮是否有必要保留原來登記的信息時,亦要分析犯罪行為人目前的人格狀況。
有英美法系國家學者對法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人格調查進行了研究。通過旁聽法庭審判,他們指出,與英國、威爾士相比,法國法官在處理被告人品格證據方面有很大不同。研究者認為,在法國庭審中,更多時間和資源被用于展示品格和生活方面的證據,對這類證據的關聯性的定義更加寬泛。這種證據在案件中,尤其是在最嚴重的案件中更加普遍和明顯。該學者在一個關于法國辯護律師的實證研究中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一起謀殺案件中,被告人在醉酒的狀態下將一個鄰居擊打致死。令人吃驚的是,在重罪法院的第一天審理的第一個小時中,庭長一直在詢問被告的嗜好及閑暇時的活動習慣,而一點都沒有提及與案件的事實有關的問題。庭長開始核實了被告在一家無線電遙控汽車模型俱樂部的會員身份,又談論了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被告人生活方面的種種瑣事,如個人經歷、家庭生活、教育情況、服役情況、工作、夫妻關系、業余愛好等。隨后兩個俱樂部的會員也作為證人出庭,證明被告人是個有責任感的人,曾一早到達俱樂部幫助他們安裝比賽障礙物,并等到很晚幫他們拆除該障礙。
以上描述的庭審并非例外現象,法庭詳細、深入調查與案件直接事實無關的被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法國重罪法院審判中很常見的一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相信有關被告人人格的信息,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被告人會發展成為實施某種行為的人。在庭審中,差不多第一件事,就是庭長通過詢問被告人繪制出其生活和品格的一幅圖片。在可能的情況下,庭長讓被告人本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如果被告人不愿意,庭長則推動庭審發展。庭長還可以使用卷宗中的書面陳述構建其對被告人作出的評價。案件的卷宗在法國刑事程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個單獨的部分是關于被告人前科、服役、生活情況及品格等信息的。在重罪案件中,大部分的這類信息是審前通過警察在預審法官指示下進行的“人格調查”得到的。庭長則從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中尋找這種信息,除了將被告人的陳述與卷宗內容相驗證外,通常還會有同事、朋友、家人、老師等作為品格證人出庭作證。在重罪法庭,同樣有很多時間用于聽取這些證人證言,一個重要的品格證人甚至可作證30分鐘。而來自于獨立或中立的證人,如老師、社會工作者等人的證言的分量更重。另外,一個對被告人更加不利的因素,是與被指控犯罪無關的前科證據的廣泛使用。被告人以前的刑事犯罪記錄總是在庭審之初就被提起,并且成為接受詢問的話題。更甚者,法庭還會參考被告人被涉及的其他案件,即使其沒有被指控或定罪,如曾被控共同犯罪或僅僅“為警察所熟知”。有時,在指出被告人曾有犯罪記錄后,法庭還會詳述以前的犯罪與現在被指控行為的相似之處,或者庭長認為可說明被告人品格方面的情況。除此之外,心理醫生與精神病醫生在閱讀卷宗、進行智力及人格測試、與被告人會面的基礎上做出的評估,同樣可作為證明被告人品格異常的證據來解釋被告人的行為模式。22
在法國,重罪法庭庭長指揮庭審,并有廣泛的自由處分權,可采取其認為有利于查明事實真相的一切措施,包括聽取被告人、證人或專家的陳述。一位經驗豐富的庭長曾提出,這樣做是因為在移送重罪法庭75%的案件中事實已經調查清楚,一般沒有爭議,在這時,對品格的分析旨在理解被告人行為的產生過程。如果事實仍有爭議,庭長也可采取另外的措施。但研究人員發現,即使案件事實存在極大分歧,庭審依然如此進行。而在輕罪案件與違警罪案件中,雖然幾乎沒有品格證人或專家證人,但記載于警察例行筆錄中的被告人與證人的陳述,仍然包括關于被告人品格、前科的詳細材料,可用于對事實作出的審判。正如一句法國的法律諺語所說,“我們審判的是人,而非事實”。
四、成因分析:品格證據與人格調查適用之差異
英美法系國家認為,雖然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證據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它可能造成的偏見遠大于其自身價值,因此,原則上在刑事審判中應當將其排除。在大陸法系國家,司法實踐并不刻意回避與被告人品行特征、先前的定罪記錄、其他不良行為相關的證據。例如,在法國法庭審判中,關于被告人的性格、嗜好、生活經歷等材料不會被排除在法官的視野之外。當然,這并非表示大陸法系的法官會過度關注這類證據所帶來的品格推論。事實上,與英美法系相比較,歐陸國家對品格推論理解的范圍較為狹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于以前的犯罪記錄對定罪的影響。因此,法國刑事訴訟同樣認可某人的犯罪記錄不應當用來作出其實施了當前被指控犯罪的推論。刑事訴訟法條例部分第16條規定,對受審查人的人格、家庭狀況、物質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醫療檢查、醫療-心理檢查構成受審查人人格卷宗,其目的只是客觀地向司法機關提供對受審查人過去及現在的生活模式進行評估的材料,并不具有對犯罪事實作出結論的功能,也不得作為有罪證據使用。雖然如此,卻并不影響這類證據繼續呈現在法官面前。
與英美法國家刑事司法的“被告人應當因其犯罪行為受到審判,而非因其本身”基本理念相反,作為傳統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國,更注重的是法庭對“個人”的審判。正如貝爾納·布洛克在《法國刑事訴訟法》序言中所講,審判“人”的刑事法院,應當發現并深入調查“人”之人格,以便更好地對是否有罪作出評價,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確定最適合其人格、最適于其矯正的刑罰或處分與再教育措施。23但是,對于對抗制傳統的普通法國家來說,從刑事審判之初就如此寬泛地使用品格證據顯然不妥。在英美法系國家的研究者看來,至少有三個問題是十分令人詫異的:其一,如何解釋法國對于品格證據關聯性的理解——為何極少區分良好品格與不良品格、與定罪相關的品格證據及與量刑相關的品格證據?其二,為什么在法國更多時間和資源用于展示品格證據?其三,法律模式的問題。這種審理程序并不僅僅在于發現個體的被告人為什么會做出某種犯罪行為,而是在于從更深層次找到在普通公民生活遵循的一般標準的背景下,誰在何時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為什么要做。這種調查的目的已經超出了對犯罪進行審判的范圍。正如法國預審法官在審前會見被告人時所表述的一樣:法官將會依照事實對你進行審判,但亦依據你的人格。
可以看出,法國刑事訴訟程序對待被告人品格特征、行為方式這類證據的態度,與英美法系品格證據的適用規則存在極大差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受到大陸法系傳統的深刻影響。因此,要想回答英美國家研究者的三個問題,必須從法國具有的訴訟程序的典型特征入手。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由于歷史原因,現代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立法限定證據證明力的規則表現出抵制情緒。在16世紀至18世紀,歐洲大陸建立了法定證據制度,法律對訴訟活動中各種證據的證明力作出了預先規定,嚴格規范法官對證據的取舍。法官只能機械地依照法律規定的標準認定案件事實,沒有判斷與使用證據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與當時的糾問制訴訟模式相適應的。在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法定證據制度遭到了強烈批判。因為如果法官能夠獲取兩個目擊證人的證言或者被告人的口供,則可宣判被告人罪名成立,通常來說取得被告人的供述顯然比尋找目擊證人更為容易,這種僵化而嚴苛的證據制度成為刑訊逼供滋生的溫床,并造成大量的誤判。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推動司法制度的改革,在證據制度方面,自由證明模式取代了死板的法定證明模式。人們認為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明價值無法預先確定,并且相信事實裁判者具有對證據進行主觀評判的能力。由此,大陸法系國家逐漸形成了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的證據評價模式,前者傾向于整體主義模式,后者傾向于原子主義模式。即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證據的證明力依每個特殊案件的情況而定,某一證據的證明價值需要在與其他所有證據的相互作用中體現出來,單獨一項證據的證明價值難以斷定,對事實的認定應當基于證據的總體判斷,規定統一的認證標準和普遍性的排除規則已顯得不合時宜;英美法系則承認單項證據的證明力,在裁判者認定事實的過程中設置了更多干預,要求禁止采納某種證據材料或者將其限定在特定的目的之下才可使用。對于與被告人品格有關的這類證據應當如何評價,按照大陸法系的思路,某一特定證據的證明價值依賴于個案的具體情況,被告人的品行特征、行為模式等信息是否有價值,理所當然也應在個案中具體分析。
第二,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審判組織模式不同。大陸法系實行參審制,即一體性審判模式,法官和參審員共同對案件事實及法律問題作出判斷,討論決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所有證據在統一的庭審中同時提出。而在普通法刑事訴訟程序的兩段式審判中,法官負責解決法律問題并對陪審員進行指引,陪審員在法官的程序性指導下獨立判斷指控事實是否成立,在定罪后由法官裁定具體刑罰。定罪、量刑兩部分是分開的,作出裁判所依據的不同類型的信息材料也因此得以區分。這也正是達馬斯卡論述的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刑事審判程序傳統上不同之處的關鍵部分。大陸法系國家在法庭退庭進行評議前,與量刑相關的證據、與定罪相關的證據都已經提出,這樣排除可能導致推定有罪的品格證據是不現實的。24
第三,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程序追求的價值目標不同。英美法系重視程序的正當性,相比發現案件真相,更加注重案件真相認定的過程,強調程序本身的公正。證據調查的對抗制模式,使得雙方當事人都試圖以最大限度的保護自身利益的方式調查和使用證據,各方當事人會選擇他希望提交給法庭審理的爭議點和證據,這時證據往往只服務于某一方當事人。在劍拔弩張的法庭辯論中,雙方都在全力爭取裁判者的信任并竭盡可能質疑對方的證據,這使人不禁擔心由外行人組成的陪審團可能會由于缺乏經驗而受到控辯雙方辯論策略的迷惑或誤導。因此,普通法國家更重視呈現在事實裁判者面前的證據的資格限制,英美證據法的特征之一就是對事實裁判者分析證據活動的控制。對證據的調查應當更加謹慎,證人作證的內容也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以防止陪審團受到某些信息材料的影響形成不當的偏見。而大陸法系更強調實體真實,要求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盡可能的發現事實真相。在職權主義的訴訟構造中,法官可積極主動調查證據,甚至突破控辯雙方提交證據的范圍。通常來說,只要調查、收集、提出證據的手段是合法的,能夠證明事實真相的一切信息都可以加以運用。法官在了解案件事實時享有較大的自由,法律極少對法官獲得信息材料的范圍予以限制。比較典型的,如依據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10條,庭長享有自由裁量權,依此權力,庭長本著榮譽與良知,可采取其認為有利于發現事實真相的一切措施。并且,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外,法官可依據任何形式的證據認定犯罪。法律并不規定一種規則強制法官必須依此認定某項證據是否完備、充分,法官可以完全自由判斷證據之價值且無需對其據以定案的證據證明力作出說明。25事實上,在另一典型大陸法系國家德國也有類似的規定。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為了查明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主動就對判決有重要意義的事實與證據進行調查,不受訴訟參與人的申請或者陳述的限制。法官必須對所有其可得使用的證據加以利用,包括由人事檔案引申出來的被告人個人資料。26追求發現事實真相的大陸法系職業法官占據審判的主導地位,是導致大陸法系國家對品格證據采取不同態度的重要因素。出于對專業法官的信任,人們認為其有能力理智地對待各種證據,并避免可能存在的偏見,使之同樣不會影響陪審員的判斷,由此,一般性證據排除規則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
盡管如此,法國關于人格調查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質疑。這是因為,一般認為,雖然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明確規定人格調查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定罪的證據,但由于在庭審之初已經出現對品格的描述,即使是專業的事實裁判者也很難準確甄別關于品格的種種信息。達馬斯卡認為,大陸法系國家對不良品格證據可以較為自由而寬泛地采納,其中一個因素是這些國家的職業法官是專業的事實決策者;但同時,他也質疑專業法官是否有能力排除可能帶有偏見性的信息。在大陸法系的一元化法庭中,事實認定者對某些證據信息的排除是否能表現出一種超俗的態度。他們是否可以對審判中提交的帶有偏見但有說服力的證據不加理睬?這樣的證據是否會在他們腦中留下絲毫影響?事實上,在大陸法系法官審判的過程中,對品格作為證據采用的態度已經超出了上述范圍。品格與被告人被指控罪名的相關性已經不是重點,人格調查成為法官從總體上考量個體犯罪成因的重要手段,而通過對品格證據的處理,傳達了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特殊社會信息。
第四,訴訟制度差異背后的文化、社會、政治因素。法國刑事訴訟關注的重點,并非人格與被告人定罪是否具有關聯性,而在于通過人格調查來表達國家與公民的特殊關系。對此,法國法學家安托萬·卡拉邦(AntoineGarapon)曾提出,兩大法系不同的法律文化,依賴于不同的社會模式形成個體與社會關系的不同概念。對人格進行司法調查的傳統,在法國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根據自1810年至1958年一直規范著法國刑事程序的《重罪審理法典》,預審法官可對受審查人的生活進行調查,以使“過去闡明現在”。理解法國刑事司法程序對品格證據的處理與適用,問題的關鍵在于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模式。與英美相比,在法國傳統文化中,國家這一概念是建立和維持民族認同感的關鍵。在舊制度中,教堂與貴族是社會權威體系中穩固社會服從關系和正統社會秩序的核心。但是,自從法國大革命后,政治思想家開始致力于重建某種服從關系的社會構架,即將國家作為建立既定秩序的正統性的核心。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共和國”這一理念被反復灌輸,在其中就包括建立了一個抽象的高度標準化“法國公民”概念。這種國家的政治傳統提供了一個積極正面的法國公民模式,而法官正是依照這種形象來對個人進行審判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刑事審判之前他就要對被告人的生活、品格進行系統調查。27
五、結語: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的特性既不屬于典型的大陸法系,也不屬于英美法系。在我國,雖然立法沒有對品格證據的性質、地位予以明確規定,但是一些法律與相關司法解釋中卻以不同的形式體現了與被告人品格相關的內容,在實踐中辦案人員也會廣泛接觸到這類證據。在偵查階段,辦案人員可借助品格特征、行為傾向縮小偵查范圍,鎖定犯罪嫌疑人。在適用強制措施時,被告人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身危險性,有助于辦案人員對其采取合理的強制措施。在審判階段,無論是在定罪還是量刑中,法官都有可能獲取這類信息。如我國刑法的一些條文中,被告人曾經實施的一些特定行為是需要檢察機關提出證據證明的事實。28
總體來說,我國傳統法治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強的道德意味,通常某個人的倫理品性、道德品質和社會評價是其作為人的整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傳統刑事司法中,品格也是事實裁判者或糾紛解決機制看重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目前,我國刑事被告人品格證據的適用主要問題在于:雖然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中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一貫表現”、“人格”、“品德”等方面的情況是公安、司法機關辦案考察的重要因素。另外,長期以來,受職權主義的影響,辦案機關往往更傾向于收集與調查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因此重視不良品格的證據,容易忽視被告人良好品格的證據。立法與實踐的脫節使得品格證據在適用時產生很多問題。
通過對兩大法系國家對待品格證據的不同態度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想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品格證據適用規則,決不能完全照搬英美或大陸法系的一套做法,這是由于我國的訴訟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社會、文化因素與兩大法系都存在顯著差異。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吸收一些先進的理念和經驗,在將其本土化的過程中建立起適合我國訴訟制度的品格證據規則。
一方面,英美法系國家對品格證據的謹慎態度值得我們借鑒,源于這類證據有可能帶來誤導裁判者、造成不公平的偏見、降低訴訟效率、浪費司法資源以及侵犯訴訟參與人的隱私權等問題,品格證據的微弱證據價值,遠遠抵不上對刑事審判中認定案件事實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從這點來看,我國雖然是由專業法官進行審判,但是職業法官在評價證據信息方面是否確實優于非專業人員,能完全做到公正無私,以職業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感,并沒有科學的依據。另外,目前我國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法官的素質也是參差不齊,尤其是基層法官的專業化水平還有待提升,總體而言,法官隊伍整體的專業化程度仍不理想,制定一些規則來限定其評價證據的自由裁量空間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關于品格證據在定罪階段的具體適用,首先應當明確提出“與被告人的品格相關的證據不得用于證明其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這一原則性規定。
另一方面,大陸法系的人格調查,有助于事實裁判者全面地理解犯罪行為人,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認識犯罪行為的產生及后果。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從人格入手來預防犯罪,在犯罪發生后采取措施防止再犯。品格特征為裁判者作出適當的量刑提供了更為客觀的依據,有助于更有針對性地對犯罪行為人進行矯正、改造,使之重新回歸社會。因此,法官在對已經構成犯罪的被告人裁定刑罰時,要充分考慮被告人的個體情況與其他案件或者同一案件的其他被告人相比較有何區別,進而選擇更為合適的量刑種類和量刑幅度。這樣,品格在量刑中的適用亦有助于使量刑程序更加科學、準確,加強了量刑判決的公正性和說服力。
我國現有的立法并沒有明確區分審判中的定罪和量刑階段,但是目前量刑程序改革為品格證據的適用提供了契機。具體來說,被告人的品格證據可以分為純粹的量刑證據與不純粹的量刑證據。大部分的品格證據都是純粹的量刑證據,與定罪無關。但仍有一小部分與被告人品行特征、行為實例有關的證據既涉及定罪問題,又涉及量刑問題。在被告人認罪案件中,法庭審理主要圍繞量刑的問題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可以將所有與定罪、量刑有關的被告人的品格證據一同提交法庭。但是,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法官不應當在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之前接觸到純粹與量刑有關的不良品格的證據,這是為了避免與定罪完全無關的證據影響法官的判斷。根據新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72條規定,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應當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法院。其中,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處理,即將純粹與量刑有關而與定罪完全無關的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證據材料單獨在一檔案袋中封存,直至有罪判決作出后再拆封處理。
注:
1當然,這種禁止性原則主要是針對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證據作出的規定。通常情況下,關于被告人良好品格的證據是允許提出的,因此本文討論的主要是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證據。
2韋曉:《漢語“人格”與“性格”的內隱概念及其心理結構的本土化研究》,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1年,第3頁。
3丁錦宏:《品格教育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頁。
4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Thomson West,595.
5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6.
6黃希庭:《人格心理學》,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7郭永玉:《人格心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8[美]M.艾克森主編:《心理學——一條整合的途徑》,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頁。
9Erik D.Ojala,Propensity Evidence Under Rule 413:The Need For Balance,77 WASH.U.L.Q., 1999,PP947-978.
10Foster,CROWN LAW 246.
11Jason L.McCandless,Prior Bad Acts and Two Bad Rules:The Fundamental Unfairness of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413 and 414,5 Wi l l iam&Mary Bi l l of Rts.Journal,1997,PP.689-715.
12Erik D.Ojala,Propensity Evidence Under Rule 413:The Need For Balance,77 WASH.U.L.Q., 1999,PP947-978.
13335 U.S.469,69 S.Ct.213,93 L.Ed.168(1948).
14參見Criminal Evidence Act 1898,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898/36/pdfs/ukpga_189800 36_en.pdf.
15參見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44/contents。
16參見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2012,ht tp://federalevidence.com/downloads/rules.of.evidence.pdf。17參見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2012、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18參見[美]羅納德·J·艾倫等:《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張保生、王進喜、趙瀅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81頁。
19參見[美]米爾建·R·達馬斯卡著《漂移的證據法》,李學軍、劉曉丹、姚永吉、劉為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20《法國刑事訴訟法》第495條,http://www.legi f rance.gouv.f r/af fichCode.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 71154。
21《法國刑事訴訟法》第495-11條,ht tp://www.legi f rance.gouv.f r/af fichCode.do?cidTexte=LEGITEXT00000 6071154。
22參見Stewart Field,State,Citizen and Character in French Criminal Process,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Vol.33,No.4,December2006,PP.522-46.
23[法]Bernard Bouloc,Procédure Pénale,Dal loz,2008,PP.3.
24M.Damaska,Propensity Evidence i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s,70 Chicago-Kent Law Rev.,1994,P55.
25參見《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53條、第427條。ht tp://www.legif rance.gouv.f r/af fichCode.do?cidTexte =LEGITEXT000006071154。
26參見[德]克勞思·羅科信:《刑事訴訟法》,吳麗琪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頁、第416頁。
27Stewart Field,State,Citizen and Character in French Criminal Process,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Vol.33,No.4,December2006,PP.522-46.
28參見我國《刑法》第201條、第264條、第274條等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