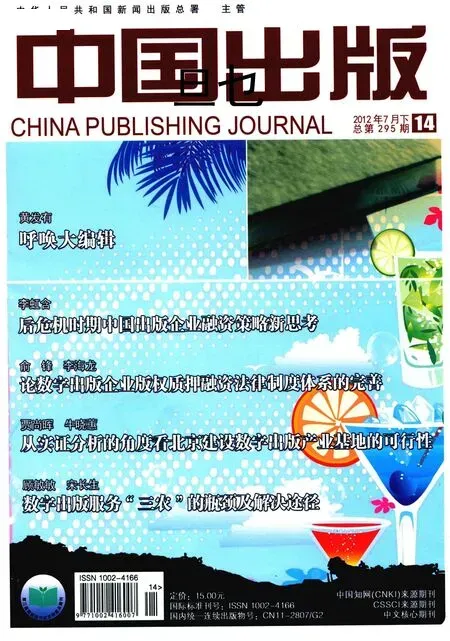呼喚大編輯 *
文/黃發有
2010 年9 月14 日,老編輯家范用先生去世,文化界、讀書界以各種形式進行紀念。朱農先生特撰挽聯,寄托哀思:“創辦讀書, 巴老鐫隨想。干校六記仿佛漫記西行, 歷史能不沉思?/首倡文摘, 傅氏傳家書。牛棚日志權當一生書籍, 理論應起風云!”此聯由書刊名組成,列舉了范用主持編輯出版的《新華文摘》、《讀書》兩本期刊和《隨想錄》《傅雷家書》《干校六記》《牛棚日記》《理論風云》《歷史的沉思》 以及重新出版的《西行漫記》《為書籍的一生》等引領一時讀書風氣的好書。隨著胡愈之、葉圣陶、陳翰伯、柯靈、趙家壁、巴金、陳原、范用等大編輯家紛紛謝世,出版界和讀書界應該對這一代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成長起來的大編輯家的出版實踐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反思,繼承并發揚其精神遺產,學習他們在飽經滄桑中不辱使命的人文情懷,在新形勢下培育開風氣之先的新一代大編輯。尤其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讀書界對這一代編輯家有極高的認知度,普遍充滿敬意,而中青年編輯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整體上有待提升。這種狀況和編輯這一為人作嫁的職業的特殊性有關,但是,隱身幕后并不意味著消極無為。因此,出版界人士更應該以他們為楷模,在片面追逐利潤的滾滾商潮前寵辱不驚,堅守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使命,立志成為站在時代高度上推動文化復興的大編輯。
一、先行者的墊腳石
大編輯不是一種“虛名”,而是一種高屋建瓴、大智若愚的大境界。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在回憶范用時,提到范用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四個不要”,即一是不要韜奮獎,二是不要編審職稱,三是不要“多得的住房”(他退出了按照規定分得的三套單元房中的兩套),四是不要遺體。[1]在編輯界,“四個不要”的范用堪稱無冕之王,他憑借自己的職業操守、奉獻精神和人格魅力確立自己的威信和影響力。他用一生的堅持詮釋了大編輯的真諦,即大編輯不是身份、地位、級別最高的編輯,也不是通過出版賺取最多財富的編輯。真正的大編輯應該是文化傳承事業中的橋梁,甚至是扎根于洶涌波濤與巉巖峻嶺之上的橋墩,用堅實的肩膀扛起絡繹不絕的通行者。巴金在給范用的題詞中寫道:“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溫暖的腳印里。”范用從中選取了“泥土”、“腳印”作為自己兩本隨筆集的書名,并宣稱:“我也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腳印里。”
大編輯必須具備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但大編輯不應事必躬親,更不應貪功起釁,他不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急先鋒,他充當的是舟橋兵和工兵的角色,為先頭部隊架橋鋪路,排除險阻,提供必要的保障。也就是說,大編輯的創新意識表現為一種腳踏實地的遠見,像開荒人一樣披荊斬棘,開辟出新的園地,為那些柔弱的種子提供肥沃的土壤。筆者非常喜歡趙家壁編輯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文學叢書》《中篇創作新集》的里封、環襯或包封上的那幅書標:“畫面上一位頭戴闊草帽的農民,在春天廣袤的田野里,左肩掛著谷粒袋,右手正在向條條麥壟撒播種子。”這幅取自國外藏書票的木刻版畫,“線條粗獷有力,含意深遠”,非常準確地概括了編輯職業的精髓——開墾和播種。[2]《讀書》創刊號“編者的話”里有言:“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敢于打破條條框框,敢于接觸多數讀者所感所思的問題。我們主張改進文風,反對穿靴戴帽,反對空話,反對八股腔調,提倡實事求是,言之有物。”這些具有明確針對性的編輯主張,力求打破思想枷鎖和陳言老套,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膽識。
大編輯不是一種特權身份,平等意識恰恰是激發編輯的創造活力的精神法寶。正因為人格上的無差異,人們才應該相互尊重能力和觀念的差異性,平等而自由地進行思想交流。針對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版界的官僚習氣,巴金不留情面地指出:“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關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3]過度強調等級觀念,就無法平等地看待作者、讀者和編者自身,在編輯觀念上以特權編者為核心,追捧特權作者的寫作習慣,迎合特權讀者的接受趣味,就忽略了廣大的普通作者和普通讀者。正因如此,大編輯需要有一種“小編輯”的自覺,即不濫用編輯權限,踏踏實實地做小事,譬如埋頭改正稿件中的錯別字。像范用就倡導大學者寫小文章,注重圖書裝幀的精美,甚至親力親為,設計言簡意賅的內容導讀和圖書廣告。在范用編的《愛看書的廣告》中,就收錄和介紹了魯迅、葉圣陶、巴金、施蟄存、胡風、趙家壁等大編輯親自撰寫的廣告文字。只有淡化等級觀念,小編輯才能成長為真正的大編輯,而不是成為靠某種特殊身份保駕的大而無當、好大喜功、自高自大的“大編輯”。
二、商海里的傳火者
編輯掌握著人類知識信息的選擇權,充當文化積累的守護者是大編輯自覺的價值選擇。在市場競爭日益劇烈的媒介環境中,編輯在對知識信息進行選擇、加工和優化時,必然要考慮產品的經濟效益,大編輯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決不會為了利潤而放棄信念,不會拋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出版流程中,根據圖書的預期銷量來決定一本圖書命運的市場審查機制,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確實,通俗化和商業化的趨勢正在不斷壓縮嚴肅出版物的空間。隨著商業意味的加強,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一些打著編輯策劃旗號推出的出版口號和出版炒作行為,與文化建設的相關性越來越遠。在暢銷與否逐漸成為通行標準時,越來越多的作者通過接受編輯的指令來獲得生存空間,以拋棄自己個性的代價來適應商業法則,最終成為批量復制的文化模特。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就被商業趣味的侵略性嚴重損害,就像加拿大一枝黃花之類的有害物種一樣,四處蔓延,輕易地突破生態安全的屏障,引發生態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對文化始終懷抱熱忱、擁有犧牲精神和敬業精神的編輯的存在,對于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就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在市場化語境中堅守人文理想,就要求出版機構在商業大潮中保持品牌優勢,利用自己的文化積累激活經典資源,同時發掘具有新品質的優秀之作,提升市場競爭力。短、平、快的暢銷書縱然粗糙而膚淺,但同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些文化產品與高品位的文化積累之作構成一種相互平衡、自然調節的關系。速效而速朽的產品的存在,恰恰烘托出了具有創造意義的精神產品的不可或缺。通過以書養書來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編輯策略。趙家壁對出版的難處抱著一種理解的同情,他認為:“如果出版商當不好,出版家也當不成了。”[4]在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機制中,必須靠利潤豐厚的產品來支撐那些賠錢的好書的出版。故作高深、遠離大眾的編輯不是好編輯,編輯不能不考慮產品的市場前景,出版的每本書都賠本的編輯絕不是好編輯,但是,指望每本書都能馬上賺錢的編輯是沒有人文情懷的商人。美國著名出版人希夫林曾在蘭登書屋旗下的潘塞恩出版公司工作30 余年,他出版過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杜拉斯的《情人》、薩特和波伏娃的晚年作品和米歇爾·福柯的學術著作,1990 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小型出版社——新新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具有思想性、藝術性和文化價值的圖書,他引用德國學者克勞斯·瓦格巴赫的話來表達自己的信念:“讓我們直接把話挑明了吧:如果失去了印數少的那些書,那等待我們的便是死亡。卡夫卡的處女作只印了800 本,布萊希特的只印了600 本。假如當初有人覺得不值得出版他們的著作,那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5]他堅信:“圖書能否獲得讀者的認可,完全取決于它的內在價值,而不是它對賬本的貢獻。”[6]中國本土像卡夫卡和布萊希特一樣的未來大師的成長,同樣需要像午夜出版社的熱羅姆·蘭東和美國天才的編輯家珀金斯一樣的本土大編輯的發現和培養。
大編輯是發掘千里馬的伯樂,必須有勇于扶持新生力量的膽識與魄力。因為只有培育新生力量,文化的發展才能有綿延不斷的生命力。作家蔣子龍認為“大編輯”必須具備慧眼識珠、重情誼、重培養、打造名作、點石成金等品質,[7]大概大多數的名家最難忘的編輯都是在他們未成名時“托上馬送上一程”的編輯。發掘新人,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發掘未來。但是,發掘新人常常要在經營上承擔風險。希夫林就深有感觸地說:“處女作幾乎都會虧錢(人們甚至說好多作家總是寫處女作)。即便如此,總有出版商把推出新作家看成一項重要的使命。無論是新觀念還是新作家,都需要時間才能被人們接受。”[8]巴金在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時,將《文學叢刊》打造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標志性叢書。從1935 年至1949 年, 前后出版了10 集, 每集16 本, 推出了86 位作家的作品, 幾乎覆蓋了所有文學體裁。整套叢書中居然有36 本是新作家的第一本書, 堪稱奇跡。巴金確實是在兢兢業業地踐行自己所信奉的編輯理念:“編輯的成績不在于發表名人的作品, 而在于發現新的作家, 推薦新的創作。”[9]曹禺的處女作《雷雨》、何其芳的第一本作品集《畫夢錄》、劉白羽第一本小說集《草原上》、 陳光英(荒煤)的第一本書《憂郁的歌》,麗尼的第一本散文集《黃昏之獻》,師陀最早的三篇小說《谷》《里門拾記》《野鳥集》等都是誕生在《文學叢刊》的搖籃里。更為難得的是,其中還收錄了批判巴金小說的劉西渭(李健吾)的作品,這充分體現了巴金的氣量與風度。在出版界,走名家路線最為穩妥,由此滋生的“客大欺店,店大欺客”的潛規則也極為盛行。魯迅的學生孫伏園是一代名編,《晨報附刊》和《京報副刊》都在他負責編輯時達到一時之盛,他非常重視名家,《阿Q 正傳》就是他反復催稿催生的杰作,但是其編輯風格亦有明顯的局限,即對年輕作者的忽視。魯迅談到他之所以編輯《莽原》周刊“聊以快意”,根源是“不滿于《京報副刊》編輯者”。在金介甫的《沈從文傳》中,談到沈從文經常說起的孫伏園的掌故:在主編《晨報附刊》期間,孫在編輯部的一次會上,搬出一大摞沈從文的未刊用稿件,把它連成一長段,攤開后說,這是某某“大作家”作品,說完后扭成一團,扔進字紙簍。當時沈從文沒有工夫多抄一份留底,報館不愿花郵費退稿,所以他早期的大約1/3 作品都是這樣被扔掉的。孫伏園的編輯成就是不容抹殺的,但他追捧名人漠視新人的風格,不無“勢利”之嫌。時下的不少編輯,也多有追星的愛好,而不是以文稿的質量作為取舍的標準。被嘲諷為“大作家”的沈從文居然真的成了一代大師,孫伏園跌碎眼鏡,這實在是有力的諷刺。最近20 年出版界有不少媒體和編輯熱衷于炒作“70 后”、“80 后”、“90 后”等時尚概念,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扶持新人,而是類似于商業選秀的拔苗助長。誰紅就炒誰,誰暢銷誰就最有水平,成王敗寇和利潤至上的邏輯的風行,使錦上添花的重復出版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
三、媒介融合的信使
在大媒體漸成趨勢的傳播生態中,大編輯必須擁有面向大文化的大視野。在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的重要時期,大編輯應當具備單一媒體形式編輯的專業性與文化深度,又應當具備多媒體編輯的包容性與文化廣度。在媒介融合的環境中,媒體技術的變革要求編輯相應地革新編輯理念,掌握新的編輯技術與編輯手段。而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的交融和對話中,編輯功能呈現出多維度、交叉性、一體化的趨勢,編輯、創作與閱讀之間也向換位、交融的互動模式過渡。編輯要在變化的環境中不落后,就必須不斷提高編輯素質,掌握不斷學習的能力。大編輯要學有專長,博而能一。大編輯柯靈和范用早年因家境和戰亂而失學,都只有小學學歷,但是他們在漫長的編輯生涯中愛書如癡,不斷豐富和拓展自己,在編輯和寫作上都自成一家。具有敏銳的時代觸覺的專家型編輯,是革故鼎新的重要推動力量,像“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張元濟、茅盾、葉圣陶等人的編輯實踐,就呼應并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大轉折與大轉型,引領了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先聲。
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語境中,隨著谷歌將數以百萬計的圖書數字化并將之上傳至網絡,“谷歌圖書搜索計劃”的實施,使許多技術至上者樂觀地為傳統圖書宣判死刑,認為傳統出版必然衰落。一方面,我們的出版人確實應該密切關注出版潮流的變化,通過技術創新提升文化競爭力。美國的柯達公司發明了全球第一臺數碼相機,但因為其缺少危機意識,這家傳統膠卷領域的霸主滿足于眼前的繁盛,錯過了將自己最先掌握的數碼技術轉換為商業利潤的歷史機遇。由于美國和歐洲在數字出版方面已經遙遙領先,我們更應該奮起直追。另一方面,不應該將數字化出版進行簡單化的理解,認為數字化的目標就是對紙質出版的全面取代。圖書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的傳承形式,已經成為歷史的有機的構成部分。紙質圖書的終結,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文明的斷裂。電子時代的信息如果完全失去了傳統的紙面資料的支持,鋪天蓋地的信息將變得不可靠,也難免陷入以訛傳訛的怪圈。因此,筆者認為理想的結果是一如偏愛舊式圖書的哈佛大學圖書館長達恩頓所言:“電子書將充當古騰堡的偉大機器的補充物,而不是替代品。”[10]尼采強調為人應當具備一種追溯和追問歷史的能力,讓“所有的歷史都被重新置于天平上衡量,往昔成千上萬個秘密從歷史的隱匿角落爬了出來”,他感嘆:“誰也無法預測,歷史將來會是什么樣子。也許,過去的歷史基本上還未被發現哩!所以還需要很多這樣的反作用力啊!”[11]在新的媒介環境中的大編輯,就應該具備尼采所言的重新發現歷史的能力,在激活歷史的同時開拓新的出版空間。也就是說,讓印刷文化與電子文化相得益彰,共同構筑閱讀的未來。
在中外文化發展史上,每一個文化大發展的時代都是大編輯層見疊出、群星燦爛的時期,他們各顯其能,以一種強大的合力促進文化的大繁榮。在商業化、世俗化漸成風潮的背景中,我們更需要大編輯對優秀文化的守護,激濁揚清,賡續文脈。他們的非凡之處在于不被外部阻力所牽制,能夠對潛在的發展趨勢有卓越的預見,開創先風,引領潮流,傳播新知,培育新才俊。呼喚大編輯,呼喚綠色的文化沃土,呼喚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影子英雄!
注釋:
[1]黃書元,張曉平主編.人民出版社的往事真情[M].人民出版社,2011:182-183
[2]趙家壁.趙家壁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191
[3]巴金.隨想錄[M].北京三聯書店,1987:374
[4]趙家壁.出版家與出版商[J].出版工作,1988,(2)
[5][美]安德烈·希夫林.出版業[M].白希峰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132
[6][美[安德烈·希夫林.出版業[M].白希峰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147
[7] 蔣子龍.編輯何以為“大”[J].中國編輯, 2010,(3)
[8][美]安德烈·希夫林.出版業[M].白希峰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89-90
[9]巴金.致《十月》[J].十月,1981,(6)
[10][美]羅伯特·達恩頓.閱讀的未來[M].熊祥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75
[11] [德]尼采.快樂的知識[M].黃明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