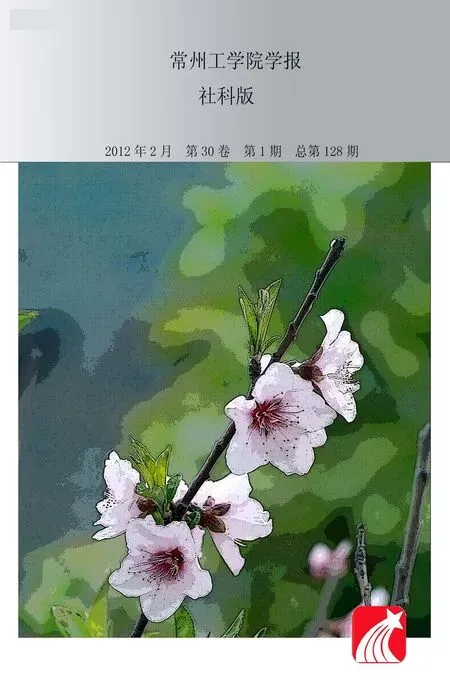《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和《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的文體學考量
趙波
(河南師范大學公共外語部,河南 新鄉 453007)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全世界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通過法律手段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在中國,每過幾年就會出臺和頒布《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及其英文版,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迄今已經有1983年版和2002年版——前者在1988年和1993年先后兩次被修改和完善,2002年作廢;同時后者產生,至今仍在施行。相應地,美國國會出于相似的立法需求和社會規范需求,于1998年制定并頒布了《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后經多次修正,沿用至今。
一、研究動機
根據功能和發布單位的不同,法律文件可以分為實體性法律和程序性規定兩大類,而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文件是應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并通過的。《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由美國立法機構制定,明確地歸屬于正式法律文件,而本文提到的《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則是由中國國務院頒布的有關商標法執行的細則規定,是一個介于法律文本和政府文件之間的過渡型文本。本研究旨在將《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用作參照文本,通過文體學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最終確定《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的文體學傾向,并為此類文本的完善、修訂和新條款的編訂提供文體學的量化標準。
二、語料庫技術與文體學分析的結合
語言學家傾向于將文體學分為文學層面的文體學和語言學層面的文體學,前者關注語言在文學文本中的美學及主題功能,后者則傾向于研究語言形式的特點,以及其完善和提高的方法。本文的文體學研究主要著力于第二個層面,即語言學層面。
按照王佐良和徐有志的看法,文體學的分析應該是一種系統性的描述方法,任何具有文體學價值的語言單位都不應被忽視,包括:句法詞匯學以及語義學[1-2]。然而,受語料庫檢索技術的制約,本文涉及的研究主要是句法和詞匯方面的分析。為了盡可能地保證任何有價值的細節都不被忽略,本文的研究引入了楊惠中倡導的語料庫語言學的技巧[3]:通過X2檢驗,并結合詞圖分布,確定兩則文本中的主題詞;借助形符類符統計,確定兩則文本的用詞多樣性差異;借助詞長、句長統計,確定兩則文本在用詞及句式選擇上的傾向性;通過給兩則文本賦詞類碼,統計兩則文本在詞類使用上的傾向。
此外,由于兩則文本規模不同,針對各個項目的原始統計數字放在一起不具備可比性,故須對所有原始統計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將語料庫技術引入文體學分析,將有助于確保本項研究的客觀性和高效性。
三、數據統計及分析
(一)主題詞
針對文本中所有詞匯的X2檢驗可以借助Wordsmith軟件瞬間完成。根據語料庫語言學的相關原理,X2大于3.84的詞匯就具有顯著的關鍵性。通過對比觀察,兩則文本中分別有6組詞具有相對較高的關鍵性(見表1),且在詞圖分布中表現出較為均勻的分布態勢,兩則文本的關鍵詞分布見圖1、圖2。

表1 最具代表性的6組關鍵詞

圖1 《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中的關鍵詞分布

圖2 《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中的關鍵詞分布
結合關鍵性統計和詞圖分布,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具有較高關鍵值的詞匯在各自文本中的分布是相當均勻的,這足以說明,它們不是因為在特定章節或段落過分使用而具備了較高的關鍵值,兩則文本都是圍繞這些關鍵詞展開的。此外,通過對這兩組關鍵詞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有4個關鍵詞是完全相同的,它們傳遞的信息也是一致的,從而說明,這兩個法律文本從主題層面來講具有可比性和相關性。
(二)詞類分布
法律文本是與責任和權利的認定和讓渡相關聯的,須努力避免模棱兩可含糊不清。也正因為此,法律文本一般刻意回避使用代詞,盡量少用形容詞和程度副詞。使用Claws軟件對兩則文本賦詞類碼,然后借助Powergrep軟件的詞類碼搜索和統計功能,筆者得出了兩則文本中各詞類的分布狀況(如圖3所示)。
《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中的詞類分布完全符合法律英語文本的基本特征,代詞被盡可能地少用,形容詞和副詞的使用也最大限度地被限制。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征:在《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中,名詞使用的比例遠遠大于其他詞類。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名詞化的現象可以使文本在更大程度上具備準確性和信息的包容性,有助于構造被動句式,避免提到動作的行為主體,使句子結構變得精煉。巧合的是,經過標準化處理的《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中的各詞類分布與《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中的詞類分布態勢幾乎完全一致,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的法律文本傾向性以及該文本本身的科學性、成熟性。
(三)情態動詞的文體學暗示
針對所有詞類的統計表明:兩則文本中的名詞使用是最大量、最顯著的,而位于第二序列的則是動詞。相對較高的動詞使用量在文體學層面是沒有意義的,然而,針對動詞的進一步分類統計卻能夠給我們帶來啟示。圖4為兩則文本中所有動詞詞類的標準化統計。

圖3 兩則文本中各詞類的標準化統計

圖4 兩則文本中所有動詞詞類的標準化統計
所有動詞被分為五類:be、do、have、情態動詞、實義動詞。這樣分類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語料庫詞類賦碼技術的限制(只有上述分類方法才能保證所有的細分類都有自己特定的詞類碼)。根據統計,實義動詞的使用量最大,be動詞和情態動詞的使用量并列第二位。其中,情態動詞的使用或者說“多用”具有明顯的文體學意義。Bhatia曾經界定過一類特定的法律文本:行動法條[4]。這類法條對特定的情景進行描述,主要用于施加責任和義務,賦予權利,禁止特定行為,對特定群體或機構讓渡利益;或者僅用于詮釋法典,明確獎懲細則。此外,Bhatia認為這類法條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傳遞允許、命令和禁止意義的情態動詞(may,shall 和 must)大量使用,尤以shall的使用最為顯著。
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對兩則文本中的情態動詞的使用進行了統計和分析,表2為兩則文本中情態動詞出現總數的標準化統計。

表2 兩則文本中情態動詞出現總數的標準化統計
基于Bhatia的描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兩則文本從文體學角度來衡量,應屬于行動法條。主要涉及與商標有關的權利的讓渡和規定。情態動詞大量使用,尤以shall的使用最為突出,而must的使用相對較少,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為了緩和語言表述的力度。
四、結語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判定,《中國商標法執行條例》(英文版)和《美國商標法條款執行法案》在文體學層面具有很大的關聯度和相似性。盡管前者的發布主體是政府機構,后者為立法機關,但兩者所涉主題一致,詞類使用的傾向性相似,特定詞類(尤其是情態動詞)的使用相似,且暗合了法律英語這一特定文體的典型特征——這些典型特征在杜金榜的《法律語言學》[5]中有描述。基于這些發現,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文本的發布主體并不能作為判定該文本文體學傾向的唯一標準;第二,特定文本的文體學傾向可借助相關文本的文體學分析來加以佐證;第三,在我國立法或制定行政規章的過程中,特定文件(尤其是英文版文件)的起草可以借鑒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相關文件的文體風格,畢竟,我們的政府或立法機關出臺的英文版文件或法律文書是以外國公民為受眾的。
此外,本文的文體學研究也將研究對象從籠統的文類延伸到特定文類中的特定文本,此類研究不僅可以完善特定文類的文體學研究,更可以為特定文本的文體學傾向的認定提供高效可行的方法,為特定文本的起草和修訂提供文體學的支撐。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層面的選取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削足適履”之嫌:用語料庫提供的可行且成熟的檢索技術來圈定文體學觀察的范圍。然而,從可操作性和效率的角度來衡量,本文所涉及的研究為特定文本的文體認定提供了便捷的方法和新的視角,而更多更深層次的研究層面的開拓需要語料庫語言學檢索技術的發展和日益完善。
[參考文獻]
[1]王佐良,丁往道.英語文體學引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7.
[2]徐有志.現代英語文體學[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3]楊惠中.語料庫語言學導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4]Bhatia V K.An Investigation into Form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fications in Legislative Writ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nglish for Academic Legal Purposes[D].Brmingham:University of Aston,1982.
[5]杜金榜.法律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