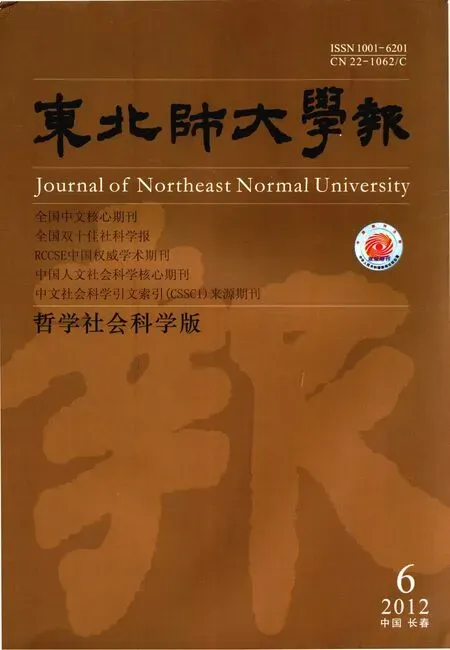論《唐律疏議》對《孝經》的承嬗離合
楊志剛
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孝經》,是論述孝道和孝治觀的儒家代表作之一。《孝經》雖然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沉積,但是后世論孝者仍難出其右,《孝經》以“五等之孝”順承“開宗明義”篇,論述了孝是“至德要道”、“天義民行”,通過對“孝道五要”的論述表達了儒學倡導以孝治家,以忠事君,以德立身,付諸于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漢唐,《孝經》倫理思想的作用發(fā)揮到了極致,成為統治者濟世經民的共同選擇。隋文帝建國伊始,便感慨道:“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1]《唐律疏議》是嬗合《孝經》思想的在唐朝的現實應用。《唐律疏議》又稱律疏、唐律,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是中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12篇502條。在唐代,國家制定法便形成了以“律”為核心,令、科、格、式等為補充的法律體系。《唐律疏議》的功能雖說是“正刑定罪”,但由于其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因此被譽為中國法學領域的百科全書,是封建王朝立法的巔峰之作。如果說《孝經》闡述了“孝”的巨大理論意義,那么《唐律疏議》則把《孝經》之“孝”通過國家立法來展現其巨大的實踐意義。
一、“孝為德本”——以孝治國
《孝經·開宗明義章》開篇即論述“先王”能夠使社會“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至德要道”就是“孝”。孝是經世濟民的政治法寶,是先王道德之根本。“孝為德本”,從個體角度,“德本”體現為個人的道德根基;從群體出發(fā),“德本”則是民族文化的靈魂和精髓。縱觀歷史,“孔子創(chuàng)建了以‘仁’為核心觀念的哲學體系,并且‘約禮入仁’,用仁學的觀點重新解釋了西周的‘禮’,主張以忠恕之道作為‘能近取譬’的方法,來達到以‘愛人’為本質之‘仁’。然而‘仁’的根源則在于‘孝’,也就是說,‘孝’是‘仁’的起點和出發(fā)點。”[2]《孝經·開宗明義章》即講:“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講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也,其為人之本與!”[3]在《孝經》中,孔子認為,無論天子還是百姓,“孝”都是做人不可或缺的道德規(guī)范,是人道德的根本。孔子認為,人有高低貴賤之分,行孝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孝的實質內容都有一個共性——“善事父母”。沈順福教授認為:“從經驗的角度來看,孝順是道德實踐的起點;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慈愛是道德實踐的本體。經驗的孝順和形而上的仁(慈)愛的統一,構成了道德的雙重基礎。”[4]《孝經》所闡述的倫理思想是:“孝”是“先王”的治世圭臬,“孝”也是人之為人的顯著特征,不僅如此,“孝”也符合天地運行的規(guī)律和法則,所以在《孝經·三才章》專門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論闡述“孝”是“至德要道”存在的依據。如果施政者行孝道,就能夠使社會的治理井然有序。正如《孝經·圣治章》所言:“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孝經》中“孝”的思想,逐漸成就為中國人特有的“孝”的品格。梁宿溟先生贊同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論及的觀點:“是故支那孝之為義,不自事親而止也,蓋資于事親而百行作始。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于所親表其年德者,皆將為孝敬之所存。則長年也,主人也,官長也,君上也,且從此而有報施之義焉。以其子之孝也,故其親不可以不慈。而長年之于幼稚,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對待而起義。凡此謂之倫理;凡此謂之禮經。倫理、禮經,而支那所以立國者胥在此。”[5]
《唐律疏議》在開篇中寫道:“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6]卷一《唐律疏議》立法思想是順承儒家“仁德”體系,而孝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唐玄宗時期為例,唐王朝經歷了武則天改朝換代和韋后作亂,政局剛剛結束動蕩,社會秩序也比較混亂,在這種背景之下,亟待重建儒家的政治秩序,發(fā)揮“孝”的教化功能和凝聚作用,所以,唐玄宗開始潛心研究“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和價值,重視《孝經》的教化思想和治國方略,側重唐律對國人的約束。第一,他用《孝經》的“孝道”教化天下百姓以及擁兵自重的四方諸侯“移孝為忠”。第二,親注《孝經》,以完成對民眾的教化。開元十年,唐玄宗參用孔傳、鄭注以及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等人的注解,參照今文《孝經》,作了“御注”。天寶二年,玄宗又作了增補修訂,重注《孝經》,親書刊石,頒行天下。他褒獎孝行,訪求孝悌儒術之士,重視《孝經》倫理思想的治世功能。唐玄宗在《孝經注疏》當中闡釋了儒家“禮政刑教”的治國作用:“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圣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理則國定,此御政之禮也。”[7]唐代統治者除了上述應用《孝經》義理的舉措以外,對表現突出的行孝者和家庭予以表彰,主要形式有:“旌表其門、免除課役、擢授官爵、賞賜財物、頒賜謚號、樹碑立傳、建立祠堂”[8]等。
二、“孝道五要”——以法保障
曾子講到:“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yǎng)。養(yǎng),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9]曾子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孝行對于一個人考驗和艱難,行孝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大事。那么,什么是孝行呢?《孝經·紀孝行章》中講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yǎng)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yǎng),猶為不孝也。”這就是“孝行五要”,也就是說,“孝”作為一種道德行為,應該表現在五個方面之上:平時居家,能夠盡到孝心;供養(yǎng)父母,能夠坦城愉快;父母生病,能夠憂心護理;父母去世,能夠哀戚居喪;祭祀父母,能夠恭敬有加。只有做到以上的五個方面,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孝子。《孝經》并非單言“事親”之孝,推廣及社會層面,“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是其社會性德育功能的一種體現。要求人們,身居高位而不盛氣凌人;身處下位的而不作亂犯上;處境不優(yōu)的而不強行爭斗。“不驕、不亂、不爭,是對現行法律和社會秩序的遵從和執(zhí)行,也包括對社會公德的自覺遵守。一個孝子除了對家庭有責任感外,對于整個社會有責任感也是同樣重要的”[10]可見,孝不但對家庭意義深遠,以“不驕、不亂、不爭”的態(tài)度去面向社會,這對于弘揚社會正氣,凝聚人心向背,促進社會和諧,乃至對當今時代來講,依然彌足珍貴。蔡元培講到:“人之令德為仁,仁之基本為愛,愛之原(源)泉,在親子之間,而尤以愛親之情之發(fā)于孩提者為最早。故孔子以孝統攝諸行,言其常,曰養(yǎng),曰敬,曰逾父母于道。”[11]儒家經典《孝經》所倡導的孝行——在家曰尊,在國曰順,就是孝之大道。
《唐律疏議》就是以這樣的指導思想來對孝行進行保護。如《唐律疏議》在法律上賦予老人一些特權:“律以老、疾不堪受刑,故節(jié)級優(yōu)異,七十衰老,不能徒役,聽以贖論。”這些尊老規(guī)定,也是出于維護孝道的觀念。再如定型于唐代的權留養(yǎng)親制度(指對于犯死刑、流刑等重罪人犯,家中尚有年事已高或殘疾、臥病在床的直系血親,法律特許其居家服侍,直到直系血親死后,再去服刑的一種制度),體現了刑法之下關于“孝”的人性化的一面。《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這里體現了孝與法矛盾時的一個緩沖,體現了法律威嚴之下的親人之間的孝的溫情。《孝經》所倡導的“老有所養(yǎng)”這一孝治原則通過《唐律疏議》的傳承演進,在司法實踐得以實現。此外,還有同居有罪相為隱制度。這條制度源于“父為子隱,乃慈父也;子為父隱,乃孝子也。”就是相互隱瞞對方過錯,法律不予追究。唐代則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同居者,“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隱。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6]卷6此外,唐律還規(guī)定了如果祖父母、父母被人毆打,子孫前往救助,致使對方受傷的也會從輕處罰。如“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毆擊,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斗折傷三等;至死者,依常律”[6]卷23等等,諸如此類的法律規(guī)定。
三、“罪莫不孝”——以刑嚴懲
《孝經·五刑章》講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雖然早在周公時期界定不孝為“元惡大憝”以及到《孝經》中也闡述了“不孝入罪”的司法原則,但是從先秦乃至后來的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制體系相對薄弱,難以規(guī)章建制細化“不孝”罪名,從真正的司法實踐中貫徹“嚴懲不孝”這樣的思想。法律對不孝罪的界定,對不孝入罪的范圍以及對各類不孝犯罪輕重不同的量刑差別等等,尚無詳盡明確的懲罰條規(guī)或縝密細則的刑律條文。在唐代的法律體系具備了實施嚴懲不孝的法律土壤,使完備的唐律發(fā)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唐律疏議》融入儒家“孝治”思想,其立法的核心思想是維護皇權,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嚴懲違反家庭倫理道德的犯罪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唐律立法的儒家化傾向,使整篇唐律對“孝”十分重視,“在唐律律文及疏議中涉及孝的條款有58條,約占全部條款的11%左右”[12]。《唐律疏議》在開篇就將“不孝”列為十惡之一,《唐律疏議》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犯,是名‘不孝’。”“不孝”有8種違犯行為:“不孝,謂告言,諸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yǎng)有缺;居父母喪,自身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對于上述不孝行為,輕則施以笞、杖之刑,重則施以絞、斬極刑,“聞父母喪,匿不舉哀,流;告祖父母、父母者絞,從者流;諸告祖父母、父母者,流”[6]卷23。足見唐律對孝道的高度重視和對“不孝”的嚴懲。如唐武宗會昌年間發(fā)生的劉詡因毆打其母而死于杖下的案例。“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柳)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13]在老人去世服喪期間,為了體現《孝經》所闡釋的“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的孝行要求,青年男女不得在服喪期間談婚論嫁,夫妻不得同居生子。《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若居期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6]卷13
不孝之罪雖然懲罰嚴厲,但與統治者的根本利益相比,這些諸如:“諸告祖父母、父母”等“不孝”罪名,還必須讓位于以皇權為代表的國家最高利益。《唐律疏議》解釋道:“謀反、大逆及謀叛以上,皆為不臣,故子孫告亦無罪。”封建法律倡揚大義滅親,傳統儒家“孝”的人倫道德規(guī)范必須讓位于“忠”的皇權政治需要,封建國家“孝治”司法的根本意義在于維系專制皇權統治的穩(wěn)定,維護封建王朝的權威,即使皇帝的親屬也不能受辱。《唐律·斗訟律》規(guī)定:“諸皇家袒免親而毆之者徒一年,傷者徒二年,傷重者加凡斗二等。緦麻以上,各遞加一等。死者斬。”《唐律疏議》為皇權、父權和夫權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以法律形式明確尊卑等級秩序,遏制不孝行為發(fā)生,維護封建社會治安與穩(wěn)定,在當時和后世都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律疏議》在繼承和發(fā)展《孝經》倫理思想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體現出“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儒家思想境界,但囿于時代背景和階級局限,使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孝”在傳統社會中:“表現于個人,形成守舊排新、安于現狀、聽命于傳統、不思變革等保守性格;表現于家庭,就是內部尊卑長幼關系的絕對權威;表現于社會,就是統治者對即成的社會狀況的維護。這一切,都在客觀上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14]所以,我們必須以歷史的、辯證的、唯物的眼光去考量和分析《孝經》和《唐律疏議》,并在現代社會中予以有辨別的借鑒和系統的反思。
[1]魏征.隋書·儒林何妥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8.
[2]徐儒宗.人和論——儒家人倫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6.
[3]張燕嬰.論語·學而[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沈順福.論道德的基礎——從仁與孝的角度出發(fā)[J].社會科學,2009:6.
[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6.
[6]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經注疏·孝經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季慶陽.試論唐代的“孝治”[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
[9]方向東.大戴禮記·曾子大孝[M].北京:中華書局,2008.
[10]王立仁,盧明霞.《孝經》新讀[J].倫理學研究,2005:5.
[11]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
[12]鄭顯文.唐代律令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6.
[13]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3.
[14]吳燦新.中國倫理精神[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