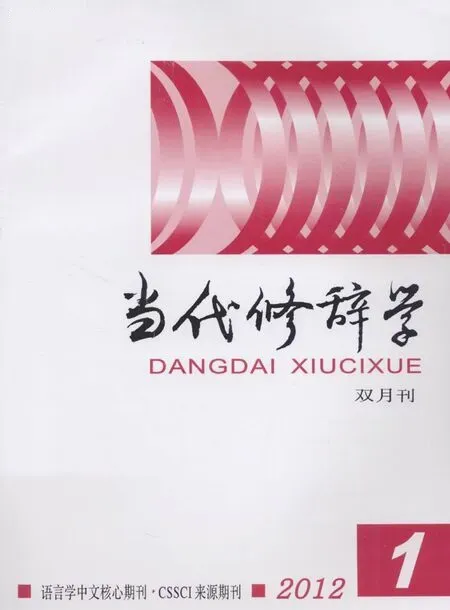從極性程度的表達看修辭構式形成的兩條途徑*
趙 琪
(同濟大學外語學院,上海200092)
提 要 本文以極性程度的表達為路徑,對兩個既有構式“(連)X都Y”構式和“不要太A”構式的發展過程進行考察,證明語言使用者為滿足新的表達需要,改變認知經驗、人際交互使構式與進入構式的成分發生新的互動整合,或通過壓制使原構式義強加在不合法成分上,或通過順化使原有構式從中心義產生派生義,最終導致具有濃厚修辭意味的新構式形成。即修辭動因強化既有構式的語法地位,并驅動新構式形成。
一、引 言
作為形義匹配的構式是對基于人身體經驗的一些動態場景的描述,例如描述物的傳遞的雙賓構式、觀照人或物位移的致使-移動構式(即漢語中通稱的動趨式)以及重構因果致使關系的動結式(Goldberg 1995,Goldberg&Jackendoff 2004)。這些構式的語例分布廣泛,具體表現形式多樣,構成語言中常見的基本句式①,有極高的能產性,完全語法化。而在這些既有構式的發展過程中,不時會出現一些“另類”、“非典型”、“非常規”的語例。還有一些構式,其句法語義與某個基本句式構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能產性、語例的分布和多樣性與基本句式構式相比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語法化程度不高。這兩種現象都是語言使用者出于表達的需要,為實現新的修辭目標,使進入構式的成分與既有的構式進行新的互動和整合,促使構式不斷發展的結果。
劉大為(2010a)提出修辭構式的概念,即“所有帶有不可推導性的構式,只要這種不可推導性還沒有完全在構式中語法化”。按照他的定義,無論是基本句式構式的一些“非典型”的用法還是語法化程度還不高的構式,都屬于修辭構式范疇,與高度語法化的語法構式相區別。他把兩者的關系描述為一個連續統的兩端,并進一步指出:“語法的變化往往起源于修辭,而修辭的歸宿也有可能是語法。”
我們贊成把兩者看作是連續統的觀點,認為修辭是構式發展的動因之一,伴隨構式語法化的整個過程。我們這里以極性程度的表達為出發點,通過對兩個語法構式——“(連)X都Y”構式和“不要太A”構式——的發展變化的考察來解析語法構式和修辭構式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修辭構式形成的兩條路徑。
二、極性程度的表達:從語法到修辭
傳統修辭學所關注的夸張,其實質就是努力將對象所具有的某種性質往極性程度上強調。特別要說明的是,這里說的極性程度并非客觀上達到了極點,而是一種主觀感受上的極致,它往往會因人而異、因境而異。每個人都會將他所認定的極性程度用語言中最高程度的表示方法表達出來,因而即使使用了同一種極性表達方式,每個人所認定的極性程度之間還會有極性程度的差異。對所觀察對象實際占有的某一性質的程度來說,客觀的極性只有一個,而主觀的極性卻會是多種多樣的,以至于我們可以在不同的主觀極性之間進行比較。本文中經常會出現“程度不同的極性意義”之類的說法,原因正在于此。
極性程度通常是與級(比較級、最高級)相關的范疇。在漢語中描述某個狀態、某種性質或某個動作達到了等級尺度的頂端,其表達通常由極性程度副詞“最”、“死”、“壞”、“透”、“極”等來實現,如(除非特別注明,本文語例均來自北大CCL語料庫):
(1)這窮人就最怕喪事和喜事兒。
(2)高太太氣死了,她大聲說:“我不會對她客氣,我要去質問她為什么這樣虐待你。”
(3)夏天突然光臨,樂壞了銷售蚊香、冷飲的商家。
(4)人怎么這么讓人生厭,生病,吃喝拉撒睡,養雞養狗,互相講究,她煩透了。
(5)他頭發極短,耳朵上戴了四個耳釘。
(6)剛到北京時,我舉目無親,真是孤獨極了。
除此以外,極性程度還可以借助語法構式來表達,除本文將分析的“(連)X都Y”、“A得不能再A”構式、“A/V到家了”構式、“怎么A/V也不/沒…”構式等也從不同角度表達了人們心目中的極性程度:
(7)我們家已經窮得不能再窮了。
(8)賀明的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9)看見的人都說憨二真是憨到家了。
(10)你們地區賀雄正書記,在電話里可把你夸到家了,簡直就是一朵花。
(11)乃文怎么想也沒想到會是他最敬愛的二姨。
(12)周圍環境怎么鬧也吵不醒她。
然而這些語法的表達方式看來并沒有達到修辭學中所謂的夸張的程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夸張就是人們主觀感受到的極性程度已經遠遠超越了語法所能達到的極限時,為了將這種程度表現出來所采取的一種話語策略。它的實現,往往會導致語法構式向修辭構式的轉化。
語法構式向修辭構式的轉化有兩種途徑:一是改變構式所依賴的認知場景,通過提出一種僅在非現實的認知經驗中才能實現的程度來給人以更加強烈的極限感,本文討論的“(連)X都Y”構式就是經由這樣一個途徑為展示修辭構式的;二是改變構式所依賴的行為方式,也即改變人際交互功能,通過曲折的推理把直接言語行為識解為間接言語行為,用舊的形式與新的意義的重新匹配帶來的新鮮感以及矛盾的語義關系來提升程度感。看似矛盾的語義關系通過間接推理而消除,帶來的程度感卻保留下來,本文以“不要太A”構式為實例分析了這一途徑。它是否為傳統的夸張,可能會有一定爭議,但在提高極性程度的要求上卻是完全一致的。
三、非現實的認知經驗與修辭構式的形成
1. 作為語法構式的“(連)X都Y”與極性程度的表達
“(連)X都Y”作為一種語法構式,為什么能表達極限程度的意義?
按照常理,如果某對象在一種性質上的表現,就在于它能引起相應類型事件的發生,那么這一對象如果居然能使這一類型事件中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發生,那么它在這種性質上所達到的程度,當然就到了極限。如在例(13)中,“資格老”這一性質的表現之一就在于能夠引人尊敬,而“他”的“資格老”在劇院中如果僅僅是引起了一般人的尊敬,那么這種“資格老”的程度只是一般的。劇院中院長的地位最高,總是處在“被人敬”的位置上,因而要得到院長的“敬”是最不容易的,也即最不可能的。現在“他”的“資格老”居然讓院長“都敬他三分”,使得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也就表達了“資格老”的程度已經達到極性的程度。
(13)劇院剛建立不久他就到這兒工作了,是劇院資格最老的人,連院長都敬他三分。
(14)不僅研究生論文答辯要請老師的客,連幼兒園的孩子也懂得提醒媽媽該送禮了。
(15)(少年梁啟超)寫出來的文章和詩詞,常常連成人都佩服、稱贊。
(16)春節前夕,各地航空市場異常“火爆”,一些航線連全價機票都早早銷售或預定一空。
如果從否定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問題,就應該是某一對象若不能夠使這一類型的事件中最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那么它在這種性質上同樣就達到了最高程度。如例(20)中,科學家是人群中最有智慧的人,因而“生下的小猴兒幾乎都是公猴”由他們來“解釋”清楚應該是最有可能的。可是現在這最有可能的事卻無法實現,當然說明了“生下的小猴兒幾乎都是公猴”難以解釋的程度同樣達到了極限。
(17)長這么大連火車都沒坐過。
(18)我迷失在浩淼無邊的波濤中,連回去的路都已經找不著了。
(19)如胸腺增生或胸腺腫瘤時,就會四肢肌肉無力,甚至連眼皮都抬不起來。
(20)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中生下的10多只小猴幾乎全是公的,連科學家至今都無法解釋其中的緣由。
所以在“(連)X都Y”構式中為了表達極性程度X與Y之間應該有如下關系:
如果Y為肯定的形式,X就應該是Y發生的最小可能項;如果Y為否定的形式,X就應該是Y發生的最大可能項。
在這樣的條件下,無論Y采取的是肯定形式還是否定形式,整個“(連)X都Y”都描述了一種達到極限的事件:因為X是發生的最小可能項,在Y為肯定形式時導致的必然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而X是發生的最大可能項,在Y為否定形式時導致的一定是最可能發生的事情未能發生。而最可能發生的事情未能發生,本身就是一種最不可能的事情,現在卻發生了,所以肯定的情況與否定的情況其實是等價的。
更確切地說,Y一旦遭到否定,雖然X對于Y本身還是最大可能項,但是對于整個否定命題Y而言,X卻成了最小可能項,因為否定改變了Y對X的要求。如“解釋生下的小猴兒幾乎都是公猴”科學家是最大可能項,但是對“無法”“解釋生下的小猴兒幾乎都是公猴”來說,科學家卻成了最小可能項。所以我們在理解“(連)X都Y”構式時其實用不著考慮Y為肯定還是否定形式——
“(連)X都Y”構式中X一定是Y實現的最小可能項。
于是只要能引發“(連)X都Y”的事件,就意味著程度上已經突破常態,達到了平時不可能的狀態,也就是極性程度。
“(連)X都Y”構式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極限程度的意義是可以從構式的構成成分和它們之間的句法-語義關系中推導出來的,以上所分析的其實就是推導的過程。所以這種極限程度的意義是“(連)X都Y”作為語法構式時所具有的構式意義:
通過舉出對于Y的最小可能項X事實上已經發生來表達一種極性程度。
2. “(連)X都Y”:從語法構式向修辭構式的轉化
2.1 極性程度的高低與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
以上尚沒有討論到的一點是,作為語法構式的“(連)X都Y”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其實是有高低差異的。我們發現,無論表現出了多么強烈的極性程度的意義,其極性程度都受到X作為最小可能項與Y實現之間的可能性大小的制約。例如在通常的情況下對于一個城市居民“沒有坐過現代交通工具”的狀況來說,“他連飛機都沒有坐過”、“他連火車都沒有坐過”、“他連汽車都沒有坐過”都能表達很高的極性程度,因為分別在說出這三個句子的說話者的心目中,“飛機”、“火車”、“汽車”都是“沒有坐過”的最小可能項,他才會選擇這一構式來表達他心目中的極性程度。然而事實上它們對于觸發“沒有坐過”事件的可能性大小卻是有很大差異的,與沒有坐過飛機的可能性相比,當今城市居民中沒有坐過汽車的可能性可謂極小極小,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
完全可以想見,“(連)X都Y”構式中的X都是最小可能項,但是不同的X對于觸發同一個Y的可能性還是有大小的,可能性越是小而在現實中卻發生了,那么它作為動因的強烈程度顯然就越是高。因而對“沒有坐過現代交通工具”來說,以上三個句子都表現了一種極限程度,但事實上沒有坐過汽車的極限程度要高于沒有坐過火車,而沒有坐過火車的極限程度又要高于沒有坐過飛機。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你會相信一個城市居民連飛機都沒有坐過,但是他如果確實是連汽車都沒有乘坐過,你一定會不勝驚訝、難以置信。由此我們可以認定這樣一條規則:
一個“(連)X都Y”構式中,X若可由不同對象充任,那么這些對象對Y發生的可能性越小,該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越高。
我們在使用“(連)X都Y”構式表達極性程度時,實際上就是在按照這一規則選擇X的,意圖表達的極性程度越高,選擇的X對于Y發生的可能性就會越小。可以把這一規則稱為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
反比規則本身也是可以從構式構成成分和成分間的句法語義關系推導出來的,但是不同的“(連)X都Y”構式實例能否表現程度不同的極性意義,也就是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該如何實現,卻是無法從構式本身推導出來的,它依賴于我們對于世界的百科知識,需要判斷進入構式的X在現實世界中對觸發Y的可能性大小。
2.2 認知經驗的突破與修辭構式的形成
語言表達中我們往往會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就是將自己心目中某種性質所達到的極性程度的主觀感受,最為極致、最為充分地表達出來。這種欲望往往是沒有止境的,當語法中“級”的范疇無法滿足它時,我們會求助于一些語法構式,而語法構式的構成成分若有變化,如“(連)X都Y”中的X由程度不同的最小可能項充任,所表達的極性程度又會提高。當這些語法構式的最高級的表達式還是無法容納它們時,這種欲望就會演變為一種修辭動因,促使語法構式向修辭構式的轉變,通常所說的夸張就是在這種動因的推動下發生的。作為語法構式的“(連)X都Y”上就經歷了這一過程,而這一過程如前所述是以構式所依賴的認知經驗的變化為基礎的。
按照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X對Y發生的可能性越小,該語法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就越高,于是表達者會拼命去尋找可能性低的對象放入“(連)X都Y”構式中X的位置上,以提高該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可是尋找到的X無論對于Y發生的可能性有多低,X與Y之間的關系畢竟是現實世界中發生過的或者可能發生的,一方面它必須滿足我們日常的認知經驗——我們知道,任何語法構式的成立都依賴于一個認知場景,而場景就規定了它所歸納的認知經驗一定在我們的常識范圍內,是現實世界所允許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須立足于事實,要理解“連汽車都沒有坐過”就需要想象一種事實,例如設想一位城市居民因為過于肥胖無法擠進汽車,或者患有某種眩暈癥無法乘坐汽車,甚而在一個特別落后的城市中汽車確實是一種奢侈品,因而這輩子“連汽車都沒有坐過”。對于一個哪怕只坐過一次汽車的人,就無法用“連汽車都沒有坐過”來提高極性程度。可見語法構式對極性程度的提高是建立在事實描述的基礎之上的,一個X對于Y發生的可能性大小,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得到驗證。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語法構式中極性程度的提高具有客觀性,受制于現實的認知經驗和事實關系。
這一結論說明,我們所討論的極性認知雖然是一種主觀上的強烈體驗,但是當它必須在語法構式中表現出來時,主觀期待中的程度必定會被降低,尤其是那種帶著濃郁情感色彩的程度感受,也一定會被語法構式所要求的客觀和冷靜所消解。然而語言是一種具有不斷自我調節能力的機制,當極性程度的表達作為一種修辭動因支配著語言時,語言通常會調整自身,產生新的表達形式,例如從語法構式中發展出修辭構式來適應這種修辭動因。當然,這種調整是表達者在使用過程中所采取的話語策略中完成的,對“(連)X都Y”構式來說,表達者所使用的策略可以做如下的描述——
按照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充任X的對象對Y發生的可能性越小,該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越高。而小,就是不斷趨近于零,可一旦到達零,就是Y的不可能。認知上的零點就是現實世界和非現實世界、起碼有一點可能與完全不可能的分界點。完全不可能意味著這樣的X與Y之間的關系超越了我們認知經驗中現實世界的限度,當然無法作為事實在這一世界中發生。在“(連)X都Y”作為語法構式被使用時,這樣的X顯然是不能進入構式出現在表達中的。可問題就在于,當表達者的主觀感受強烈到一定程度時,就完全可能將一種非現實的情景當作現實來接受,正如例(22)中“那小妖精說起謊來”迷惑人的程度實在讓人驚嘆,連歷練人生、洞察世事的智者這些最接近零點、最不容易被騙的X都被騙了,但這還不足于說明“小妖精”說謊迷惑人的程度,以至于在潛意識的一剎那中深信再往前一步就會越過零點,“死人”都會被她的謊話所迷惑。這種被強烈情感左右的主觀認知如果也尋求語言表達的話,就會作為一種修辭動因,促使語法構式發生變化而讓人脫口而出“那小妖精說起謊來,的確連死人都要被她騙活”。“被騙”的語義要求中最起碼的是[+生命],“死人”的基本語義就是[-生命],語義上的乖訛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21)那地方的氣味連死人都受不了,工作是又熱又臟。
(22)你說的不錯,看來那小妖精說起謊來,的確連死人都要被她騙活。
(23)據說鷹眼老七的分筋錯骨手別有一套,在他的手下,連死人都沒法子不開口。
特別是在例(24)中,我們整個認知世界的邏輯關系都被顛覆了:
(24)做服裝生意,必須要下棋看五步,否則,等到你想到準備的時候,(連)黃瓜菜都涼了。
已經具備某一性質的事物不可能再次占有這種性質:一朵花從枝條上采摘下來了,不可能再次從同一枝條上被采摘下來;一百元錢從口袋里摸出來了,不可能再次從同一口袋里被摸出來,這是我們藉以認知周圍事物的最為基本的邏輯常識,否則就會出現思維矛盾。黃瓜菜是道涼菜,它原本就是涼的,可是我們等待的客人來得實在太晚了,不僅熱菜熱湯都已經涼了,甚至主觀感受中“涼了”的性質都波及到了涼菜,使得原本就涼的黃瓜菜都涼了,原先的思維矛盾被作為一種正常狀態表述了出來。
表達者處于這樣一種認知狀態中,原先的不可能就會在他的主觀世界中轉化為一種可能性。也就是說,零點以外原先應該被排除的對象,現在都可以作為X進入構式。
對我們的論題更有意義的就是,這種可能性即使在我們的主觀認知中越過了零點的界限具有了可能性,可能的程度顯然也要低于現實世界原先就所允許的一切可能性——在我們的心理感覺中,“死人”被“騙活”的可能性還是一定大大低于現實世界中任何一位閱世無數的長者、洞明人情的智者被騙的可能性,黃瓜菜“涼了”的可能性也一定大大低于任何一道熱菜。可以這樣說——
因為認知關系的改變而越過認知的零點進入X系列的對象,其對于Y發生的可能性一定低于原先就位于零點之內的對象。
我們已經了解,X的充任者對Y發生的可能性越小,構式所表達的極性程度越高,現在連語義乖訛、思維矛盾這些完全不可能的現象都在構式的語言表達中成為現實了,按照極性表達的反比規則,構式表達的極性程度就應該達到極點——語言使用者就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表達出了他心目中最高層級的極性程度,語法構式也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演變為一個修辭構式。
其實在語義乖訛、思維矛盾這些最小可能項和語法構式所允許的最小可能項之間還有一個中間地帶,例如:
(25)回想起那天從街上把他巴巴地帶了回來,頓時連腸子都后悔得青了。
(26)這時屋里擠滿了人,真的是連針都插不進去。
(27)走到最美的花壇前,她連心都停止跳動了。
(28)然后就開始嘔吐,又不知吐了多久,好像連腸子都吐了出來。
(29)方鴻漸忙說,菜太好了,吃菜連舌頭都吃下去了。
(30)如心笑說:“(連)脖子都等長了。”
“腸子”因“后悔”而發青、“吃菜”連“舌頭”都吃下去、“脖子”在期盼中變“長”,在現實中似乎也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與“連黃瓜菜都涼了”不同,它們即使發生了也不會造成邏輯上的矛盾。這就是說,它們在現實中的發生邏輯上還是可能的。有邏輯上的可能性,就有了現實發生的可能性,當然受到客觀世界物質條件的限制,這種可能微乎其微,幾乎為零。不過既然有了“微乎其微,幾乎為零”的可能性,按照極性表達中的反比規則,它所表達的極性程度就應該大于“連汽車都沒有坐過”,小于“連黃瓜菜都涼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將“(連)X都Y”構式分為三種類型,分別以三種典型的表達式來代表:
a.“連汽車都沒有坐過”類
b.“連脖子都等長了”類
c.“連黃瓜菜都涼了”類
a類是語法構式,c類是顯然的修辭構式,b類就其表述的事實在現實中并沒有發生過并且也很難發生而言,也是修辭構式。它們表達的極性程度從a到b到c逐漸遞增。
2.3 “連黃瓜菜都涼了”、“連脖子都等長了”為什么是一種修辭構式?
語法構式向修辭構式的演變,主要的形式是在修辭動因的推動下產生了無法從其構成成分和成分間的關系推導出來的意義。變化較小的是句法語義上的不可推導性,例如Goldberg最著名的例句Pat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帕特將紙巾噴嚏到桌下)之所以被有的學者認為是一種修辭構式,是因為sneeze(打噴嚏)并不具有“致使Y移向Z”的能力,它出現在致使—移動構式中就產生了一種不可推導的意義。這也是一種認知關系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局部的,只涉及到我們對某些行為動作如sneeze(打噴嚏)的認識。
“連黃瓜菜都涼了”和“連脖子都等長了”也產生了一種不可推導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構式的邏輯語義,因為它涉及到的是認知的全局——認知賴以實現的邏輯規律的改變,或者是我們對于世界的基本認識——現實中事實發生的極限邊緣在那里。
通過舉出對于Y的最小可能項事實上的發生來表達一種極性程度,是“(連)X都Y”作為語法構式時的構式義。現在“黃瓜菜”對于“涼了”在通常的認知經驗中并非是一種最小可能項,而是一種不可能項;(吃菜時)“舌頭”對于“吃下去”則幾乎也是一種不可能項,在正常情況下也就是在語法構式的情況下,它們顯然是不具有可推導性的,當然也無法得出極性程度提高的構式義的。但是將強烈感受到的極性程度表達出來的主觀動因,促使表達者將非現實世界中才可能發生的事件當作現實世界中的事實來認識,從而在語言策略上制造了比現實中最小可能項的可能性還要小的項,從而能夠利用反比規則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極性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它們都是修辭構式。
四、交互方式的改變與修辭構式的形成
表達極性程度,另一種很具典型性的構式是“不要太A”。
作為語法構式的“不要太A”是一種祈使構式,表勸誡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構式與進入其中的成分不斷互動整合,先經歷了構式的壓制(Panther&Thornburg 1999),大大加深了構式的語法化;后在提升極性程度的修辭動因促動下,原有的人際交互方式發生變化,祈使類言語行為轉變為感嘆類言語行為。同一語言形式,先后對應勸誡義、贊賞義,矛盾的語義關系通過一系列的間接推理而消除,最終實現了極性程度的表達,同時也完成了向修辭構式的轉化,成為能夠表達極限感的新鮮的語言信息編碼形式。
1. 表勸誡義的“不要太A”語法構式
表勸誡義的“不要太A”構式是屬于祈使構式的“不要太A”構式的基本式:
(31)選好的股票一路騎下去,不要太在意一時的漲漲跌跌。
(32)對于當前文壇的一些現象,王蒙主張不要太夸張。
(33)擇業不要太挑剔。
(34)她還表示自己很好,希望父母和家人不要太牽掛。
(35)你們這些人不要太浪費了。
因為“不要太A”構式是行為結構,進入其中的典型動詞是表示行為的動詞,如例(31)到(35)中的“在意”、“夸張”、“挑剔”、“牽掛”和“浪費”。同英語當中的祈使構式的發展軌跡相同(Panther&Thornburg 1999)②,靜態動詞(形容詞)也能夠進入到這個構式當中,如例(36)到(40)中的“大”、“多”、“長”、“快”、“累”,也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不要太 A”語法構式:
(36)搞工業,規模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項目。
(37)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
(38)戰線不要太長。
(39)中央主張政改步伐不要太快。
(40)不要太累。
盡管非動作謂詞與祈使句的構式義相沖突,但構式與動詞重新互動整合,通過壓制/同化,祈使構式把動作義“強加”給了進入其中的非動作謂詞,擴大了構式的分布。而因果轉喻機制是這里壓制過程能夠實現的認知理據,由靜態動詞描述的動作結果概念激活動作本身,即“做些什么”(以達到描述的結果)。如例(39)激活的是“政改注意節奏”(以達到步伐不太快的結果),例(40)激活的是“干活/做事張馳有度”(以達到不太累的結果)。當然這些經過構式壓制過程的語例似乎并沒像前面討論過的“(連)X都Y”構式產出的語例那樣,帶有強烈的修辭效果,原因就在于發生這種靜態詞匯義與動態構式義沖突與和解的祈使構式已經高度語法化,其意義識解的臨場性幾乎已經完全消失。沒有額外的認知付出,自然沒有額外的修辭效果。
2. 表贊賞義的“不要太A”修辭構式
有趣的是,“不要太A”構式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面討論到的構式壓制/同化,還在新的修辭表動因促動下,發生了由表勸誡義的中心義派生出表贊美義的變化,即構式的順化(劉大為2010b),產生了具有修辭效果的新構式。這個新構式來源于吳方言,但逐漸進入到普通話當中,正處在語法化的進程當中。如:
(41)華商網美女主持在地鐵口遭到了前來乘坐地鐵市民的“圍觀”,長得不要太漂亮哦!(華商網,20110916)
(42)香港銀行服務態度不要太好哦。(517hk,20111128)
(43)真的是見識一下,絕對的見識!因為這家不要太有錢哦,簡直是太太太太有錢了。(西祠胡同,20110803)
(44)住的是大房子,想吃啥吃啥。出門就是水泥路,公交車開到家門口,這日子不要太美哦!(新華網江蘇頻道,20081209)
(45)教師最舒服了,又放假了,兩個月不要太舒服哦,還有工資拿。(幼兒教育,2011918)
(46)剛想出這招的時候還興致勃勃地編了個應用程序,專門根據投注金額、次數和賠率來計算利潤,當時覺得自己不要太有才哦!(幸運28網站,20101128)
從使令功能的勸誡義到感嘆功能的贊賞義,轉向的心理預設是:
1)“不要太”后面描述的特征是人們向往的、積極的;
2)盡管如此,這種特征仍有“過猶不及”之嫌,發展得太充分了就有可能向反面轉化。
因此當一種事物可控的積極特征在正向發展并接近極限時,應控制它的發展勢頭以避免其向消極方向逆轉。出于這種心理,人們會對特征的責任者發出警告,勸令其加以控制。而表勸誡的使令言語行為的預設是:特征的發展已接近極限,否則就沒有必要發出警告。現在勸誡發出,說明特征已接近極限,即其最理想的狀態。因而這里的勸誡本身就包含著積極評價的因素,勸誡不過是一個間接言語行為,其作用是激發推理,得出真正要實現的贊賞、感嘆的結論。
間接言語行為的發生開始都是臨時性的,一定要借助一個特定的話語場景,結合現場知識進行推理才能獲得“不要太”語法構式所不具備的意義。隨著相似場景的經常出現,相同的語言表達反復發生,通過勸誡達到贊賞的言語行為逐步穩定化,“不要太”語法構式派生出表“贊賞達到極性程度的某個性質”構式義的“不要太A”修辭構式。
此處新構式的形成和識解依賴轉喻認知機制才得以實現:“勸誡義”是轉喻鏈條上的結果,激活導致人們作出這種“勸誡”行為的原因概念——“已經足夠A了”,有“如果再做些導致更A的行為的話,就過度了,因而沒有必要”的涵義。另外,這個新構式的成立還要依賴兩個語法標記:句末嘆詞“哦”和句末升調。
3. “不要太A”修辭構式的泛化
開始進入到修辭構式“不要太A”后面的一定是表肯定描述義的形容詞,比如“漂亮”、“好”、“美”等,保證“贊賞義”的導出。可是隨著這種極具新鮮感的構式不斷引發人們使用它的欲望,使用的場合越來越寬泛,以至表否定描述義的形容詞也漸漸進入構式,如(47)-(51)中的“無知”、“丑”、“郁悶”、“自私”和“倔”等,“不要太”修辭構式構式義開始泛化,從贊美擴展到感嘆一切達到極性程度的性質:
(47)搜狐,你不要太無知!(天涯論壇,20081224)
(48)有關王力宏的丑聞不要太丑哦!(SOSO問問,20100927)
(49)房子被無良人錯賣,不要太郁悶!(加拿大家園論壇,20080610)
(50)現在小孩不要太自私哦,才不要弟弟妹妹呢。(飄渺水云間,2011721)
(51)我不動,你拿我怎么樣,我脾氣不要太倔哦。(百度空間,20100614)
這里極性程度的表達與識解有相似的認知理據:轉喻鏈條上的結果概念“勸誡”激活原因概念“性質已經到了極限”。極性程度的進一步表達,表明“不要太”修辭構式的進一步語法化;而另一方面,“不要太”修辭構式對極性程度的進一步表達和識解,一定要借助特定的話語場景進行現場推理,用法有限,表明“不要太”修辭構式正處在語法化的進程當中。
五、結 語
在提升話語極性程度表達的修辭動因的促動下,已經高度語法化的既有構式“(連)X都Y”構式和“不要太A”構式在發展過程中,或通過認知經驗的改變,或通過改變人際交互方式,發生了從語法構式到修辭構式的轉變。與語法構式不同,修辭構式強調極限的主觀程度,能給人帶來更強烈的極限感,而其構式的形成和識解,離不開特定話語的具體場景,要結合現場知識借助一系列推理才能最終實現。我們的分析同時也證明,新構式形成的實現、識解的完成、以及修辭效果的達成,都依賴作為基本認知機制的轉喻來完成。
修辭是構式發展的動因之一,伴隨構式語法化的整個過程,促使構式朝兩個方向發展:即為滿足新的修辭需求,既有的已經高度語法化的構式與進入其中的本不符合構式準入規則的成分發生新的互動,構式義強加于“不合法”成分上使其發生適應自己的變化,產生這一構式的“非典型”語例,描述具體語境下的、體現更豐富身體經驗的動態場景,使這一構式朝修辭構式轉變;另一方向的發展是,既有構式為滿足新的修辭動因與進入構式的成分發生互動整合時,構式由基本義派生出新的意義,最終導致產生與原構式緊密聯系、但又有差別的、處在語法化初級階段的新構式,即修辭構式。無論朝哪個方向發展,修辭構式的出現都使既有構式分布更廣泛、用法更多樣、使用頻率更高,導致這一構式更深的語法化。
注 釋
①構成語言中的常見基本句式的構式因具體語言的不同而不同,但也不排除具有某些共性。目前對英、漢兩種語言的研究表明,雙賓、致使-移動和動結構式分別構成英、漢兩種具體語言中的基本構式。
②Panther&Thornburg(1999)給出以下例子:
(a)Be happy!
(b)Be guided by what I say!
(c)Don’t fall into the w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