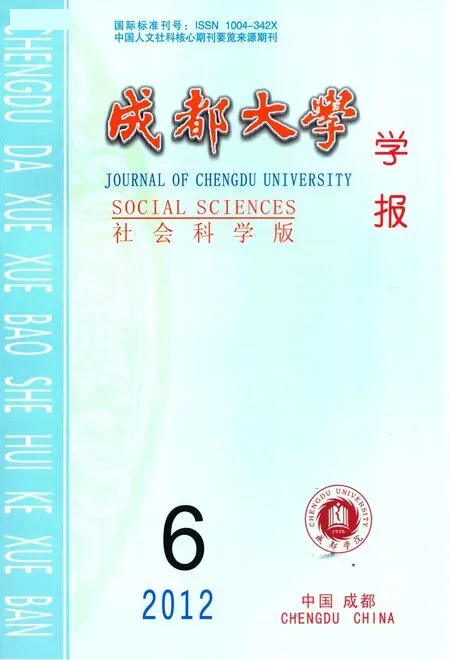烏托邦、非理性、歷史與個人
——格非小說“人面桃花三部曲”主題分析
梁 儀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1)
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以《追憶烏攸先生》、《迷舟》等中短篇小說聞名,并以其敘事技巧和存在探索上的先鋒姿態而被文學史歸為“先鋒派作家”的格非,近年陸續推出《人面桃花》(2004年)、《山河入夢》(2007年)及《春盡江南》(2011年)三部小說,構成長篇小說系列“人面桃花三部曲”。
與80年代先鋒時期中短篇創作以形式技巧探索為主以及90年代轉型時期初作長篇小說時的生澀迷惘不同,“人面桃花三部曲”無論其藝術技巧還是思想主題都較為成熟。尤其是作為對內容厚度和思想深度有更高要求的長篇三部曲而言,這三部作品中顯現出來的對人性、歷史、烏托邦、知識分子精神的重大命題的思考,是我們探討其得失成敗的重要關注點。
三部曲講述的三段故事,在時間上有承續關系(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十年代、當下),在空間上有重疊關系(地處江南鄰近的普濟、梅城和鶴浦,“花家舍”),在人物上有血緣關系(陸秀米、譚功達、譚端午),結構上有回環照應關系(秀米臨終所見、譚功達聽到的戲文、譚端午的創作等),這些都是三部曲作為整體的宏大建構。而更為重要的是三部小說在思想主題上的邏輯統一關系:烏托邦、非理性、歷史時代與個人內心是一以貫之的主題,這些主題依托三個不同時代的不同故事反復地被探討,不斷被深化,形成三部曲的核心主題,值得探究。
一 烏托邦的精神追求與局限失敗
“人面桃花三部曲”概括而言就是發生在不同又相關的三個時空對烏托邦精神追求與局限失敗的故事。“烏托邦”是古今中外文學文化的重要母題,西方有柏拉圖《理想國》、莫爾《烏托邦》等,中國有老子的“小國寡民”、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及近代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等,不勝枚舉。格非在三部曲中強烈地體現出對這一母題的高度關注和思考,不同于前述作品的是,格非的這種思考既不是一相情愿的求索,也不是具體而微的實踐方案,而是表現出一個現代作家對古老綿延的“烏托邦”精神既追懷贊美又質疑反思,既孜孜以求又無奈嘆息的復雜心態。
格非在三部曲中設置了一塊“烏托邦”的試驗田,即三部小說中都出現的地名“花家舍”。可惜這塊負載了烏托邦夢想的土地卻都走向了它的反面,露出或猙獰、或陰森、或淫邪的面目。《人面桃花》中王觀澄滿腔抱負,試圖建設一個世外桃源,結果只成了爭權奪利相互殘殺的土匪窩,花家舍外表一派安逸祥和,其實暗藏權欲邪念。《山河入夢》中郭從年建設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物質豐美、井然有序,但是社員卻大多畏畏縮縮、戰戰兢兢。其背后是社員相互監督的“匿名信”制度和神秘間諜機構對人們精神的禁錮和摧殘,花家舍的空氣中布滿了陰森恐怖的竊聽和偷窺。《春盡江南》的花家舍從理想主義者王元慶的手中敗落給商人張有德,最終成了一個充滿物欲肉欲的“銷金窟”,成為現代消費社會人們放縱聲色的眾多消遣去處中的一個。對于精神淪落、物欲騰升的部分現代人而言,他們的桃花源就是這樣一塊“花家舍”。從花家舍在三部小說中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對桃花源的向往與曲解、追求與失敗。要么成土匪窩,要么成集中營,要么成銷金窟,都是桃花源的反面教材。
作家格非對于“花家舍”流露出痛惜又諷刺的態度,也是對盲目追求烏托邦的一種警醒。在這里格非所關注的不僅僅是桃源夢的探索與失敗過程,而是潛伏其中的人性悖論:苦心孤詣追求夢想的人們最后卻在背離夢想的路上越走越遠,或曲解或遺忘或丟棄了最原初的夢想。無論是秀米、譚功達,還是譚端午,烏托邦的精神追求都潛伏在他們心底或付諸行動,但最終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他們熱切甚至不惜代價、不顧后果地追求心中的桃花源,而這樣的完美追求注定在現實里頻頻碰壁。他們身上都兼具了理想的可貴與理想的失落,二者之間構成強烈的人性悲劇張力。格非對此既有痛惜懷戀的感傷,更多更深刻的是對理想追逐中人性變異的思考和警惕。
有意思的是,這種烏托邦精神是與知識分子精神融為一體的,無論是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其后都是知識分子對精神家園的追尋和追尋路上的思索。其中包含著知識分子如何參與現實、如何安頓靈魂、如何在理想幻想與現實實際的落差里反思自身與反思人類等重大問題。對于從理想主義大行其道的20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格非這一批作家,烏托邦色彩在他們作品里并不少見,如閻連科《受活》、陳忠實《白鹿原》、賈平凹《廢都》、王安憶《烏托邦詩篇》等,這些作品都從不同角度或深或淺地思考著烏托邦。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格非對此有一種強烈的偏好和執著,三部曲不僅僅是烏托邦的故事和思考,小說本身也帶上了濃厚的烏托邦氣質,即對完美追求的幻想和追求而不得的失落。這種幻想性和失落感可以說貫穿格非從早期《迷舟》為代表的短篇小說到現在的三部曲創作,構成格非小說的獨特氣質。只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正由于這種對烏托邦的偏好和執著,三部曲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理念先行、圖解思想的痕跡,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作家的幻想性和失落感特質也往往掩蓋了更深刻的理性挖掘,盡管有一定的思考和警覺,但小說深度仍有所欠缺。
二 非理性:理解的同情與警惕
“人面桃花三部曲”中的烏托邦探索體現在人物身上便是富含激情的狂熱的非理性特征。三部曲中的“非理性”最集中的是通過一種極端的方式——瘋癲來表現的。這種瘋癲往往與小說人物的烏托邦追求有關,正如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認為激情本性是瘋癲妄想的基礎,瘋癲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因此它既帶著濃烈的激情和狂熱,又因其不切實際幻想性異質性而與眾人產生緊張關系。
這點在第一部《人面桃花》中最為明顯,書中凡有烏托邦情結的人物無不帶有瘋癲氣。在小說開篇就有詳細記述父親的發瘋。母親和仆人不知就里把父親發瘋歸于“天底下的讀書人,原本就是一群瘋子”[1];而迂腐先生丁樹則嘲諷父親“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也不無道理,在這里格非借丁先生之口點出所謂桃源夢背后恐怕也只是官場功名的失意又不甘心。中國古代文人自來有隱逸之風,其中多少人不過是如父親陸侃一般在桃源夢鄉里安頓功名利祿之心罷了。此外,革命與情欲糅為一體的張季元、“活死人”王觀澄、冷漠絕情的“校長”秀米等,他們身上都帶著強烈的“非理性”特征,在眾人眼里也無疑都是“瘋子”。有意思的是作家格非對筆下的這些瘋子,既寄以同情理解甚至流露出贊賞,又不時地通過瘋子與實際的脫節與眾人的緊張來揭示“非理性”因素的危害和悲劇。
再如《春盡江南》中王元慶并不是主要人物,但他卻是全書精神的一個縮影和隱喻。他曾是80年代理想主義的熱血詩人,90年代下海的成功商人,然而最后他卻淪為了精神病人。他那些箴言式的信往往直切現代社會精神弊病“我們其實不是在生活。連一分鐘也沒有。我們是在忙于準備生活而提心吊膽。”[2]“如果一個人無法改變自己受奴役的事實,就只能想盡一切辦法去美化它。”[3]這里,從80年代走過來的格非既有對曾經理想主義的追懷和反思,又有對商業經濟控制下人性變異的擔憂和警惕,作為瘋子的王元慶承擔了這兩方面的寓意。相比前兩者,格非對《山河入夢》中的譚功達則寄予更多的喜愛和同情。與陸侃和王元慶的“真瘋”不同,譚功達只是帶有“呆氣”,這一方面體現在他身為縣長卻不懂官場斗爭,一心只想實踐自己的桃源夢,最后落得百姓受災官位不保;另一方面體現在他對“女兒家”的態度,一如寶玉式的花癡,可惜后來錯過與姚佩佩的愛情卻落入了虎妞式的張金芳手中。即便是作者自己喜愛的人物也難免悲劇的結局,這便是格非對“非理性”理解的同情和警惕。
這種對“非理性”的曖昧態度其實表現出曾經歷過70年代文革癲狂、80年代理想主義激情和90年代商業社會熱潮的作家格非面對“非理性”的復雜心態:既一次次深陷“非理性”的熱潮不能自拔,又在退潮后清醒與感傷交織。如格非自言:“作家的重要職責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處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線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躍的、易變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4]對于“非理性”(如瘋癲、偶然、卜卦、預感等)的表現一直潛伏在格非創作中,無論是早期短篇《迷舟》《褐色鳥群》《傻瓜的詩篇》還是長篇《敵人》《欲望的旗幟》,到了近幾年的三部曲,可以看出格非對“非理性”因素的把握已經更為純熟。這種非理性特征與小說虛構藝術結合構成了格非創作的一大特色,有論者將其歸為“格非的神秘主義詩學”[5]也不無道理。
三 歷史時代與個人內心
格非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表現出對歷史的濃厚興趣,有趣的是他把這種歷史思考與個人內心融合在一起,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雕刻人物的細微心態,既寫歷史時代風云變幻中個人的心態命運,又寫個人內心激蕩中折射出來的歷史時代影子。“動蕩年代里挾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個人,尤其是個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識——不論它顯得如何脆弱、如何轉瞬即逝,但在我個人的記憶和想象中,卻顯的不容辯駁。”[6]從中可見,格非創作三部曲的初衷之一便是這種歷史與個人的糾葛,歷史中的個人、個人內心的歷史形成三部曲的另一個核心主題。
《人面桃花》中秀米是個秋瑾式的女革命者,全書四章就是她從“閨女”到“女人”到“校長”再到“禁語人”的人生經歷圖譜。其中具體記述革命行動的只在“校長”這章,而且采用旁人的視角敘述,看到的只是秀米的側影。重心放在革命前后,重點寫初潮來臨驚恐羞澀的少女“秀秀”、出嫁被劫傷心的女人“秀米”和革命失敗后黯然沉默的“禁語人”。這樣的秀米一改革命者的刻板印象,他們不是癲狂冷漠或熱血正義的形象,而有脆弱纖細的神經,有情欲沖動的折磨,有失敗后落寞感傷的隱退。這也是作家格非在“革命外衣”之下,試圖引領讀者深刻反思:知識分子們一直試圖干預現實,可是他們孜孜以求的驚天動地的“革命烏托邦”為什么一碰到現實就破碎,要么軟弱逃遁(陸侃),要么面目猙獰(小驢子、張季元),要么失敗而歸(秀米),何處才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所?
《山河入夢》同樣表達了對歷史與個人關系的思考。作為縣長的譚功達卻常常沉浸在“花癡”的神游里,在白小嫻、姚佩佩的愛情里舉棋不定,在桃花源的夢境里癡想不已。作為五六十年代國家初建時期的縣長,歷史賦予他的任務是建設,盡管他也參與其中,但他所夢想的不過是一個桃源勝境,這與歷史任務是相沖突的,因此后來他在官場斗爭中落敗下臺。小說中對歷史時代與個人內心沖突的表現形成巨大的張力,尤其最后一章在“花家舍”的背景下,命運的感傷和錯過的愛情交織把全書推向高潮,這便是歷史風云里個體生命的悲歡,所以能夠深深地打動人。
《春盡江南》不同于前兩部有歷史背景而主要記敘當下生活,它同樣折射出時代與個人的隱秘關系。詩人譚端午和律師龐家玉構成小說中兩種氣質的分裂與交融:在物質時代,一方面文弱清高的詩人不斷逃避現實企圖回歸性靈而不得,另一方面世俗功利的律師不斷迎合現實卻又陷入精神痛苦之中。他們及周圍一批人都是時代的“失敗者”,勾勒出時代風云里種種個人無奈。由此思考集中在當下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和心態、物質消費時代的人性扭曲兩大方面。前者集中體現在譚端午身上,盡管他是小說主人公,但其言行思想無時無刻不處于“邊緣狀態”。工作上,他所在的地方志辦公室只是個清閑部門;家庭生活中,經濟收入高的妻子處于絕對領導地位;朋友圈子里,他猶猶豫豫,總愛說“也不妨試試”這樣無關痛癢的話。在周圍人忙著升官掙錢、縱欲狂歡時,他始終沉浸在自己的思緒里,沉浸在書本和音樂里。實際上,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分子地位的失落是必然的,最可怕的是知識分子精神的失落,幸而格非始終為譚端午把持著這條底線,可想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格非對這個群體的喜愛和希冀吧。后者則是通過多人來表現:在現實里摸爬滾打的龐家玉卻始終參不透現實的game,她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而肉體和精神雙重出軌;在官場上呼風喚雨的陳守仁最后死于不明不白的謀殺;徐吉士混跡煙花柳巷放縱肉體;年輕女人小史借自己的肉體來換取金錢和夢想等。這些在我們當今社會見慣不驚,可是被格非放置到小說里,不禁讓人訝異:人們精神中那些夢想的激情和力量到哪兒去了?難道都化作了或肉體或金錢或權力的欲望?這些欲望又如何扭曲了人性?這些都是《春盡江南》帶給我們的思考。只是這樣的承載太多,太貼近現實真實而損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和想象力,這也是第三部的缺憾。
“人面桃花三部曲”在藝術技巧上也許還值得商榷,但其主題選擇卻體現了作家一定的眼光和勇氣。一方面是三部曲勾勒出20世紀初至今的時代風貌,故事背后既是歷史和現實的隱喻,更重要的是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精神狀況的探析。“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人已經生活得相對比較猥瑣了,不太會想烏托邦的問題或者是做白日夢。其實文學的職能之一就是白日夢,在現實生活重壓之下給我們提供一絲喘息。”[7]對烏托邦激情的呼喚同時又有對烏托邦背后非理性的警惕,這是時代精神建構的難題,也是三部曲努力探求的問題。小說不一定能給出答案,重要的是它給人以警醒。另一方面從格非小說的主題探索之路來看,自80年代先鋒的存在思考到90年代轉型的迷惘與陣痛,再到近年的三部曲,作家對這些主題始終在關注,且不斷在成熟。從三部曲可以看到格非面對烏托邦和非理性的曖昧態度,這種曖昧態度也普遍代表了時代風云里的知識分子復雜心態。與別的作家不同,這種復雜心態下形成的幻想性和失落感一直貫穿格非小說,成為其獨特氣質。
綜上所述,格非“人面桃花三部曲”既有宏大建構又著力表現人類精神細微的顫動,既在虛擬時空里馳騁想象又關涉當下生存實際。三部曲在烏托邦、非理性、歷史時代與個人內心三個核心主題的統攝下叩問時代精神,可說是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上一次較為成功的主題探索。尤其是在我們這個物質至上的消費時代、娛樂至死的戲謔氛圍里,像格非的三部曲這樣比較純粹的人性精神思索,也許可以給人們日漸麻木的精神一些刺激。正如格非在一次接受訪談時所說“文學敘事是對生命和存在的超越”,這種力圖超越的精神力量對作家而言是十分寶貴的,對于當下日漸泛濫的文學創作也具有某種借鑒意義。
:
[1][6]格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8,1.
[2][3]格非.春盡江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72,175.
[4]轉引自劉偉,格非的神秘主義詩學[J].文藝評論,2009(1):64.
[5]劉偉.格非的神秘主義詩學[J].文藝評論,2009(1):62-67.
[7]格非.《山河入夢》書封[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