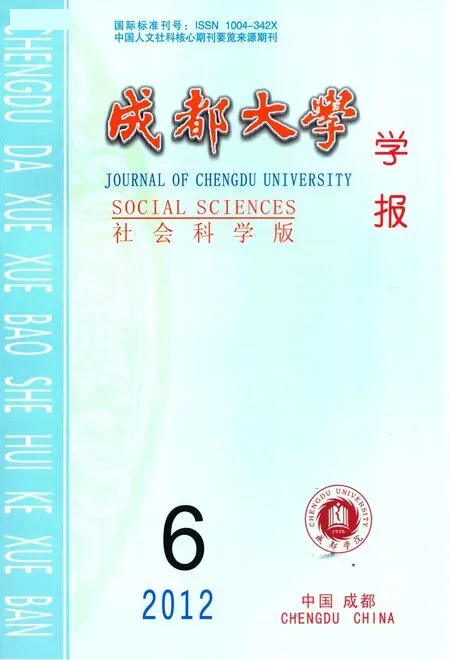從“神女”到“女神”
——試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轉型
粟 斌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 637009)
在對于郭沫若詩集《女神》的意象進行研究的論文中,關于其中諸如鳳凰、天狗、煤、太陽、大海以及其他個體性意象的研究成果比較多。但對于作為中心意象的“女神”的關注明顯遜色,所據往往是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所引用歌德的詩句“永恒之女性,領導我們走”作為有關的說明,還有一些研究將女神意象與其他意象放在并列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為中心意象的重要意義。今天,重新回顧九十年前由《女神》所帶來的這一場新詩風暴,探索《女神》得到時代認可的原因,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詩集中作為中心意象的“女神”,在貫連起新舊文化之間的聯系,并誘發時代性的詩情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喚起新詩與古典文化精神的聯系
文學意象的審美接受,首先是對其載體也即文學語言符號進行的認知活動,這也是一個從詞語的表層線性結構中探索深層命意的充滿著積極思維特征的心理活動過程。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文學作品的生命體現在意象層中,接受者在閱讀中的審美對象,不僅僅是白紙上的黑字,也是“呈現在自己感覺中的、由作品三個語言學層次激活的意象。”[1]經由詞語表象的刺激,語言描繪能夠對詞語的接受者喚起相應的想象,進而呼應起接受者的深層語言心理結構,使該詞語與有關意象發生相互的作用。在“女神”一詞中,“女”與“神”兩字都具有單獨表意功能,可以組合為“女神”,也可組合為“神女”。盡管各自表達的意思不同,但由于字面上的相似性,其詞語表象所刺激和引導的功能仍然存在。
眾所周知,在一個文明自成體系的社會中,語言表達總是以某種約定俗成的習慣為基礎。某一類型的形象總是帶有該文化土壤中強烈的集體情緒記憶色彩。以“女神”(女性的神祇)為例,在漢文學關注過的所有女神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為充滿了浪漫情色因子的巫山神女系列。盡管在中國神話傳說中,女神數量眾多,其形態、功能、精神類型各異,但在文學創作中,像女媧那樣的原始古老的創造神,享有神仙世界崇高地位的西王母,以及在地方民間傳說和各類祠祀中出現的務于傳統生育事務或各類世事的女神,則很少被選擇為詩人們浪漫情懷傾吐的對象。
自宋玉《高唐賦》、《神女賦》以來,“神女”作為漢文學史上最為經典的感性形象之一,她(她們)不但有美好的形象,而且還有不同時代版本的浪漫的故事,以及伴隨著誘發欣賞者聯想和想象的情感因素。這種影響還波及到其他類似對象,像曹植的《洛神賦》寫的是宓妃,卻是“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而來。由于宋玉、曹植的藝術成就,高唐神女、洛神幾乎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女神的代稱。以至于類于母親型神祇的西王母,盡管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但許多詩人的關注視點卻不在于西王母,而在于她座下的侍女。這個有趣的文學現象,從創作心理的角度來說,是創作主體在尊重古老而崇高的人神關系時意圖拉近彼此情感距離的一種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可謂是神女型故事在文學中的變異處理。
從郭沫若詩集《女神》推出的時代而言,用“女神”一詞能呼應起新詩與古典文化精神趣味的聯系,得到更多的關注及認可。這正如臺灣學者葉維廉《秘響旁通》一文指出:“打開一本書,接觸一篇文章,其他的書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異國的,都同時被打開,同時呈現在腦海里,在那里顫然欲語。”[2]接受主體已有的心理經驗和情緒記憶,不但是理解、體驗外來情感和審美信息的基礎,也左右著人們的行動和思想。盡管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文化水平和心理基礎上的差異,將不同程度地影響接受者根據自己的文化信息網絡和情緒記憶所獲得的審美體驗。但閱讀中的審美接受體驗,仍然需要在接受主體的文化積累基礎上,進行主客體的融合、再創造,才能得到新的審美體驗。
二 郭沫若新詩中女神形象的時代轉型
前文已指出“女神”一詞意在喚起知識群體對于傳統文學意象“神女”的記憶和情感體驗,但是在《女神》詩集中,詩人筆下的女神形象并不唯傳統是繼,而是出現了明顯的轉型。這種轉型首先表現為閱讀者看到的是女神形象由神女型轉向創造性的女神。
宋玉筆下的神女,是一位姣麗迷人,主動薦枕席的女子。盡管聞一多先生以為神女乃是在原始宗教和生殖崇拜意義上的高媒女神[3],但這并不影響后來的寫作者,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無論是欣賞艷羨還是其他角度,幾乎都把與神女有關的事歸入艷情。這種創作傾向在漢魏六朝以來,又與當時的求仙方術結合,將神女作為男性作家編織艷遇類白日夢的故事原型。詩人們筆下的“巫山云雨”專指風流韻事。唐代杜甫極其精練地創造了“峽云”、“行云”、“神女雨”、“巫山雨”等等詞,而李商隱則移植了這批詞,……《花間集》的作者又把李義山的手法移植了這批詞,成為以寫愛情為主要內容的表現手法[4]。在這種創作思維的影響下,宮體詩中用“巫山女”、“洛川神”、“姮娥”、“弄玉”等指稱美人,是十分常見的用法。至以陳寅恪言“六朝人已侈談仙女杜蘭香萼録華之世緣,流傳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目娼伎者。”[5]無論是作為理想寄托還是情欲之思的對象,在歷代文人的創作中,神女型的女性神祇多是無所事事型,或清新孤遠,或放蕩游佚,都沒有表現出對現實世事的明顯關注。而郭沫若新詩中的女神形象明顯超越了傳統藝術視野所凝固的神女的層次,不但與創造大神(女媧)的使命結合起來,而且也不僅僅局限于女媧神話中運用五色石修缺補漏的內容,而是堅定地主張“我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神。”“我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結。”“為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甚神像!”這些語言突顯出女神形象在新時代的轉型。
當然,這種轉型在詩歌史上并不是完全無跡可尋。比如蘇軾有一首吟詠巫山神女的《神女廟》,其形象就迥異于過去文人詩中的神女形象。“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奸。深淵鼉鱉橫,巨壑蛇龍頑。”在這猛獸橫行的環境中,“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而且該女神造福人間建不世之功的方式也很令人嘆服。“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其結果是“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云興靈怪聚,云散鬼神還。”[6]這一混亂世界的秩序整頓者的形象,使文學史上的神女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總的說來,這一形象的文學影響與傳統視野所凝固的神女形象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與女神形象的轉型密切相關的,是其精神狀態上的重要轉變。在傳統文學中,神女系列形象的精神狀態明顯地集中于個體的情怨之思,集中于表現纏綿悱惻的情感,人神之間無可奈何的殊途以及由此而來的不絕如縷的精神痛苦。在蘇軾的《神女廟》詩中,即使是作為一方生靈的掌控者,似乎也看不到她的情緒變化。反映在與寫作主體的關系上,神女系列形象在傳統的求偶型、艷遇型等人神關系中,始終是一個“他者”的形象。而在新詩中,女神的精神氣質轉而變為充滿崇高的宇宙大愛的積極樂觀型。她們與新詩中出現的諸如鳳凰、天狗、太陽、大海等意象所反映的內在精神幾乎處于同一位置,并且與寫作主體實現了自我內化,成為了一體。
比如在《日出》、《浴海》、《太陽禮贊》、《新陽關三疊》、《金字塔》等詩中的太陽,就是一個充滿了破壞力和再創造神力的意象。比較其中的詩句,如《浴海》中,“我在這舞蹈場中戲弄波濤!∕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我的心和日火同燒,∕我有生以來的塵垢、粃糠∕早已被全盤洗掉!”“太陽的光威∕要把這全宇宙來熔化了!”“趁著我們的血浪還在潮,∕趁著我們的心火還在燒,∕快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全盤洗掉!∕新社會的改造∕全賴吾曹!”很明顯,抒情主體“我”和詩中的“太陽”實為一體。《天狗》中也是如此。“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脊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筋上飛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大量強烈力度性動詞的使用和急促的排比句式,又不斷肯定著創作主體意欲抒發的內在情感。詩人使用的“太陽”、“天狗”等意象與抒情主體之間,不分彼此,并不存在著“他者”的關系。
回首再比較《女神之再生》與《鳳凰涅槃》二詩,也可以很明顯地認識這種意象之間的同一性。在它們的開篇,前者有共工與顓頊的爭帝,傳來不和諧的喧嚷之聲;后者鳳凰出現時的背景則是梧桐枯槁,醴泉消歇,大海浩茫,平原陰莽,冰天凜冽,都呈現出一個黯淡晦冥、秩序混亂的背景。傳說中修煉五色石補天的女神(女媧),在漢民族文化中象征著吉祥、高貴、神圣的鳳凰,都具有作為中心秩序的整頓者的身份。只是前者在新詩中是以創造一個新世界的神祇的面貌出現,而后者在新詩中是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實現新世界(包括自己)的光明、和諧、歡唱。從這一意義上說,閱讀者所接受到的“女神”意象和“鳳凰”意象,其內在的精神氣質不分彼此,都充滿了對世界更新的強烈的意愿。從詞語使用情況來看,在《女神之再生》中,女神的歌詠中“我”和“我們”共出現16次,在鳳凰的歌唱中,則共出現49次。無論對于閱讀接受者而言,還是作為吟詠的表達者而言,“我”、“我們”這類帶有強烈集合性及呼喚意義的詞語,在使用中不斷淡化著寫作主體與他所借助的表達對象之間在空間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距離,與寫作主體實際上合而為一。
楊勝寬先生曾就《女神》中出現的文學意象進行分析,指出“女神”作為詩人自我的化身,也作為人格的象征,被詩人賦予創造太陽、創造宇宙的能力,在天、地、人的三維結構中居于最為重要的地位。他還結合郭沫若在解釋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時的話,指出《女神》中“我”與天地萬物平等如一,而且天地宇宙為“我”所用。女神創造太陽、鳳凰“火便是我”的高唱、對地球“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的比況,都是其泛神論思想中“我即神”的藝術體現[7]。這一分析也充分說明學術界對女神這一中心意象與寫作主體的關系的認識。
三 滲透著新文化思想的詩性必然
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理解當年郭沫若在選擇新世界的破壞者和創造者時,使用的是女神的形象,這固然如他在《女神之再生》的前言中引用歌德的詩句“永恒之女性,領導我們走”,將女性視為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過程中精神指引的崇高力量有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的創造的神,諸如女媧、蘇軾《神女廟》中的形象的繼承,但更多的是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過程中,對傳統女神文學在題材和主題上的革新。這種革新究其原因,極具時代色彩。除了與“女神”相似的“神女”形象能夠喚起漢文化群體共同的情感和文化記憶,滿足新生的民國國民對于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回憶與夢想以外,新的“女神”形象也開啟了二十世紀20年代受新文化思想激勵,渴求新時代精神的文化階層,在中華文明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對于文明引導力量的文化想象。
這種想象,在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中,一方面表現為“對過去的新發現”,即賦予女神創造者的身份,并在詩中加以不斷的強調。這一認識,即顛覆、重塑世界的力量向女性轉移,是與時代的認識潮流相呼應的。民國以來,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在社會生活領域中,有關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變化對于時代的心理沖擊力尤為強烈。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可以很輕易地在當時的各大報刊上發現男女共同發布的同居的聲明、解除同居關系的聲明,說明至少在社會的某一階層或某一類群體中,已經越來越將女性視為平等的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對于女性的重新發現。那么,在文學領域,英雄神祇的形象也由原先更多地由男性的、外在的、力量性的,開始轉化為女性的、社會內在的、精神性的形象。因此,帶有明顯古典人文色彩的女神形象的轉型,在“五四”時期的話語方式中能夠表現出非常的時代性號召力量。這印證了接受美學的觀點,“新的文本為讀者喚起熟知的早先文本的期待視野和規則,那樣,這些早先的文本就被更動、修正、改變,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創作了。”“這種文學—歷史參照系的客觀能力的理想范例是那些喚起讀者期待視界的作品,這種期待視界僅僅是為了一步步地打破它自己……能夠自身重新產生詩的效果。”[8]這也是在“五四”時期,用中國傳統的神話資源貫連起這一時期的轉型話語的重要原因。包括郭沫若在內的許多文學創作者有意識地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文學的現代化敘寫。無論是郭沫若其后的系列歷史劇創作,還是魯迅的《故事新編》,以及朱湘等人對于古典詩風的繼承和發展,都反映出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想象的傾向。
另一方面,這種想象還表現為在詩歌中“對西方文明的引入”。這種引入在女神形象的塑造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以女神的數量為例,在漢民族的文化記憶中,不論是神話傳說中作為創造神的女媧,還是后來通過文學創作而流傳的神女形象,在其流傳的經世文本中,都是以個體的形象出現。(六朝以來的女性游仙形象時常群體出現,但從其神性、功能及地位上看,都不具備前二者那樣的典型意義。)在郭沫若的《女神》中,女神出場之初,則由單一之數轉為群體性形象。“女神各置樂器,徐徐自壁龕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面對共工與顓頊爭帝的亂局,是集體性的思索及行動。“姊妹們呀,我們該做什么?”出現三個女神分別說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其他全體隨之共同呼應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從詩歌場境來看,這些女神彼此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這種神性上的平等及數量上顯而易見的變化,極易讓人聯想起以希臘神話為中心而雕塑的面貌相似,體態、服飾差異不大的眾多女神群像。
另外,關于女神口中“新造的葡萄酒漿,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之語,也泄露出這種將西方文明因素與中國古典神話相結合的傾向。眾所周知,葡萄從西而來,其引入是在西漢時期,釀造葡萄酒,以及以皮囊作酒器都不是漢民族農耕文化的代表性生活內容。將西方詩歌中常見的“葡萄酒”引入新詩,除了受20年代前后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將中華文明的起源附于西方的文化影響以外[9],應該也有詩人郭沫若順應閱讀接受群體對于詩歌內容明顯的心理取向和強烈的時代需求,有意識地將以“葡萄酒”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符號放入詩句中,在閱讀者中激發起關于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向西方文明靠攏的詩性想象。
也就是說,女神形象的轉型,對于受單一審美慣例影響從而形成相對凝固之勢的藝術視野并培植出比較固定的心理結構的接受主體來說,其“再生”的意義非常明顯。
比如,在《女神》詩集中,對熟悉事物的陌生化體驗,以及對新世紀新事物的吸收,成為這一創造過程的必要組成部分。有關“科學”用語及西方現代文明意象頻頻出現,如“振動數”與“燃燒點”等用語[10],《天狗》、《光海》等詩中有關天文學、現代物理學、現代醫學所反映出的現代科學意象,輪船、火車、摩托車等工業文明的意象,閃耀著開放眼光的世界性人名、地名意象[11],甚至有對工業港口“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筆立山頭展望》)這樣的深情吟詠,都反映出20年代的文藝與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時代主題之一——“科學”緊緊呼應。用“女神”這一語言符號構筑的帶有“群”的意義的中心意象,迥異于古典文學中的自然意象和人文社會意象,正是新文化思想滲透的詩性必然,反映出當時的詩歌創作者與接受群體之間對中國向現代文明國家快速轉型的共同的熱切渴望。
綜上所述,郭沫若新詩集中女神這一“新”的形象,既如詩歌文本中所表現的那樣,承載著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時代使命,也為熟知傳統女性神祇經典形象的文化階層建立起一個承載抒情記憶與浪漫夢想的詩歌通道,更通過女神“新”的轉變,表達出受新文化思潮影響下的20年代的社會群體對于現代文明國家的企盼情緒。
:
[1]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73.
[2]溫儒敏,李細堯.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葉維廉比較文學論文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68.
[3]聞一多.神話與詩·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A].聞一多全集(一)[M].北京:三聯書店,1982.
[4]鐘來因.《高唐賦》的源流與影響[J].文學評論,1985,(4).
[5]陳寅恪.讀鶯鶯傳[A].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M].北京:三聯書店.2001.111.
[6]蘇軾.蘇東坡全集·續集·第一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7]楊勝寬.太陽 大海 女神——《女神》文學意象分析[J].郭沫若學刊.2007(1).
[8]堯斯.文學史向文學理論的挑戰[A].蔣孔陽.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下)[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480.
[9]顧頡剛.古史辨[Z].北平:樸社印行.1926.
[10][日]橫打理奈.《女神》中含有詩意的科學用語.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9,(1).
[11]張建鋒.郭沫若《女神》意象體現的文化精神[J].成都大學學報.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