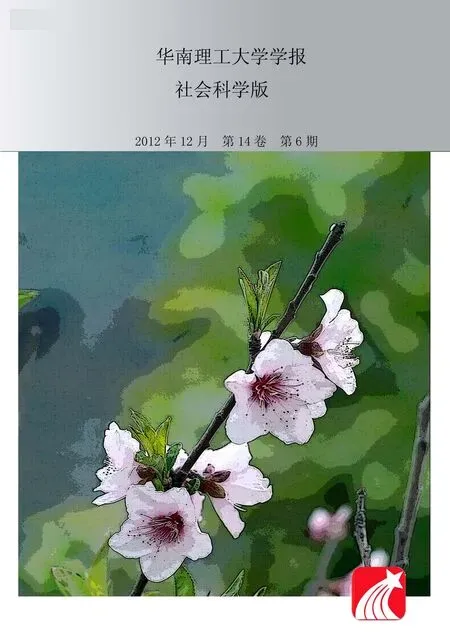電信網互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分析及其借鑒
陳小龍
(武漢大學法學院,武漢 430072)
隨著電信業從壟斷走向競爭,電信業便從獨家經營邁向多點開花的競爭格局。有了不同的電信運營商,其網絡和業務之間就需要實現互聯互通,才能使不同電信運營商的電信用戶享受跨網絡的通信服務。由于電信網間互聯互通直接關系到企業切身利益,因此,各電信運營商在網間互聯過程中發生爭議是在所難免的。發生電信網互聯互通爭議(以下簡稱互聯爭議),爭議方能否直接向法院起訴?這就是互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問題,即發生互聯爭議時,法院是否擁有直接管轄權?本文試圖對世界各國法院是否擁有對互聯爭議的直接司法管轄權進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可供我國相關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議。
一、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模式
(一)互聯爭議的處理程序
介紹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模式繞不開互聯爭議的處理程序。互聯爭議的處理程序不同將決定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模式各異。由于電信網間互聯直接關系到企業切身利益,而且涉及技術、經濟、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互聯談判及實施工作中可能會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加上相關的法規和技術規范不可能面面俱到,各電信業務經營者在網間互聯工作中發生爭議時在所難免的。[1]44按照我國《電信網間互聯爭議處理辦法》第二條的規定,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因互聯技術方案而產生的爭議;二是因與互聯有關的網絡功能及通信設施的提供而產生的爭議;三是因互聯時限而產生的爭議;四是因電信業務的提供而產生的爭議;五是因網間通信質量而產生的爭議;六是因互聯費用而產生的爭議;七是其他類。日本將網間互聯爭端分為:互聯費用、互聯設備、互聯設備空間占用、互聯設備安裝、商務合作、土地使用等六類,但也主要集中在互聯費用和互聯設備空間的占用和互聯設備的使用三方面。從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實踐看,互聯爭議也大多集中在互聯協議簽訂過程中互聯費用爭議的討價還價上。
出現互聯爭議時,爭議方應如何尋求救濟?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各有關機構對爭議是如何處理的?這是在分析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模式前必須回答的問題。
對于互聯爭議的處理程序問題,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應當首先申請電信監管構進行協調或者裁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訴,美國、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均是如此。
按照美國的電信監管體制,對電信業(包括互聯爭議)的管理,由通信監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負責州際之間的糾紛管轄,州內的管轄權主要由公共事業委員會(PUC)負責。根據《1996年電信法》的規定,在美國互聯互通爭議的解決程序是:先由爭議方進行自愿談判,談判過程中可以調解。如果談判和調解不能解決糾紛的,可以采用強制性仲裁達成協議。概括來講,美國的互聯互通爭議(包括互聯協議簽訂或履行過程中的爭議)的解決程序共分三個階段:
(1)自愿談判
自愿談判是互聯互通爭議各方訴求仲裁解決糾紛的前置程序,只有談判不成的,才能提起仲裁請求。負有義務的市話電信交換運營商自收到其他運營商依據《1996年電信法》第251條所提出的網間互聯、業務或網絡接入請求后,有權與提出請求的運營商進行談判并簽訂具有約束力的協議。簽訂的協議內容應包括有關網間互聯、各項業務和網絡接入的詳細分項收費安排。當然,任何網間互聯協議應當依法呈送給州委員會。
(2)調解
互聯互通爭議的任何一方均可就談判中的任何一個問題提請州委員會參與,并就談判中產生的分歧進行調解,以解決爭議。
(3)強制性仲裁
負有義務的市話交換運營商在接到談判請求的第135天至160天(均含本數)開始,談判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請求州委員會進行強制性仲裁。向州委員會提出仲裁請求的一方應當在提出請求時提供下列相關資料:未解決的爭議;在這些爭議中各方所處的地位;其他所討論的或尚未解決的爭議。同時,提出仲裁請求的一方應在向州委員會提供相關材料的同一天將上述材料的復印件送交其他相關各方。非請求方應在州委員會接到請求的25天內對對方的請求提出答復并提供其所希望獲得的相關信息。在仲裁過程中,州委員會可以要求請求方和答復方提供為解決爭議、做出決定所必需的信息。州委員會應當解決請求和答復中提出的每個爭議,并應在市話電信交換運營商接到請求不超過9個月的時間內解決爭議。當電信運營商發生互聯爭議時,可以提交FCC進行裁決,如對FCC的裁決結果不滿意的,可以訴至法院。因此,聯邦監管機構FCC、州內監管機構PUC以及司法機關對互聯互通都有管轄權。“國會既不將全部權力授予FCC以制定電信政策,也不運用其權力修訂基本電信法,許多機構因而得以進入電信管制過程。這種制度結構雖然在每個機構適于其決定的問題上提供了某種邊界,但這種邊界是模糊的,因而參與其中的機構可以對之做出不同解釋。”[2]59
美國獨特的法律訴訟文化,在互聯互通領域有相當大的影響。美國的法律對互聯爭議的介入并非直接針對互聯爭議本身,而是通過對其管制機構FCC的司法管轄實現的。比如,美國最高法院曾經于2000年初作出裁定,認定FCC有權規定本地電話的價格(Local Phone Price),從而徹底推翻了美國第八巡回上訴法院(the 8th Circuit Appeals Court)此前作出否決FCC關于互聯互通的價格管制規則(the Interconnection Price Rules)。[3]465
在日本,互聯爭議的解決也是首先經過監管機構的裁決程序。按照日本2001年《電信事業法》的有關規定,互聯雙方就互聯協議的簽訂發生爭議時,可以提請日本總務省進行仲裁。總務省收到一方仲裁申請后,應通知另一方,并給予另一方在合理期間內作出書面陳述的機會。總務省作出仲裁后,應不遲延地通知對方。作出仲裁后,視同與當事方達成了協議。任何一方當事人如果對仲裁作出的互聯費用等感到不滿時,可以自獲知仲裁結果之日起3個月內以另一方(或幾方)為被告提出訴訟,要求增加或減少互聯費用。[4]33-34與美國法律規定類似的是,日本法律也規定互聯爭議方只有對總務省的互聯仲裁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其起訴的對象并非爭議事項本身,而是監管機構的仲裁決定。
德國和新加坡關于互聯爭議的解決程序規定與美國和日本大致相同。但英國的法律規定卻略有不同。根據英國2003年《通信法》的規定,英國通信管制局(OFCOM)也有權介入互聯協議的爭議解決過程。OFCOM鼓勵談判地位平等的企業通過平等協商的方式達成協議,或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互聯爭議。只有當談判一方擁有主導地位而另一方沒有,或者該互聯協議涉及到多方利益的情況下,OFCOM 才會做出強制性裁決。[5]27-30但是,爭議一方將爭議提交OFCOM并不妨礙受影響一方將爭議事項提起訴訟的權利。在英國的互聯爭議解決程序中,監管機構并非前置的必經裁決機構。盡管監管機構也有直接管轄權,但未剝奪爭議方直接向法院起訴的權利。這是英國關于互聯爭議處理程序與美國、日本及其他歐洲國家所不同的地方。
(二)電信監管機構設置模式
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模式又與各國電信監管機構的模式設置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將,電信監管機構模式的設置將直接決定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模式。從現有的互聯爭議處理程序看,電信監管機構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專屬性的或者至少是優先的。這種電信監管機構優先處置的制度設計與各國是否設立獨立的電信監管機構的電信監管體制密切相關。從世界上的電信監管體制看,大多數國家都設有專門的電信監管機構,有政監合一式的,也有政監分離式的,這也是WTO對各成員國的要求。
政監合一式是指國家成立專業的電信監管機構,該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是政府部門的組成部分,如我國的工業和信息化部。政監分離式是指國家成立獨立的電信監管機構,該機構既獨立于企業,也獨立于政府,一切監管權力均來自法律的直接授權。最典型的就是美國模式。美國成立專門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負責整個國家的通信監管工作。FCC是法律授權的獨立于政府的具有準司法性質的通信監管機構。這種模式的機構設置受到世界上眾多發達國家的推崇。比如英國電信監管機構(OFCOM)便接近美國的FCC。另外,在全球電信私有化進程中建立的巴西、印度監管機構也采納了FCC許多元素。
無論是政監合一還是政監分離,這些國家都設置了專門的電信監管機構,這樣包括互聯爭議在內的電信糾紛就都有了專門的處置機構。且電信監管機構往往成為互聯爭議的優先管轄機構,電信監管機構的協調或裁決程序則成了互聯爭議的前置管轄程序。
當然,也有未設立專門的電信監管機構的國家,如新西蘭,當出現互聯爭議時主要由各政府的相關部門,依據反托拉斯法(即反壟斷法)或消費者保護法等法律體系履行監管職責。由于缺乏獨立的電信監管機構,所以在這樣的國家出現互聯爭議時便沒有電信監管機構的前置監管程序。
(三)互聯爭議的兩種司法管轄權模式
從以上對互聯爭議處理程序的制度分析可以總結出目前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兩種基本模式,即直接司法管轄模式和電信監管機構的優先管轄模式。
直接司法管轄模式就是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有權直接向法院起訴。這種模式往往發生在未設有獨立電信監管機構、對電信業采用司法管制的國家,新西蘭便是其中的代表。這種模式下,沒有設置專門的電信監管機構,而是將電信監管的職責分散在政府的相關部門中,通過反托拉斯法(即反壟斷法)或消費者保護法等法律體系履行監管職責,從而直接將互聯爭議交給了法院。這種模式一般適合于人口不多、市場化程度比較發達的小國家。當然,在設有專門電信監管機構的英國,法院也擁有對互聯爭議的直接司法管轄權,同時也保留了電信監管機構的直接管轄權。法院和監管機構誰優先,法律并未直接規定,而是將選擇權給予了爭議方。
電信監管機構的優先管轄模式是指,當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必須首先將爭議提交電信監管機構裁決,對其裁決不服的,方能向法院起訴。這種管轄模式的特點就是,對互聯爭議的解決給予了電信監管機構的優先裁決權,從而排除了法院的直接司法管轄權。采用這種制度設計的國家,往往設立了專門的電信監管機構。
從世界各國的電信業改革歷程看,電信業是一個由長期處于壟斷逐步發展到市場競爭的過程,客觀上培育了電信監管機構對電信行業的壟斷或者優先管制局面。因此,電信監管機構對互聯爭議的優先管轄模式是目前世界上比較通用的模式。
二、我國電信網互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一)我國電信網互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現狀
介紹國際上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模式是為了能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欲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就必須首先分析我國互聯爭議的現狀,并查找我國現狀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我國法律對電信網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是如何規定的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以下簡稱《電信條例》)第21條的規定,電信網間互聯雙方在互聯互通中發生爭議的,依照本條例第20條規定的程序和辦法處理。《電信條例》第20條是關于網間互聯爭議的處理程序,核心內容就是互聯雙方發生爭議的,應向電信監管機構申請協調解決,協調不成的,由電信監管機構組織電信專家組進行論證,并根據專家組的論證結果作出強制實現互聯互通的行政決定。我國關于互聯爭議處理程序的法律規范中并未明確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即未明確規定爭議方是否具有直接起訴的權利。但從上述兩個條文隱含的意思來看,似乎要求互聯爭議方將爭議首先提交給電信監管機構解決。
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似乎不愿意受理互聯爭議。2000年7月13日,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和中國電信集團海南省電信公司就IP電話網接入的互聯協議發生爭議,前者以后者違反雙方互聯協議為由訴諸法院,一審法院以“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原告提起的互聯爭議之訴,爭議方也不能對電信網間互聯糾紛提起民事訴訟而只能提起行政訴訟”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亦認為即使雙方屬于合同糾紛,按照《合同法》第123條的規定,雙方的爭議應按《電信條例》的規定提交電信管制機構解決,維持原判。[6]117-119
法院的判決從法理上是說不通的,有“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嫌疑。《合同法》第123條規定,“其他法律對合同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就算《電信條例》對互聯協議有特殊規定,但作為行政法規的《電信條例》并不屬于“法律”的范疇,故不符合《合同法》第123條“法律另有規定的”要求。事實上,只要雙方的互聯協議并未違反《電信條例》的強制性規定,合同未因違反《合同法》第52條而無效,那么,雙方的互聯協議理應屬于民事糾紛范疇。況且,引用《合同法》進行判決的行為恰好證明了雙方的互聯協議受《合同法》的約束,理應屬于法院管轄的范疇。當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三項的規定,“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由其他機關處理的爭議,告知原告向有關機關申請解決。”即法律規定應由其他機關處理的爭議,法院不應受理。雖然《電信條例》第20和21條規定了互聯爭議的特別處理程序,但其法律位階屬于行政法規而不是法律,因此,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11條不予受理的范圍。
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法律并未排除法院對互聯爭議的直接管轄權。當然,如果將來《電信法》中亦對互聯爭議的處理設置了特殊處理程序的話,法院可以不予受理此類爭議。然而,法院不愿受理互聯爭議在我國司法實踐卻是事實,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二)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對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規定是模糊的,法院的做法是不予受理互聯爭議,直接放棄了對互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一是法律規定不明確。從現有的《電信條例》及相關的配套規章來看,法律雖規定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應向電信監管機構申請協調解決,但并未明確這種協調解決申請是否為法定的前置程序。同時對爭議方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未作明確規定。
二是電信監管機構仍存在優先監管的趨勢。我國電信業的改革也是從壟斷逐步走向競爭。電信業的長期壟斷局面同樣造成了我國電信監管一直處于內部監管的局面,從而造就了電信監管機構的優先和壟斷監管結果。雖然我國現在法律上已向外資開放,但從現有市場上基礎電信企業國有資本仍唱獨角戲的局面看,脫胎于這些國有企業的電信監管機構的優先或壟斷監管局面短期內仍無法得到根本改變。
三是法院有意排除直接司法管轄。從前文所述案例來看,我國法院對于互聯爭議案件不愿直接管轄,除了電信監管機構的強勢監管地位給其造成的壓力外,更重要的是法院沒有直接管轄的動力。一來我國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處理案件的任務繁重,顯然不愿主動“攬活”,二來互聯爭議一般涉及到電信技術和業務問題,法院管轄起來會面臨很多技術上的障礙,無疑大大增加了法院的畏難情緒,因此,可以說我國目前法院在法律并無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對互聯爭議是主動排除了管轄權。
三、完善我國電信網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建議
如何將國際上的先進做法引入我國的法律制度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本文從三個方面提出完善我國互聯爭議司法管轄權的建議。
(一)要厘清行政管轄與司法管轄之間的關系
由美英等發達國家發展而來的電信監管機構優先處理互聯爭議的模式,皆因電信管制長期處于封閉壟斷狀態滋養出電信監管機構的監管特權,從而導致司法管轄權排在電信監管機構管轄權之后的局面。對于互聯爭議的處理,電信監管機構和司法機構之間的管轄并無孰優孰劣之分,二者都是處理糾紛的法定機構,且各自的處理程序和權限也不盡相同。因此,在對互聯爭議管轄方面,行政管轄和司法管轄應各司其職,不宜設置優先管轄。
從我國現有法律制度設計看,對互聯爭議的行政裁決權似乎也是專屬性的。我國《電信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互聯爭議任何一方可以向電信監管機構申請協調解決互聯爭議。監管機構應當按照技術可行、經濟合理、公平公正、相互配合的原則進行協調。協調不成的,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論證。監管機構將依據專家論證的結果強制實施互聯互通。可見,按照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須向行政監管機構尋求行政裁決,并未給予爭議方向法院直接起訴的權利。當然,爭議方對監管機構的裁決不滿的,可以向法院起訴。但此時的訴訟對象是監管機構的裁決行為,屬于行政訴訟的范疇。
因此,對于互聯爭議的糾紛處理,法律應該厘清行政管轄和司法管轄的關系,不能含糊。筆者以為,有必要修改我國《電信條例》的第二十條的規定,避免給人造成誤解:互聯爭議只能向電信監管機構申請行政裁決。或者在將來的《電信法》中對此進行完善,明確電信監管機構對互聯爭議的處理僅是一種普通的行政管轄,不排除其直接法院起訴的權利。
(二)須完善相關立法,給予法院對互聯爭議的直接司法管轄權
電信監管機構長期壟斷了對電信行業的管理,因此,對互聯爭議的管理,法律給予了監管機構的優先管制權。即使在美國這樣競爭法律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仍然是將互聯爭議的優先處置權交給了FCC,對FCC的裁決不滿意的,才訴至法院。法律對互聯爭議設置了監管機構的前置處置程序,實際上是在維護主管機構的監管權威,也是處理特別法與普通法關系的一種必要選擇。否則,一旦發生互聯爭議就直接向法院起訴的話,主管機構的處理職責實際上就被架空了。
這樣的制度設計雖有其合理性,但從爭議方來說,既然互聯爭議屬于民事爭議的范疇,法律就不應剝奪其訴諸法院的權利。一旦發生互聯爭議,是向行政機關提請仲裁或裁決,還是直接向法院起訴,理應由爭議方自己決定。一旦剝奪爭議方直接起訴的權利,實際上是增加了爭議方解決問題的成本。雖然許多國家的法律規定對行政機關的裁決不滿意的可以向法院起訴,但畢竟經過了一道行政裁決程序,對于爭議方來說不但要付出額外的經濟成本,還要負擔更多的時間成本。而時間上的成本往往比較大,因為網間不通的話,對運營商的業務收入將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時間拖的越長,損失越大。因此,對爭議方來說,應該給予其自由選擇權。如果其對行政機關的處理效率滿意的話,就可以選擇向行政機關申請裁決;如果其對行政機關的處理不信任,就應該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而無需等到行政機關裁決后再起訴。
因此,在將來的電信法中,應該規定:當發生互聯爭議時,爭議方可以將爭議提交電信監管機構進行裁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就裁決結果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爭議方也有權直接將互聯爭議提交法院進行司法裁判,而無須事先經過行政裁決。取消行政機構的前置裁決程序,將申請裁決或提起訴訟的選擇權交給爭議方。
(三)無論從司法實踐還是現有法律理解法院均應受理電信網互聯爭議
法律的修訂或完善畢竟需要經過漫長的論證過程及復雜的程序。制度設計也往往反復的論證。選擇何種制度并無明確的優劣之分,還需實踐的檢驗。新技術的發展可能催生新的法律制度的誕生。因此,法律制度的探討和法律的制定永遠都在追趕現實的腳步。在我國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完善的當下,如何做取舍,無疑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遍查現有的資料,很難找到因互聯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案例,即使有也會以法院不予受理告終。看來,欲將互聯爭議納入直接的法院管轄范疇,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司法實踐毫無作為。從前文所引的海南法院處理海南兩家通信公司的互聯爭議案例看,雖然最后以不予受理告終,但起碼已經讓法院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
筆者以為,法院大可不必對互聯爭議的案件有畏難情緒。盡管有技術上的困難及案件量大的現實壓力,但這些不應成為法院遠離電信網互聯爭議案件的理由。邀請技術專家論證完全可以解決互聯爭議案件技術上的問題。至于案件量大的問題是當前中國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問題。況且,從現有的《電信條例》關于互聯爭議特殊處理程序的規定,并不排除互聯爭議雙方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在電信基本法律尚未出臺的現實狀況中,我們可以理解法院對互聯爭議應該具有直接的司法管轄權。至少從現有法律規定看并未禁止這一點。從有利于糾紛的解決、更進一步保護爭議方的合法權益出發,建議我國法院受理互聯爭議的起訴。這樣做除了可以拓寬爭議方的救濟渠道外,還可以為法院積累審理此類案件的經驗,為以后法律確權后審理互聯爭議案件打下基礎。
[1]信息產業部電信管理局.電信網間互聯管理[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8.
[2]Gerald·W·Brock.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Cambrid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白永忠.電信業熱點法律問題透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續俊旗.解析日本互聯互通新規則[J].世界電信,2003(9):33-34.
[5]程卓.非對稱管制助推互聯互通[J].中國電信業,2007(5):27-30.
[6]婁耀雄.論我國電信運營商之間互聯互通糾紛的司法管轄權[J].法律科學,2005(4):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