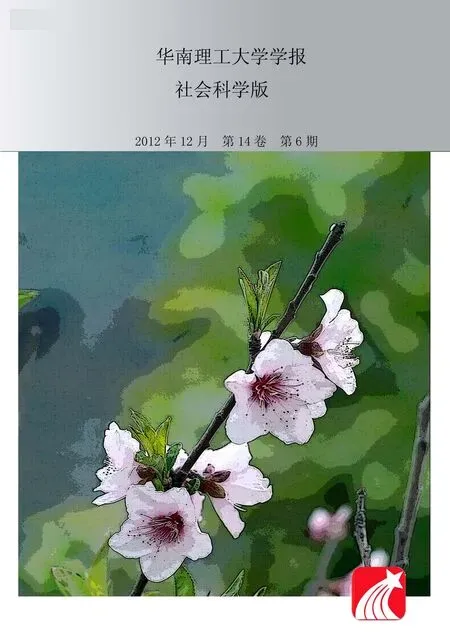魏晉自傳文學的嬗變
劉桂鑫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中國古代的自傳文學,余英時認為“較之歐洲未見得遜色”,其首先提到的便是自傳: “以自傳文字而言,司馬遷的《自序》(及《報任安書》),班固的《敘傳》,王充的《自紀篇》,葛洪、劉知己的《自敘》等都是不折不扣的自傳文字。中國自傳的興起不但遠比西方為早(西方以4~5世紀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為正式自傳之始),而且確實形成了一個傳統。”[1]298-299庾信《哀江南賦序》: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2]94這則材料表明中國的自傳文學,有一個由書籍自序式自傳至詩文自傳、由附屬于正史子書到詩賦自傳的獨立狀態的發展過程。而這個發展過程在魏晉時期得以完成。
一
普遍認為,中國早期自傳始終偏重在“家風”、“世德”方面,不是以作者自我為中心,不能以突出一己的個性或人格為主,其實這種情況更多的出現在正史類的自序中。《史記·自序》以下的作品,如班固《漢書·自敘》、西晉司馬彪《續漢書·敘》、華嶠《譜序》、南朝梁沈約《宋書·自序》、北齊魏收《魏書·自序》、唐初李延壽《北史·序傳》等,“從說明寫作的原委,逐漸變為撰寫者家庭的傳記”,唐代以后,史書由個人撰述轉為朝廷集體編纂,敘傳之類于是消失,“正史的‘自序’中具有自傳意味的,結果只有《史記》可以入選。”[3]23子書類自序式自傳,卻自東漢起便以突出自我為中心,而至葛洪《自敘》標志著純粹自傳的成立。*子書類自序可分為兩類,一是自序,一是自傳。本文僅討論第二類。
王充《論衡·自紀》一般認為既是作者自傳,也是全書總序,這個看法不太準確,《自紀》主要還是一篇自傳。王充在《自紀》中歷述自己的家世、生平、志趣、操守和思想等,此具有自傳因素可不待論,而大量篇幅所討論的文學觀點,并不專為說明《論衡》一書,也涉及他的其它著述。《自紀》篇在說明何以作《譏俗》、《節義》、《政務》、《論衡》、《實論》后緊接著便分幾大段討論何以“充書形露易觀”、“違詭于俗”、“不能純美”“稽合于古,不類前人”、“文重”等問題,可見顯然不專為《論衡》一書而設,是全面陳述自己的文學觀點,而非《論衡》書序。《自紀》以時間為順序歷述自己的生平事跡,中間相應地敘論自己的著述,跟一般自序先敘生平后論著述不同。這種不同表明王充是把自己的著述,包括著《論衡》當作自己一生的重要事件、事業編進自己的自傳里,而不是先敘生平來闡釋著述的原委。
《自紀》之后有代表性的是曹丕的《典論·自敘》。《自敘》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自敘》和《典論》正文所呈現的自我形象形成強烈的反差。《自敘》以炫耀的語氣津津樂道于自己的騎射、擊劍、持復、彈棋等技藝,持復彈棋固然純粹是娛樂,而為了證明自己騎射擊劍的能力,所舉之事為隨曹操出征,軍敗,“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為畋獵“弓不虛發,所中必洞”,為宴飲酒酣耳熱之際,以甘蔗代劍也他人校技以助興等等,而不提及自己的軍功,不提及這些軍事技能對于自己軍事行動的功效。這表明曹丕想突現自己非常生活化的、多才多藝的、富于游戲精神的一面,他注重的是自己所擁有的才能本身,而不是這些才能究竟有何作用。但《典論》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則嚴肅得多。《典論》的內容跟傳統子書沒有什么差別,是一部討論政治、社會、道德、文學等問題的論文集。曹丕在《典論》中曾嚴厲批評東漢末社會“論無定檢”、是非標準混亂的情況,而他把自己的著作取名為《典論》,顯然寄托自己為社會重新制定是非標準、統一言論的使命。該如何理解這種反差現象呢?這并非作者刻意地粉飾或前后經歷的不同而造成的性格變化所致,而是嚴肅與活潑、務實與游戲本來便在曹丕身上統一在一起。他一方面能清醒地區分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手段只有在服務于目的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但另一方面,在一般人僅僅注意于目的的時候,他往往能欣賞手段本身,甚至把一些枯燥無味的手段工具、程序規則創造為可以娛心悅目的娛樂活動。曹丕的這個特點也為一些既實干又富有藝術精神的建安文人所共有。曹丕借子書自序之名行自傳之實,大概是當時的風氣。徐干《中論》無序,很可能是突染疫疾逝世而來不及作,同時人所作序言擔心其書不以自己姓氏命名很有可能導致身死名沒: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繼圣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于今厥字不傳……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4]567這位作者隨即把徐干的名、字、出生地、家庭背景和生平一一做了詳細交待,以補徐子“不以姓名為目”的不足。此可見一時風氣。
葛洪《抱樸子·自敘》標志著書籍自序式自傳的完全成熟。與王充、曹丕相比,葛洪對自己的生平、性格、才能等敘述得更詳細,而且更自覺地突現自己的特點。“從出身和家境來看,王充是寒門,曹丕是王室,葛洪則是先為吳國名門、滅吳后仕晉的所謂亡國的名門,因而抱有一種對寒門、名門意識都十分敏感的復雜心態。在自我認識方式上,王充通過提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來確認自己,曹丕是以自己較之眾人優越來顯揚自己,葛洪則是用強調自己是一無所能的凡庸之輩來把握自己。”[3]46從葛洪對自己的稱呼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自敘》開篇: “抱樸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真實的姓、名和籍貫反而成了號的補充成分。篇中又特意解釋了號的由來: “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樸子,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這顯然是因為葛洪認為“抱樸子”這個稱號比自己的真實姓名更能體現自己的個性。葛洪在《自敘》中提到自己創作《抱樸子》的原委: “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于世……洪年二十余,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但是,這里敘述自己創作觀念的轉變,是作為自己生平事件來敘述,從而構成了這篇自傳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他對《抱樸子》一書的介紹放到《應嘲》等篇中去了。《自敘》篇的結尾特設一問難: “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他的回答是: “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于世”,“故因著述之余,而為自敘之篇,雖無補于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5]684-722這清楚地表明葛洪創作《自敘》是為自己寫篇傳記以冀“將來之有述”,而非作《抱樸子》一書之序言。
二
自傳詩在魏晉有比較豐富的創作成果。東漢末蔡琰《悲憤詩》以第一人稱敘述,敘述者與主人公一致,且也敘及一生重要經歷,已初具自傳詩性格。但正如川合康三所說: “這首詩與其說是自傳,還不如說是一篇傳奇故事。因為較之自傳性,故事性在全詩中更起支配作用。敘述者的感情表現太過類型化了,作為個體的性格,反而顯得薄弱。”“《悲憤詩》是蔡琰這個實際存在的女性,以她自己悲劇的一生為素材寫成的故事詩。”[3]47
嵇康的《幽憤詩》是第一首真正的自傳詩。此詩是對自己為好友呂安辨誣受牽連入獄一事的反省。開頭追敘自己“托好老莊、賤物貴身”思想的形成,中間分析致禍之因在于自己的性格缺陷: “曰余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最后告誡自己要吸取教訓,希望過一種“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發嚴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的生活。[6]122與蔡琰《悲憤詩》相比,《幽憤詩》完全以自身內在的心理變化為主,是一首真正的、同時也是一首非常獨特的自傳詩。這種獨特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烈的自我批判,類似于西方的懺悔式自傳。從懺悔、告白出發的西方自傳,其本質是自我省察,即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然回顧昨日之我,乃知自己之非。作為精神的自我形成史的西方近代自傳,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二是非政治性。嵇康、呂安的入獄,完全是司馬昭、鐘會、呂巽諸人出于狹隘的政治集團利益和睚眥必報的卑劣心理而鍛煉出來的冤獄,但嵇康基本上并未對此等小人或當時之非人政治進行批判。他把致禍的原因歸結為自己“好善暗人”(好行善而暗于知人)的“不敏”,“好善”指“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暗人”指暗于知“民之多僻”。他所說的“顯明臧否”即是劉向所謂的“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說苑》卷十九《修文》)。嵇康自我批判的結果,最根本的一點是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代表著“道”這一最本質特點的放棄,他的后悔,最根本的一點是自己曾經履行了知識分子社會批判這一最本質的責任。因此,嵇康的懺悔,不能理解為對司馬昭的示弱乞憐,也不能理解為一時憤激的違心之言,而是通過懺悔重新確認自己最初的人生理想——“托好老莊、賤物貴身”“無馨無臭”,“頤性養壽”。這里面未嘗沒有明哲保身、珍惜生命的平凡想法,但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種莊子式的“逍遙游”: 實質是徹底疏離政治,在政治之外尋求人生的價值。這才是《幽憤詩》所要塑造的自我形象。潘岳《河陽縣作》(其一)敘述弱冠舉秀才、上宰朝、廁王寮、辭歸東山、再掌河陽縣等事件,以線性的排列展示了一個由昔日掙扎于仕途到現在意在恪守縣務以求名聲的自我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是對嵇康《幽憤詩》的繼承。
左思的《詠史》以組詩形式為自己作傳,是自傳詩的一個重要發展。《詠史》“雖只八首,卻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決心歸隱的思想變化過程。”(余冠英《漢魏六朝詩論叢》)第一首歌唱自己的博學、文才和軍事理論素養,表現自己御外侮、平內亂而功成歸隱的抱負。第二首批判士族憑借門閥制度壟斷顯職,造成“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平等現象。第三首借歌頌段干木、魯仲連表現自己“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這兩首訴說了詩人在仕進受阻、較深刻認識現實后對初衷的堅持。第三首“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云”,初看似是對第一首“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的簡單重復,其實內涵更為復雜深沉。詩人已經褪去了當初的自負幼稚,而對“不羈”的刻意強調,流露著詩人在體味到門閥制度的冷酷后所產生的憤激情緒。第四首把王侯貴族的淫靡享樂生活與揚雄寂寞著述的生活作了比照,肯定了揚雄的立言不朽。第五首前半寫皇都壯麗,侯門深邃,后半寫自己本非攀龍附鳳之輩,而志在追求一種“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高蹈生活。第六首歌頌荊軻,以為人之貴賤非取決于政治地位之高低,市井豪俠遠勝豪右。這三首從不同角度展開對貴族的批判,也展現了詩人不斷尋求人生價值的過程。第七首慨嘆 “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詩人雖仍然以英雄自命,但情緒己頗為無奈,無復過去的自負和高傲。第八首先以“籠中鳥”喻自己仕進的屢屢受挫,以“枯池魚”喻自己末路處境,再以“達士”之知足寡欲自慰,流露著十分絕望的心情。《晉書·文苑傳》: “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7]2376此二首正反映了左思晚年絕意仕途的心境。
陶淵明是第一個成熟的自傳詩人。《五柳先生傳》“頗示己志”一語是陶淵明對其自傳文學思想的自白,也揭示出其詩歌自傳的特質。他許多詩歌的標題明白地交代了寫作時間和寫作緣由,這說明他愿意將自己的真實生活公之于眾。其詩歌的小序往往有同樣的參考價值。通過陶淵明如此豐富細致的敘述,我們很容易在這種傳記式的文學場景中結撰出陶淵明的傳記,而無須太過依賴史傳。以角色敘事抒情為典型特征的樂府詩,在陶淵明的筆下也呈現出強烈的自傳性。兩漢樂府詩以反映、批判社會為其特色,人物角色化、類型化,雖說曹植的樂府詩帶有更強烈的個人色彩,但是曹植樂府詩所描繪的游俠、游子、女子形象,本質上仍然是虛擬的角色,絕不能與本人等同,即使其中融入了詩人很多的情感體驗。而陶淵明敘述的卻是一個真實的自我,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發念善事,黽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后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8]108詩從結發時說起,結發如何,弱冠如何,始室如何,目前如何,意在總結平生,反省自己一生饑寒交迫、艱苦備嘗的根源。既表明了天道鬼神不可憑、善事不可為的憤慨,也表明了自己非以安貧邀名的心跡。又如《擬挽歌辭》(三首),或設想自己死后情況與心情,或以第三者眼光觀察死后之自己,以及周圍之人之事。這種寫法可追溯到阮瑀《七哀詩》,陸機《挽歌》(三首),“但這些先前的詩作,并不一定是寫作者自己的死,而是作者化身為詩中的登場人物,詠嘆抒懷。在‘挽歌’這樣的樂府作品中,作者、歌者和登場人物,是可以自由換位、隨意往來的,因此即使借死者之口說話,讀者也不會感到別扭。而陶淵明《擬挽歌辭》的特別之處,就在于他不是詠嘆一般的別人的死亡,而是設想他自己死了,悲從中來,自我哀悼,這種奇思怪想帶來的沖擊,使他具有了區別于以往挽歌詩人的獨特個性。”[3]129自傳性實為陶淵明樂府詩的突出特征,也是他對樂府詩的一大改造,惜其所作無多,且又為其田園詩所掩,故略表而出之。
依據自傳的方式,陶淵明的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自己較長時段內的行事來反映自己性格、思想和情感的變化。如《雜詩》其五,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歸園田居》(五首)。此組詩的主題是敘述詩人由世俗生活逐漸融入田園生活、由一個官吏逐漸變成一個農民的過程。陶淵詩自傳詩的另一重要類型是“一種用形象作出自我界定的‘自我傳記’”,“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他的大多數詩歌自傳總是表達了他一以貫之的愿望,即界說自己在生命中‘自我認知’這一終極目的。”[9]15最突出代表為《飲酒》二十首。這組詩,不僅僅是討論仕隱問題,更是討論如何隱的問題,是陶淵明通過潛藏的論辯方式、通過與不同類型的隱士(朝隱、莊園式隱居、佛教化的隱居)比較中確定自我位置的自傳詩。還有《詠貧士》七首,第一首寫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真正能夠固窮的貧士的思想根基,第二首寫自己,以下五首分詠歷代著名貧士,如榮啟期、黔婁、袁安、張仲蔚等等。一方面,這組詩可算是一微型高士傳,陶淵明把自身放置其間,通過這種方式巧妙地把自己評定為可與黔婁等著名貧士媲美的人物。這組詩的第一、二首都提到“知音”這一概念,通過這個概念,陶淵明試圖傳達給我們這樣的信息: 這些人正是他對自己所終生尋覓的志同道合友伴,實際上也就是他自己。另一方面,由于陶淵明在這組詩里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貧士都做了非常具體、個體化的描寫,因此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辨別出陶淵明與其他貧士的不同之處。宇文所安指出: “中國在4世紀和5世紀初產生了無個性的虛構文體——游仙詩、詠物詩、樂府詩。另外還有一種文體……詩人熱烈地談論自己,但不使用普通人經驗中與自我相連的抒情主體——‘我’。這其中包括詠懷詩、雜詩。第三類是場景詩,當詩人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存在,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談論自己的時候——有著他特殊的經驗和對場合的反應以及態度。”[10]119除陶淵明外,魏晉最有成就的詩人,如曹丕、曹植、王粲、阮籍、陸機都基本上可以歸入這類概括性強、無個性的虛構文體,而場景詩自魏至東晉逐步發展,從蔡琰、嵇康、左思至陶淵明,終于發展為成熟的自傳詩。
三
自傳的創作,一般出于兩個基本原因: 一是因自身不為他人理解,甚至遭到他人曲解、詆毀需要辯解; 一是希望不朽。一個有著真正尊嚴的人,他會全力寫出真實的自我,所再三致意的是同時人和后代的真正理解和評價,他拒絕求全之毀和不虞之譽。如果一個作家不能以寫出真實自我為原則,他必須考慮同時人和后代人理解、評價人的不同方式,他會因為不能兼顧這兩者而焦慮,并依據這兩者而塑造相應的自我。
正史的自序,由于史家所代表的過于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立場,即使意在為自己立傳,也無法突出自己的個性。司馬遷之所以首創自序式自傳并表現了自己鮮明的個性,這歸因于他個人屈辱的身世和發憤著述的心理動機。子書作者不同,他的自序是否要表現自我的個性取決于他本人對“自我”的理解。王符《潛夫論·敘錄》開篇即道: “夫生于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無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效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圣亦咨詢。草創敘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11]465以下條列《潛夫論》設立三十六篇的用意而無一語涉及自己身世。王符顯然認為一個人最有價值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個性、感情。與王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充、曹丕、葛洪等人。他們的子書展現他們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見解,自我的形象顯得嚴肅沉潛,但他們的自序卻展現了自我另外的一面: 豐富多彩的個性、才藝,甚至個體的形態。
詩文自傳取代自序式自傳而發展至于成熟,原因很多。首先,作家們找到更好的“自我表述”方式而導致文體的更迭。子書內容豐富復雜,一人一生很難有幾部子書,但詩賦可以抒寫一時一地的情懷,在人生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情境下都可以抒情言志,表現自我。詩賦作為自我表述的方式顯然更簡便更自由。復次,文學的價值得到更普遍的認同,僅僅作為文學家,便具有不朽的價值。復次,作家所要傳達的“自我”發生了根本變化。“在魏晉時期,子書似乎承擔了‘自我表述’的責任,……對中古士人來說,‘自我’或‘個體’意味著作為‘士’的個人生命之精華,而一部厚厚的子書,提煉了這位士人對于社會人生的全部看法,可以最好地體現這種精華。”[12]但另一方面,魏晉又是一個社會、思想大變動的時期,價值趨于多元,而重要的一點便是不再把政治價值視為人生唯一、甚至最重要的價值,政治生活也不再是最有意義的生活,因而作為負載作者經時濟世思想和抱負的子書自然衰落,而意在展現一個性格豐富、個性強烈的自我的詩文自然便獲得極大發展。最后,情感體驗的傳遞是溝通自己與后人的重要鏈帶。王羲之《蘭亭集序》非常自覺的意識到這一點并給予深刻的表達: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13]258
王羲之由自己的生活體驗、通過閱讀與古人發生強烈共鳴的閱讀經驗,領悟到“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所以興懷,其致一也”,領悟到貫穿古今、現在與未來的,使今人能夠活在后人心中的因素: 對于生命瞬息性的哀愁。因為這種哀愁超越“取舍萬殊”(價值選擇的差異)、“靜躁不同”(個性不同),也超越“世殊事異”。毫無疑問,在傳遞、延續情感體驗方面,詩賦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本文限于篇幅,僅能就書籍自序式自傳和自傳詩簡略地探討魏晉自傳文學的發展過程,因為前者最近于現代意義的自傳,后者的研究至今尚頗為寥落。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未能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比如,詩歌歷來以抒情言志為本質特征,當我們注目自傳性詩歌時,會發現除了這類自道己事己情的詩歌外,還存在著一類代他人言情的角色詩,這兩類詩有何異同?魏晉詩歌史上,有一類詩人所擅長的、并憑此而在詩歌史占有地位的恰恰是這類角色詩。如曹丕的游子思婦詩、傅玄張華的女性詩,“太康之英”陸機的擬古、擬樂府詩。玄言詩本質上也是一種角色詩,它的主題是表現一種儒道兼綜的人格,詩人往往舍棄自己的個性,在詩中刻意扮演這種理想形象。[注]劉勰: “江左篇制,溺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 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67頁)錢志熙認為東晉文學的主題為表現一種名教與自然合之的人格。見其所著《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五章。謝靈運“山水詩,每以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逍遙之致,詞氣與詞意,苦相乖違”,[14]427他的這種乖違,實際上也是其刻意把自己塑造為玄遠自然這一時代理想人格所致。如以自傳詩與角色詩這兩種類型為線索,或許能重新描繪魏晉詩歌史。總之,魏晉是中國文化第一次大蛻變時期,也是人的自我個性覺醒和文學自覺的關鍵時期,從自傳文學的角度進行探討,相信對此時期的文化和文學會有新的認識。
參考文獻:
[1] 余英時. 現代學人與學術[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2] (北周)庾信撰. 庾子山集注[M]. (清)倪璠,注. 許逸民,校點. 北京: 中華書局,1980.
[3] (日)川合康三. 中國的自傳文學[M]. 蔡毅,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4] (清)嚴可均. 全三國文[M]. 馬志偉,審訂.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9.
[5] (東晉)葛洪撰. 抱樸子校箋[M]. 楊明照,校箋. 北京: 中華書局,1997.
[6] (魏)嵇康撰. 嵇康集注[M]. 戴明揚,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7] (唐)房玄齡. 晉書[M]. 北京: 中華書局,1974.
[8] (東晉)陶潛. 陶淵明集箋注[M]. 袁行霈,箋注. 北京: 中華書局,2003.
[9] (美)孫康宜. 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M]. 鐘振振,譯. 上海: 三聯書店,2006.
[10] (美)宇文所安. 自我的完整映象——自傳詩[M]//樂黛云,陳玨. 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 蘇州: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110-137.
[11] (東漢)王符. 潛夫論箋校正[M]. (清)汪繼培,箋. 彭鐸,校正. 北京: 中華書局,1985.
[12] (美)田曉菲. 諸子的黃昏: 中國中古時代的子書[J]. 中國文化,2008(1): 64-75.
[13] (清)嚴可均. 全晉文[M]. 何宛平,珠峰旗云,王玉審訂.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9.
[14] 錢鐘書. 談藝錄[M]. 北京: 三聯書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