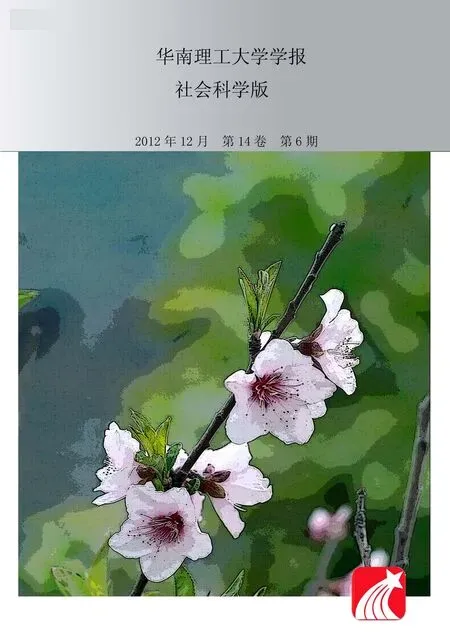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互聯網改變中國”雜談
胡 泳
(北京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871)
一
中國外長楊潔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記者會上,闡述有關中國的外交政策時提出,“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著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
把這段話用來形容有了互聯網以后的中國,也不無貼切。簡單地說,互聯網讓普通民眾都獲得了擁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一瞬間,前所未有的興奮激蕩全身,人們舉起形色各異、長短不一的“小喇叭”,千軍萬馬,千言萬語,其核心特征正如我一本書的書名所說,即“眾聲喧嘩”。
盡管社會弱勢群體伴隨著技術和表達能力的障礙,許多窮困者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聯網,部分人甚至難以接觸到數字媒體,但計算、通信和存儲成本的下降,使中國人口的可觀部分獲得了信息傳播的物質手段。每一個網絡用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發表意見,從而可能為公共討論注入一種想法、一個批評或是一種關注,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履行監督的功能,影響議題和話語。這無疑是互聯網所帶來的社會進步。
二
民族主義問題曾經是中國網絡輿論的起源性問題,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彭蘭教授認為,中國網絡輿論發端的標志性事件是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排華事件后全世界華人(也包括國內)在網上的抗議活動。而《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刊登的林楚方、趙凌《網上輿論的光榮與夢想》一文則認為,“真正以國內網站為平臺來表達民意的標志性事件,則應該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網為抗議北約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而開設抗議論壇一事,這是傳統媒體網站開設的首個時事新聞類論壇。”
曾幾何時,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在中國互聯網上構成歷久不衰的熱點,舉凡中美關系、中日關系、臺灣等話題,總會在網上見到激烈的輿論震蕩,甚至引發線下的群體行動。這個現象受到國外很多觀察人士的注意,《經濟學家》雜志甚至把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放在《電子仇恨的勇敢新世界》的大標題下討論。這個現象到2008年,發展為一個高峰。
2008年以降,在中國的網絡上,民族主義的議題越來越讓位于關于民生的議題。隨著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的浮現甚至激化,互聯網完全被民族主義議題主導已成為不可能之事,換句話說,大家一定會把更多的目光、討論集中到中國社會的發展上。譬如震驚全國的上海膠州路大火事件、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以及橋梁坍塌、地溝油和毒奶粉等民生性議題成為網民們關注的熱點。
三
“網絡社會力”有兩大特點: 一是依網絡而表達,二是憑網絡而組織。它的核心內涵是,人們通過互聯網而學會自治。
社會必須自治,才可能有轉型的基礎。在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看來,“市民社會在國家活動中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它“無須‘法律約束’或強迫的‘義務’就能運轉”。
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的生產”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研究者們對此一直在進行探索。今天,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中國的網絡公共領域正在形成,這是新的社會生長點。
互聯網在建立公共領域方面發揮的作用可以主要歸結為三點: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第三,互聯網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系與集體行動。可以這么說,互聯網社區的創建及其社會參與方式戲劇性地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活,創造了強大的社會資本,產生了積極有效的社會影響。
四
因為互聯網固有地從最終用戶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門人那里生成知識和價值,接入、訪問和發布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內在于互聯網的設計。互聯網治理的政策框架應與此相適應。
中國互聯網要想進一步發展,需要政府與網民共謀利益,共同制訂規則。就政府而言,網民既是監管對象,更是服務對象,主要是服務對象。這就需要調整治理思路,從全能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這樣的政府是沿著“網民-市場—社會—政府”的先后順序來構建政府職能的。
以網民為服務對象,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門必須盡職盡責地滿足公民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要求不同利益集團達成一種求同存異的“重疊性共識”,并允許試錯。為此,要倡導寬容和忍讓,對話和溝通。廣東等地的“網絡問政”可謂開了先河。
簡言之,在一個復雜、動態和多元的環境中,政府很難成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它必須與非政府組織、社區、民眾,協同治理公共事務,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
毫無疑問,服務型政府并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這種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嚴格約束,有固定的范圍、程序,以及明確的責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