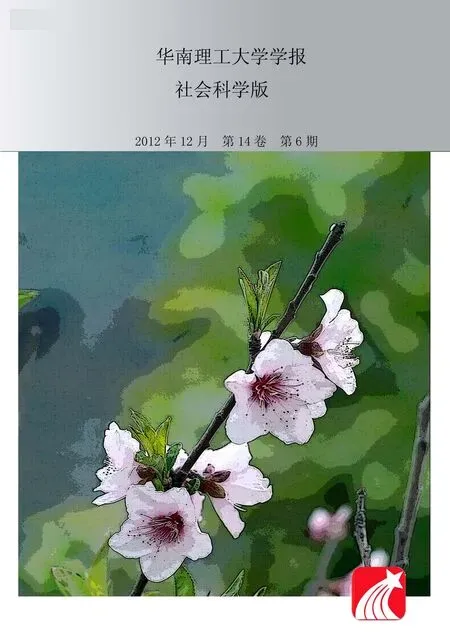網絡文化的內在價值及其呈現
蘇宏元,郭瑩瑩
(華南理工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一
互聯網的興起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文化傳播更為便捷的工具,同時預示著人類文化基本因素的重構,并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文化活動空間,即賽伯空間(Cyberspace)。
賽伯空間一詞源于美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創作的科幻小說《神經漫游者》。這部小說塑造了一個將電腦直接聯入大腦的主人公,描繪了一種電腦聯網把人、機器和信息源都聯接起來的景象,昭示了一種社會生活和交往的嶄新空間。此后,伴隨著因特網在全世界的擴張以及各種在線文化形式的出現,以Cyber為前綴的詞匯迅速流行。與因特網(Internet,一個更為技術性的名詞)、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對因特網的形象詮釋)不同,賽伯空間強調的是因特網的社會文化特性,代表的是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形式和生存方式。因而一時之間成了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網上還出現了專門研究賽伯文化或網絡文化的網站。現在,“賽伯空間”或者“賽伯文化”不如以前那么流行,人們更經常地使用網絡文化(Internet Cultur)這一概念。
二
因特網起源于美國的軍事實驗,阿帕網是其早期的形態,但這并不能掩蓋其自由的探索和創新的精神和“反文化”特色。實際上,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特網作為科技發展的前沿陣地,主要是一群電腦專家、技術人員以及計算機愛好者們醉心的領域,尤其是80年代早期,由于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退出了因特網,發展網絡的核心力量越來越是一些技術精英和黑客。于是,早期的網絡空間甚至被某些研究者描繪成“只有一些身強體健的技術人員才能生存”的一片“蠻荒地帶”(卡勃)//巴洛)。“在這片網絡世界的處女地上,拓荒者們、移民們和定居者們,進行著社會秩序的謀劃,并且已經開墾出一塊塊井然有序的田地。他們的理由很簡單……真正的自然資源只能出自頭腦,只有共享,才能產生巨大的價值”(威特爾)。他們普遍認同的信條是,進入計算機網絡應該是無限制的,所有的網上信息應該是自由的,網絡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的限制[1]266。尼爾森(Theodor Holm Nelson)則概括道: “計算機的目的就是人類的自由。”[2]51自由和共享,正是互聯網精神的終極體現,也是互聯網文化的內在價值。無論是Linux掀起的開放源代碼軟件的新浪潮,還是與技術和市場相關的的“摩爾定律”和“吉爾德定律”,乃至黑客文化的精髓,都與此緊密相連。其實,某些早期的開拓者早已作過大膽的預測和構想: 未來電腦網絡的發展,將超越傳統的、真實的生活空間(物理世界)……這個虛擬的電腦網絡,將幫助未來的所有人類,都能輕易地通過這個系統,自由地按意志建立其個人的社會聯系(克里德J.C.R.Lichlider/泰勒Robert Taylor)。[3]89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米切爾(WilliamJ·Mitchell)(1999)則用數字化的磚石建構了一個嶄新的所謂“比特之城”(City of Bits)。這些“虛擬社會”的構想與麥克盧漢的“全球村”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直至尼葛洛龐帝宣稱人類進入“數字化生存”時代,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今日的主流文化”。從某種角度而言,“數字化生存”重構了人類的時空關系,展示了一種嶄新的生存方式、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于是,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宣稱,通過新溝通系統的強大影響力,以及社會利益、政府政策與商業策略的中介,一種新文化正在成型: 真實虛擬的文化。[4]408
隨著因特網的快速發展和商業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網絡原本的自由和共享的精神日益受到威脅,虛擬現實與現實社會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也越來越大。諸多強權力量正迅捷地以法律和技術來“馴服”因特網。創新將再次受到由上而下的束縛,逐漸為網絡所有者、專利大戶以及版權囤積者所控制。[5]與此同時,起碼到目前為止,實踐證明: 域外空間(extraterritorial space)和地球之城(global cities)并不能消除文化之間的沖突和數字化鴻溝的擴大; 網絡傳播并沒有使人類的心靈更為接近; 在信息自由流動的同時,計算機病毒也在悄悄地擴散; 在網絡游戲市場不斷擴大的同時,“網癮癥”正在侵害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諸如此類等等。目前,網絡犯罪、信息系統安全、知識產權和個人隱私保護等都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卡斯特也坦承: 科技的癥結在于科技是人類的折射,而我們并不十分善良。我們丑陋,科學就會呈現出來,造成各種惡果……擺在面前的問題是: 今天我們擁有最有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幫助我們,或是毀滅我們。現在我們做的是后者。[6]
也許我們不必如此悲觀,對人類的理性和智慧應該抱有希望,而且我們無法拒絕網絡時代的到來,也無法否認虛擬空間文化的真實存在。互聯網已延伸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盡管存在著明顯的數字化鴻溝),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影響著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
就歷史傳統而言,中國是一個所謂“超穩定性結構”的“老大”帝國。[7]然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萬里長城已很難阻擋全球化的步伐,也無法隔斷互聯網無遠弗界的延伸。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 2012年7月19日發布的《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已達到5.3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88億),其中即時通信用戶為4.45億,搜索引擎用戶為4.29億,網絡新聞用戶為3.92億,博客和個人空間用戶為3.53億,微博用戶為2.74億,社交網站用戶為2.51億,網絡游戲用戶為3.31億人,網絡視頻用戶為3.50億,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到2.10億,團購用戶規模為6181萬,網上銀行和網上支付用戶規模分別為1.91億和1.87億。這是一個龐大的消費者和用戶群體,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也是社會文化變遷的壯觀景象。
自1978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發生著變化,從牛仔褲、流行歌曲到時裝、美容等等,中國的年輕人總是緊隨著世界時尚的潮流,應和著流行文化的節拍。因特網可以看作是現代生活方式新的象征和隱喻。《華爾街日報》記者晨慧龍(Lisa Movius)認為,因特網一代正在進行他們自己的文化革命。“這場所謂的革命首先意味著尋求‘E生活方式’”。[8]1466毫無疑問,這種所謂E生活方式以年輕人為主體。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顯示,30歲以下人群所占比重為56.8%,30至39歲人群所占比重為25.5%,但報告同時顯示中國網民增長空間正逐步向中年和老年人群轉移,40歲以上人群比重逐漸上升,截至2012年6月底,比重為17.7%(比2011年底上升1.5個百分點)。總體而言,網民在年齡結構上目前仍保持年輕化的態勢。
對于這種所謂E生活方式,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予以分析。有的認為,網絡傳播具有開放性、交互性和虛擬性等特性,因此特別容易吸引追求新奇刺激、社交欲望強烈的青少年網民;有的認為,作為社會的邊緣群體,青少年希望擺脫社會規范的束縛,以此來顯示自身的獨立性;還有的認為這是對中國那種填鴨式的單向灌輸式的教育方式的反抗。無論從哪種角度去觀察和分析,E生活方式和所謂“新人類”已與中國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相去甚遠。
譬如網絡游戲,其仿真性和競技性,融合了互動性、即時性以及不受空間限制等網絡傳播特性,對青少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然而,游戲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類似于玩物喪志和“精神鴉片”的代名詞,被看作是嚴肅健康生活的腐蝕劑,對之持排斥的態度。因此,網絡游戲在中國起步時,不免遭到社會的責難,加上某些媒體對網絡游戲的負面效應大肆渲染,網絡游戲被嚴重“妖魔化”,似乎成了青少年犯罪的同義語。
也有學者和業主站出來“正名”。他們宣稱游戲是生活的需要,網絡游戲是一種正常的娛樂方式,只不過它利用了一種先進載體。 中國最大的網絡游戲商盛大甚至提出了“人民需要游戲”這樣一個頗有點調侃意味的宣傳口號。對于網絡游戲中存在的暴力、色情和賭博誘發了犯罪,有學者認為,電子游戲出現前,暴力、色情和賭博等犯罪現象也普遍存在,即使沒有電子游戲的誘發,其他原因照樣可以誘發犯罪動機。甚至有研究表明,電子游戲不僅沒有誘發青少年犯罪,而且還減少了犯罪。
其實,只是強調網絡游戲的負面效應或者正面作用都是偏面的。網絡游戲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但不能因噎廢食,把網絡游戲視為洪水猛獸,限制網絡游戲商的發展空間,而是應該采取措施予以積極有效控制,尤其是要依靠法律的手段。何況許多網絡游戲作品不僅僅是信息與傳播技術的產物,也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其高度的創意和精妙的“玩法”體現了人類的智慧和靈感,也有助于智力本身的訓練和開發,只是以“游戲”的形式。
再譬如微博,因其高度的開放性、速度優勢以及簡潔的特性為普通人提供了自我表現和“發聲”的舞臺,因而廣受網民尤其是年輕用戶歡迎。根據互聯網數據中心(DCCI)的數據顯示,19歲及以上國內網民中,微博用戶占88.81%; 近7成用戶擁有唯一賬號,用戶規模趨向穩定; 高頻率訪問微博用戶占據主流; 瀏覽轉發以及發布微博是用戶基本操作,收看視頻、聊天、參與商業促銷活動已成為用戶新的興趣點。盡管名譽侵權、惡意謾罵乃至所謂“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等現象屢見不鮮,但微博同時潛藏著推動新聞業乃至整個社會變革的巨大能量,譬如公民報道和網絡問政等。
四
互聯網是一個多元生成的“千高原”(德勒茲和加塔利語),呈現出相對自由開放的流動性的文化景觀。這兒既充滿了被壓抑的欲望釋放的“快感”,也不乏人性的張揚、現實的關注和理性的思索; 既交織著各種問題、矛盾乃至沖突,也洋溢著活力和生機。
網絡文化呈現出的新特征或者說文化變遷的這種新景觀,既是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開放的結果,也與互聯網傳播和賽伯空間的多媒體、交互性、離散性和虛擬性等特性緊密相關。換句話說,在此傳播技術的因素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互聯網不僅極大地推進了文化傳播的深廣度和速度,而且創造出了新的文化存在形式。
應該強調的是,虛擬空間并不是烏托邦世界,而是現實世界的拓展和延伸。另外,人類對于技術的運用也可能導向不同的結果。作為當代社會一個重要的文化活動空間和“公共領域”,它還在發展和變化過程之中,需要予以進一步觀察。
參考文獻:
[1] 劉吉,金吾倫. 千年警醒: 信息化與知識經濟[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2] Nelson,Theodor Holm.Literacy Online: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Reading and Writing with Computers[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
[3] 劉文富. 網絡政治[M].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2.
[4] 曼紐爾·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5] Lessig,Lawarence.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 in a Connected World[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6] 周燕. 虛擬世界哲學家: 信息時代如何改變生活[N]. 北京青年報,2002-03-11(B8).
[7] 林語堂. 吾國與吾民[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8] Fang Weigui.Das Internet und China[M]. Hannover: Heise Zeitschriften Verlag GmbH & Co KG,Hnov,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