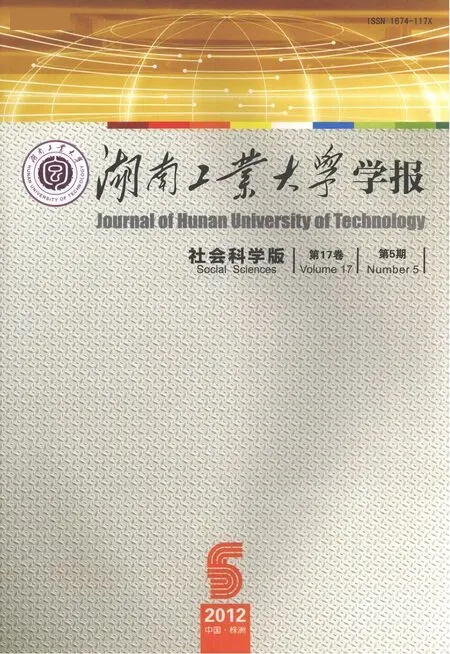沉痛記憶中的村莊敘述——讀王鵬翔的散文集《村莊的背影》
張羽華
(1.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南京210093;2.長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重慶涪陵408100)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一直從事地域民俗風情散文創作的作家王鵬翔來說,他對阿嘎屯高原的抒寫越來越顯示出獨特的創作個性。2009年9月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村莊的背影》就是有力的佐證。散文集試圖為阿嘎屯彝族人民描繪一部民俗志,并用銳利的“觸痛”穿透被現代文明進程所裹挾著的阿嘎屯高原鄉村世界,以殘酷的現實感去記憶模糊的村莊,還原被浸淫的村莊形貌。作為長期躲避在云貴高原深處不為外界重視的作家,他懷抱拯救本土母語文化的情愫和重鑄民族靈魂的責任,把思緒的閃光點聚焦在鄉村民風民俗歷史記憶的坐標上,真誠地記錄著他記憶深處那原汁原味的村莊。在當今城市化逐步蠶噬鄉村的境況下,作者把模糊的村莊由記憶贖回到現實詩化般的心靈世界,于是記憶自然成了王鵬翔《村莊的背影》生命表達的出發點和靈魂的歸屬地。
一 生命情結:村莊風俗民情的詩化再現
對貴州六盤水彝族作家王鵬翔來說,其散文創作似乎有點踏不上時代的鼓點,但他卻義無反顧地把體驗過粘連生命情結的阿嘎屯村莊運用儒雅詩化的語匯、優美和諧的意蘊、揮灑游弋的運筆鑄造成一篇篇優美的詩章。在城市進程“高鐵”化的今天,村莊的背影離我們越來越模糊,散文家尤其是一些少數民族作家也拋棄了族群的記憶,爭先恐后著眼于都市生活的日常性書寫,無情地遺忘鄉村的歷史民俗文化記憶,這對于王鵬翔來說,“在具有極強烈戀土情結的俗民眼里,離鄉背井從來就是一種悲慘、愁苦的處境”。[1]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當今進入全球化機械化時代,不識時務的王鵬翔還一頭扎進農耕文明的最后一塊陣地,飽蘸深情執著地抒寫鄉村記憶的原始風貌,試圖把村莊贖回到靜態的歷史節點,盡情地在阿嘎屯高原村莊揮灑著鐮刀、斧頭、薅刀、鋤頭,播散著包谷、洋芋、豆類、烤煙、蕎子、油菜、胡豆,吟唱著鄉村土地上最勤勞的歌謠,跳著別致的舞蹈。這些物質生活品、民俗民情養育了作家的思鄉情愫,具備積累性的感受以及出自于內在生命的某種訴求的沖動,在作家的筆下遂成為歷史的表達與抒寫。鄉村的農事、節氣、民俗民歌給讀者帶進了久違的阿嘎屯村寨神奇美麗的境地,風俗這條澆灌村莊心田的河流,將永遠在村莊流淌。我以為民族的風俗性比純粹的自然景觀描摹更具備深層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蘊,農事、土地、農具、莊家物語的呈現,殷實了村莊,承載了作家久遠幽深的記憶。《操鐮而歌》寫的不是村民苦難的勞作,而是抒寫鐮刀作為兒童苦樂的記憶,寫鐮刀的形狀,收割的姿勢,伴隨著山歌:“聯妹要聯這一個,翻過丫口遇不著”那種甜美的回憶,滋養著兒童時代的歡樂。割豬草的鐮刀以及平穩樸實的薅刀在農忙季節鋪寫的詩行,印證了農民的艱辛勞作,體現了他們勤勞、質樸、善良的美好品質。“憨厚的鋤頭”鋤著村莊最地道的原生態山歌,“躬耕出大地的詩行”的犁不緊不慢地躬耕在鄉村土地上,抒寫著有韻無韻的詩句。這番民俗景象,活像山澗的一股股清泉直闖進我們的心房,清新而靜謐,又像久違了村莊的臘肉耐人咀嚼。
除了抒寫記憶中的農具以外,作者深情于追憶“人畜共居的村莊”,回溯羊腸般的古棧道,步行,爬坡,身體前傾,踏著石級,沐著山風,聽著悅耳的鳥鳴,這些具有濃郁的鄉村民風古樸氣息,多少顯得厚實、老道。我被作者的記憶招引進三面環山的山間小盆地,慢慢傾聽人畜和諧共處的故事和牲畜們多聲部的合唱縈繞在耳際的余音。《一匹馬奔馳在思想的曠野》寫了馬多年在作者夢想中奔馳,把馬的外形、馬的功用、馬的愛情、人與馬的情感盡情地展露出來,“隔山聽到妹歌聲,隔河聽到馬玲搖。趕馬三年知馬性,跟妹三年知妹心”,這是多么逼真的一副風俗畫,多么浪漫的一首風情詩。《一牛抵半家》寫到牛對村莊農家的巨大作用,還有騸牛悲壯的場景以及牛的脾氣,把生命的情感和人的生存狀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鄉村狗事》意在表明狗在城市和村莊所體現出來的不同價值,彰顯作者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認同感。 《熱熱鬧鬧殺年豬》寫殺年豬的熱鬧場面,家庭親人團聚,洋溢著濃厚的鄉村生活風習和傳統文化意蘊。《雞鳴村莊》寫了雞不僅能夠生蛋——雞屁股銀行,還能夠雞鳴,同時還可以祭祀驅鬼神以保平安。《羊兒滿三坡》抒寫羊的溫順以及村莊的經濟來源,隱隱滲透出作者對羊過度繁殖后對生態破壞的擔憂。通過對人與畜的話語表述,把兩者之間的和諧關系很好地透視出來,展示出一種具有生命氣息的原生態生活方式。
作家把童年生活的村莊體驗與本民族文化經驗、地域文化情愫完美地結合,進而追索精神家園的燭照。鄉村的節氣,任憑時光的沖洗,曲曲折折的排立在村莊生命的河道上,輕盈的微風吹拂著傳自遠古風俗的音符,喚醒作者原生態的記憶。《爆竹聲中一歲除》中過年的濃厚氣氛籠罩著村莊,村民走村串戶,“新年到,新年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兒要一頂新氈帽”,從村童稚氣的口中釋放出的兒歌洋溢著一股充滿活力的生命氣息,村莊上人們忙碌著置辦年貨,打掃衛生,供奉天地神靈,兒童給祖宗磕響頭,青年男女對歌,顯得神圣和莊嚴。另外《五月十五燈滿山》《清明時節雨紛紛》《端午尋藥游百病》《七月半鬼亂躥》《八月十五去偷瓜》也都浸透著濃郁的民間傳統風俗色彩,飽含著作者兒時天真快樂的情緒。
“真正把人們維系在一起的是他們的文化,即他們所共同具有的觀念和準則。”[2]也正因為如此,村莊作為集體的生活場域,事物和風俗仍然維系著遠離村莊的作者。他將村莊觀念性的農事、節氣、風俗破碎的影子重新搜集、拼貼、編織,用原始的語言還原了一個兒時天真快樂的村莊。憑借對鄉村民俗文化深入探究的執著精神,他的思緒始終縈繞著村莊模糊的背影,一個心靈的村莊反復闖進他記憶的牢籠。《熱鬧裝點死亡》寫的是村莊村民死亡后隆重的葬禮,做法事、放河燈、親人哭鬧、舉行葬禮,都被作者濃墨重彩地呈現出來。《紅紅綠綠的哭嫁》說媒定親、哭嫁、完婚,也是一種彝族與眾不同的傳統婚姻方式。《熱熱鬧鬧起新房》中,作者有條不紊地敘述建新房的全過程,讓我們隱隱感受到傳統建筑方式被遺棄的隱痛。
作者對喪葬歌、哭嫁歌、上梁歌、勞動歌、山歌、諺語的描述,并不是對自然純客觀的攝影,因為“完全來自客觀方面的印象是沒有的,事物之所以給我們留下印象,只有當它們和觀察者的感受力發生接觸并由此獲得進入腦海和心靈大門的手段時方能產生”,[3]作者從小生活在阿嘎屯村莊,如果沒有對村莊的真誠體驗,彝族人民的民間信仰和生存方式就不會如此了然于心。“風俗既是現實的存在,又是數千年民族歷史的產物,同時具有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特點;它既是實實在在的物相,又是民族文化意識的載體,同時具有物質性與精神性;它既是某一地域特定生活的表現,‘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征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同時具有地方性與民族性”。[4]春節后的春耕生產,要舉行儀式,擇日期在地里燒香燒紙時所唱的儀式歌:“天無忌,地無忌,年無忌,月無忌,日無忌,時無忌,今日動土,大吉大利”充分印證了村民們渴望來年風調雨順的心愿,以及充滿宗教意味的農耕生活方式。村莊死人時,必須每晚做法事,散花紋,唱孝歌,“輕輕接過花盤來,花在盤中次第開,借問此花因何事,專等我佛下山來,桃花杏花滿樹紅,花香托送亡魂升凈土。說花紋,散花紋,散朵鮮花度亡靈,萬靈度到西天去,逍遙快樂上天庭”,這些吉利的話,企圖在莊嚴悲痛的氛圍中化解主人失去親人的悲哀。又如插科打諢說到,“散花散花,散到對門阿一家,對門那家有個懶大嫂,頭發亂成雞窩草……”很容易引發大家的笑聲,主人家悲哀的心情自然也能夠緩解一些。還有哭嫁歌,主要傾訴父母的養育之恩,體現一種離別時的憂傷和惆悵。比如哭爹媽的“啊我的——媽媽啊,啊我是個呢——姑媽嗎——媽媽啊。人家會養呢——養兒子嗎——媽媽啊。爹媽不會養呢——養姑娘嗎——媽媽啊”,表征了女子哭嫁的獨特文化內涵和她們的人生命運軌跡。還有建新房木匠師傅的上梁歌帶來“爬了大椽爬二椽,兒子兒孫中高官,爬上散椽到梁頭,兒子兒孫中諸侯”的祝福,嗩吶散發出來的“嗩吶嗩吶嗚嗚哇哇,大紅花轎已到娘家。美麗的姑娘要出嫁,苦命的后生亂如麻”的優美凄涼的歌聲,則彰顯出彝族民間文化的豐饒與富麗,反映了阿嘎屯高原特定的人文風尚以及社會風貌。
二 魂靈皈依:村莊歷史物語的詩意表達
記憶猶如巨浪一次次狠狠地闖入王鵬翔久違的心靈空間,無疑會給他帶來精神的陣痛。作為已經生活在城里的他,村莊已成為歷史記憶和靈魂賴以抵達的棲居之地,他在表達對村莊的記憶時難免要經歷撕心裂肺的精神之痛。如果說鄉村的農事、節氣、民俗民歌是對彝族民間文化的拯救、親情的承傳表述的話,那么阿嘎屯地區彝族人民的歷史和親人以及村莊物語、莊稼、花事自然是難以擺脫的靈魂皈依之地。由于記憶的縈繞,面對現代都市生活的瞬息萬變,作者不自覺地存在一種內在的不和諧的精神斗爭,這主要根源于他與村莊歷史物語、莊稼、花事的親密擁抱,源于他的鄉村記憶和現實的抵悟。蒲公英、葵花、桃花、豌豆花、梨花、紅杏、蕎子、馬道、卡子、石拱橋、營盤這些物語在當代散文里似乎消失了,我們很難在當代散文里找到當年老舍養花那種樂趣。王鵬翔努力重振歷史記憶,把阿嘎屯散落一地的風物經過語言符號的組編,給予鄉村歷史風物一次詩化般的重鑄,給焦灼的心靈以溫暖的撫慰。
在《村莊往事》這一組散文里,作者用盡筆墨抒寫阿嘎屯的來歷以及生命之鹽和戰事的記憶。歷史的滄桑在村莊猶如村寨上空的炊煙慢慢散去,引來絲絲情意,唯有對村莊存在進行歷史的挖掘和拯救,才能喚起我們的記憶。在序篇里,作者蠻有情味寫到“我的村莊在高高的阿嘎屯上”,然后講到阿嘎屯的地形、阿嘎屯的歷史。雖然是幾筆模糊的歷史記憶,但也勾勒了村莊的整體圖像。作者富有情味地敘述了明初朱元璋調配移民到貴州屯田戍邊的歷史,還寫到這里屯上的幾座祖墳,以及王氏家族、范氏家族、趙氏家族作為第一代的開拓者的故事,作者對村莊的激情溢于言表。《大茶樹記事》記敘的是充滿神奇色彩、經歷戰火洗禮的神樹。《鹽井記憶》講述缺鹽的鄉民們在鹽井壩挖鹽的辛酸歷程。《遠年的戰爭》描寫吳三桂攻打阿嘎屯時那硝煙彌漫的戰火和血腥慘烈的場景,還寫到咸豐十一年的苗民起義。如今,歷史的戰火已經過去,山歌在山巒上輕輕回蕩,屯上的人民正在用汗水澆灌富裕之花,鋪筑幸福之路。
《鄉村的花事》是作者在《村莊的背影》中苦心經營的一篇篇詩章。村莊沒有花朵,就沒有招蜂引蝶和鄉村繁忙的生氣,也就沒有溫馨多彩的阿嘎屯世界。作者在序篇中寫到“繽紛花事,慢慢成波濤記憶,花的舞蹈,花的歌唱,花語、花香、花色,令我忘情地操筆而歌:鄉村花事!”作者的靈魂歸屬已經抵達鄉村,與鄉村生態融為一起,暫時忘記了作為已是城里人的身份。蒲公英、葵花、桃花、豌豆花、梨花、桂花等瞬間成為他村莊心靈之約的伴侶,一種詩性的純潔之花綻放在作者遭受城市污染的心里,滌除著城市的煩躁,村莊再一次闖進入了作者的心靈空間。
我以為每一個從村莊走出去的人必經過痛苦的回憶,王鵬翔也如此。父輩們操鐮而歌的面容雕塑般幻化在作者的面前,他們激越的歌聲響徹其靈魂,正如作者在文章寫到:“我懷想勞動的快樂,懷想汗珠在太陽下的閃爍……莊稼,給城市中孤寂的我許多溫馨的慰藉。”若是沒有鄉村生活經驗和人生體驗是難以寫出這樣感情真摯的詩篇的。《蕎子》《麥子》等篇章寫得自然、親切,心靈與村莊物語的邂逅,試圖達到一種內在的默契,追求一種精神的和諧。作者把感知物象、體察村莊的自然存在和親人的離世予以情感的鑄造附麗于藝術對象,使詩情和鄉情的沉痛記憶得到巧妙的糅合、融化,顯示出彌足珍貴的藝術質感。鄉村的蛇、喜鵲、鷹、鳥語、蝴蝶、鴿子、炊煙、石磨、石碓窩、馬道,組成了村莊的詞匯,這些感性的形狀和聲音藝術化地呈現出來,充盈著作者高妙的藝術旨趣,正如黑格爾說:“這樣,在藝術里,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呈現出來”。[5]作為村莊的母語,教會了作者思考和抒情,也教會了作者的感恩。他寫到冷冷的蛇對鄉村帶來的好處,他對城里人吃蛇肉深惡痛絕。他還寫喜鵲的勤勞、鷹的勇猛、村莊早晨大自然的天籟之音……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村莊逝去的親人們》這一系列散文。作者從農村走出,走進大城市讀書,畢業以后再到城市工作,都是親人含辛茹苦送出來的,而親人們并沒有享受到城市人那樣的生活。他們依然勤勞,依然質樸,依然深愛著生之養之的村莊。一個山頭地洼,一口黑漆棺材和一座饅頭狀的墳墓就是親人們最后的歸屬。作為遠離村莊的游子,他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那繞不開的鄉村情結始終成為一種痛苦的回憶。他寫到奶奶,寫得非常真誠,寫到了她的勤勞、善良和賢淑。“奶奶”為“我們”三代人的操勞,勤儉節約一生辛苦一生,對“我”幼小時的格外疼愛。他對逝去的親人飽蘸著濃濃的情誼,暗含著絲絲憂傷。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出生于農村后走出農村,在城里生活的那份心情的沉重。當人生走向不如意時,我們的靈魂棲居之地,只有在曾經生活過的村莊才能找到心靈的慰藉。村莊逝去的親人、物語、花事、莊稼、景物甚至鳥的天籟之音都成了我們精神之旅的親密伴侶。
三 生態焦慮:現代性叛逆的刻意抒寫
作為阿嘎屯高原生存的親歷者和體驗者,王鵬翔自覺堅守那份彝族文化民俗風情的守護立場,注重挖掘本民族獨特的民俗風情和文化心理,試圖通過文學的書面話語表達傳承民族民間的生存境況以及人們的文化心理,同時以民俗志的形式抒寫即將被現代文化遮蔽浸淫甚至吞噬的村莊。我們認為王鵬翔并不是固執于傳統的散文題材敘述策略,恰恰相反,他是以本真的態度和執著的精神追求,對母語文化進行自覺維護,在母語民俗文化遭受現代性文化侵略蹂躪時作出本能反抗。當前,我們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化日益遭受侵略,逐漸失去了民族的原生態滋味,顯得蒼白無力,同時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也遭受到無情的破壞,王鵬翔試圖通過散文抒寫來表達自己的反抗,他對當前的民族生態語境透露出無盡的焦慮。而散文集《村莊的背影》著意彰顯的是對現代文明入侵的搏擊和反抗,雖然模糊的村莊記憶對現代性的搏擊和反抗多少顯得力不從心,但他至少拯救了遭受沉重創傷的心靈和對村莊原始養育恩情的歷史記憶。
散文作為作家主體心靈世界的真誠表露,人類話語的自覺抒寫,已經成為當代作家抒發情感的重要載體。但新世紀以來,能夠把鄉村題材真正處理好的作家還不多,以本民族身份抒寫生存體驗的少數民族地區鄉村世界的民族風俗風情、文化生存心理的作家就更少了。追究其原因在于,新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的急速發展,消費主義文化的盛行,使得都市生活話語的表達存在更多的看點。與之相反,當前的鄉村經歷著分娩般疼痛的裂變,少數民族居住區正在經受著現代文明的浸染,大眾媒介的傳播、人員的流動加速了鄉村的現代化,新一代村民脫去了固有的民俗文化底色,彰顯著更多都市化生活情結,因此,執著于散文抒寫的作家如果沒有民族文化身份的切身體驗,要想揮灑自如地表達鄉村情感就顯得多少有些矯揉造作。比較而言,王鵬翔的散文對六盤水地區阿嘎屯高原彝族村莊的抒寫,就顯得老道和厚實,體現出一種對原生態民俗風情的自覺保護意識和守衛立場。
王鵬翔筆下的村莊滲透著對社會大語境的體察與反思,表露著生存的切實體驗,以城市的發展作為參照系,表述著對即將消失的村莊的詩意重構,讓讀者獲得一種真切感人的審美愉悅。作者寫到蘭花躲在村莊背后的深山老菁林里,被迫離開故土,像風塵的女子流落繁囂的城市,被附庸風雅者據為己有,最后消香玉損。
蘭是屬于山野的,蘭是屬于村莊的,蘭被迫近了城市,被噪音吵得無法入睡,被充滿油味塵埃的空氣嗆得無法呼吸,被腳下那一盆人為的水土翻來覆去地煎熬著!她懷念廣闊而高藍的天空,懷念流動的風和陽光,懷念晶瑩甘甜的雨露。蘭犯了思鄉病,不蔫不死才怪呢![6]
雖然作者在話語的表述中并沒有滲入對現代意識和都市意識的強烈抵制,但在潛意識里,他對那些矯揉造作的城市文明是絕然否定的。
當然,我并不刻意在王鵬翔的散文集《村莊的背影》里捕捉村莊風景畫的描繪是如何吸引讀者的眼球的,但他的敘述的的確確喚起了我們對久違的村莊歷史民俗的記憶和反思。讀這部散文集,我們不難意識到作者對當前村莊生態環境遭受肆意破壞時所表露出來的焦慮。桂花樹從村莊消失,流進了城市。狗肉、蛇肉成為城市人的盛宴,村莊的碓窩、石磨被城市的機械化代替,農具漸漸“退休”,農事再也沒有那份熱鬧的場面,民歌已成為一份遺產靜靜地躺在村莊的某個角落休憩。村莊的物語,永遠珍藏在作者的記憶中。他寫到《薅刀在大地上游走》時,回憶當年自己親身體驗勞作的艱辛,吟唱“我曾經無數次咒罵城市,詛咒城市生長的惡之花,懷念鄉村清新樸實的花朵”的情致。然而作者并沒有斷然否定城市,他認為:城市喂養我們缺少營養的軀體,鄉村喂養我們純凈但卻蒼白的精神。作者試圖對即將遺失的鄉村民俗文化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進行重構,并通過堅守本民族的文化習俗陣地,對身處異鄉者給予心靈的安慰和救贖,同時,展示出城市深處中那些曾經有過濃濃鄉村生活體驗的經歷者,對現代都市的觀念行為惡意瘋狂地侵入寧靜的鄉村作出了批判,但不是抵觸、回避、拒斥。
當前,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界認為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少數民族作家創作視野狹窄,固守于狹小的生存空間,沒有勇氣沖破民族文化原生態抒寫的禁區,只顧一味地歌頌和展露民俗風情,缺乏現代性的眼光和批判意識,悖離了現代性的期待視野。[7]不過,把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低迷的原因歸結為少數民族作家缺乏現代性的視野,實在有所冤枉。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與否應該是多重因素所致,我想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王鵬翔散文抒寫根源于他“一只腳踏在城市的胸膛,另一只腳跨在村莊的肩膀”。作為游走在城市和村莊之間的民族文化闡釋者和歌吟者,也注定了他靈魂的不安,“注定了靈魂的躁動,注定了產生記憶和對比”,當然也注定了這本精美散文集《村莊的背影》的順利分娩。對村莊詩意的發掘和抒寫構成了王鵬翔散文的獨特價值,這就是筆者帶著好奇心理解讀王鵬翔散文集《村莊的背影》的原因所在。
[1]黃永林.中國民間文化與新時期小說[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2]魯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18.
[3]桑塔亞納.審美范疇的易變性[M]//蔣孔陽.西方美學通史:第6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82.
[4]周 凡,文德培.當代文學風俗化傾向的美學評析[J].文藝研究,1986(2):57-63.
[5]黑格爾.美學: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49.
[6]王鵬翔.村莊的背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5.
[7]嚴秀英.論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和現代性[J].民族文學研究,2010(1):1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