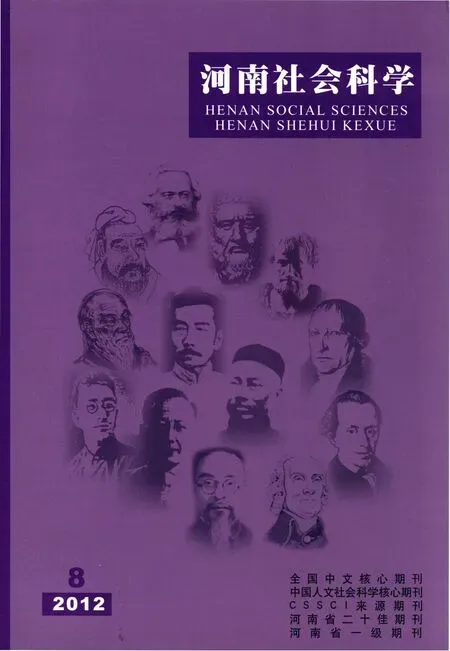試論卡夫卡名作《訴訟》的模糊判決法則
仝志敏
(中原工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7)
試論卡夫卡名作《訴訟》的模糊判決法則
仝志敏
(中原工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7)
奧地利小說家弗蘭茨·卡夫卡(1883—1924),以獨特的創作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被表現主義、意識流、存在主義、荒誕派、黑色幽默及新小說派作家奉為大師[1]。《訴訟》是其標志性作品。它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銀行襄理約瑟夫·K一天早晨突然被宣布“被捕”,但仍可以自由行動和工作,只是在訴訟進行時接受審判。經過一年的“反抗與辯護”,他最終意外地被法庭的兩個代表帶到郊外的采石場殺害了。作品除深刻揭露了司法制度的腐敗和官僚機構的龐大之外,還揭示了一種模糊判決法則。受這種法則約束的個人,隨時都有可能被模糊地抹掉脖子。卡夫卡驗證了這種法則的合法性,也進而挖掘出人類精神世界并非清晰存在卻真實的模糊元素,這一法則與現實法則共同規定著人存在的自由。前者過多地來自內心,法則條文使具有了相當的模糊性與朦朧性。被模糊法則捕獲的人往往有種自尋死路的意味,其中的原罪感、疲勞意識和懷疑及虛無主義始終模糊地控制著人們的靈魂,陷入或違背其中之一,即是觸犯法律。因此,這些痛苦著的生靈只能絕望地勉強生存下去。K即是在這些條文的規定下選擇了近似自盡的死亡方式。
一、圓圈里的原罪
“惡是人的意識在某些特定的過渡狀態的散發。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惡,這惡在我們的眼里卻呈現為感性世界”[2]。卡夫卡不僅聲稱沒有人比他更懂得原罪,而且還用他的寫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個幻想罪惡的文本。《訴訟》即是其中之一。
約瑟夫·K在被劃進了原罪的圈子之后就再也沒有走出來,頭腦中模糊的“上帝/法官/罪惡感”給他戴上了重重的枷鎖,于是他在這固定的圈子里飛快地旋轉直到暈眩和死亡。K本身所固有的罪惡意識在一天早晨被“被捕”事件喚醒后逐漸擴展,從閣樓到業務生活然后到交際的廣大圈子,最后綿延至心靈的角角落落。K在審判之初有幾次不明確的提問,他對被安排在這場訴訟中的處境感到莫名其妙。這些混沌的法官和審判程序讓他難以捉摸,審判的原因、時間、地點和人員都有相當的不確定性。K此時卻把眼光放在揭露法院的腐敗上,這恰恰中了法的圈套,陷入了“上帝/法官”有意或無意劃定的怪圈子。可以說讓K走入法庭的外因是其外部生活的壓抑感或者說是“法院”的作用力。法庭代表賦予K的“罪責”竟被周圍所有的人認同,包括他叔叔、畫家、律師等,他們不是去關心其有罪無罪,而是幫他如何擺脫罪惡,都不約而同地認定K犯了“罪”。這是人類意識的一種想當然的感覺,受其控制,他們在幫助K的過程中不得要旨,使K陷入孤苦無援的境地,成為模糊法則的犧牲品。這樣,模糊的罪惡感就必然成為判決法則的一項條文,因此,個人一旦認識到自己的存在,就都不可避免地會把自己當成一名罪犯。K在尋求“清白”的路途中躑躅獨行,其余的人就都成了他前行過程的自剖者和看客。他們都無法擺脫罪惡,獲得清白。可見,K最終被判決的根本原因是模糊的罪惡感。
模糊不是物質世界具體的個人處境,而是整個群體乃至人類的共同生存狀態。《訴訟》中的審判不僅僅針對約瑟夫·K,也針對周圍的人乃至整個人類。卡夫卡創造了模糊法則,證明了法則條文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他想跳出被“上帝/法”劃定的圈子,改變被圈的無望狀態,只不過他采取的手段是自己設立一個靶子,然后朝它射擊,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這是卡夫卡在更深層次上對這種法則的反抗和力圖超越。
二、疲勞的迷惘
疲勞在《訴訟》中不僅僅是一種身心感覺,更是一種無望的心理狀態,是死神的秘密判決法則。如果跌進這種狀態或違反這種法則勢必要落入判決的口袋。約瑟夫·K逐漸進入狀態時因其不得法的戰爭,使得他在辯護中爭取到的一點點鮮艷色彩都被無端地抹煞掉了。就其結果而言,判決死刑是不可違拗的結局。但他在抗爭路途上出現的點滴希望并沒有得到加強,法院的審判程序搗毀了K的每一個小小的勝利。他走的每一步,即使是為了打探一點點關于案子的進展情況也都要耗盡心血,直至筋疲力盡,陷入難以掙脫的疲乏厭煩之中。這時哪怕有一點點清晰的勝利都可以從無限疲憊之中挽救K。但這些可能有利卻弱小的勝利始終表現得異常模糊,最后都被困乏覆蓋了。K始終處在判決之水的掩埋之下,直到疲勞窒息被判致死,可以說,K根本無法清晰地洞察自己的困難處境。他在疲勞中沒有明確的方向,摸不著頭腦,而從叔叔的幫助、律師的解救,甚至畫家的出謀劃策中都看不出一點希望,每一步努力僅僅在心靈上觸動一下然后又無可奈何地蔫敗下去,其中的“素質”主要是在K身上,最先放棄和最為驚恐的都是他。于是K從根本上順應了人性的弱點:“人的根本弱點不在于他不能勝利,而是在于他不懂得利用勝利……”
K與商人布洛克都是被法勾畫的圈子里的人,布洛克的命運始終處于運動之中,他被法庭判斷有罪之后,耗盡財力精力也沒能洗清罪惡,但他確信活動的效果,承認辯護行為存在的價值,相信結局的圓滿,內心較K清晰得多,除看不到結果之外,還基本上能夠清晰地活著。在布洛克身上我們看不出辯護價值的喪失。K的內心則不同,他除當初確信自己無罪可以擺脫法庭糾纏以外,到審判之后,已經不能再堅信自己能擺脫罪責了,K的自救行動和別人為幫助他而采取的行動都被他盲目地否定了,他已經對這類行為感到疲乏厭煩。K在傾聽畫家的拯救對策時,先是感覺有興趣,后來逐漸辨析出無罪開釋、假無罪開釋和延期審判的矛盾,于是對拯救無限厭煩,匆忙逃遁。他固執地認為:自救和他救已經無法挽回自己的悲慘處境。這些毫無結果的努力只是在默默地損耗自己的能量,身心自然而然地疲勞下去。他以后的苦苦掙扎與悲劇性反抗只不過是生命的一種本能,不代表任何意識。疲勞不斷地接踵而至,它已不是簡簡單單的身心之感,而是更為深刻地凝結為一種符號——痛苦/無奈/絕望/黑暗/目的的喪失/精神的無限困惑。實際上它是一種方向判定的模糊性,一種前途命運的無所指歸和迷惘,因迷惘而疲憊,因疲憊而厭煩,因厭煩而否定自己的活動效果。這樣,每種救贖手段都在疲勞厭煩中戛然而止,如擺脫畫家、解聘律師等。K的反抗滑稽而痛苦,他已經摸索不清法的原則,走不出曖昧的罪行和精神困窘,最后被判決法則死死網羅住。
三、無邊的懷疑及虛無
法要求在其面前必須協和、認同甚至屈服而不是違逆,被法追究的人有其自然而然的終途,任何辯駁和反抗都將被視為悖逆而橫遭“天怒”。
K的懷疑經過了一個不長久的過程,他在開始被捕時確曾產生過懷疑,這對任何一個身處平靜卻突然陷入危險的人來說是很正常的。但他只是對兩個法庭職員的行為和身份表示懷疑,而且這種懷疑也不是漫無邊際的。他此時還是確信自己是清白的,因此這種懷疑只是一種不滿的內心情緒,并沒有罪惡意識附著。但經過一系列外界的折磨,法庭職員身份的確定及行為、初審和周圍人的強烈認定以及苦苦掙扎的毫無結果,直至到了第九章,其懷疑就變得天翻地覆起來,漸漸將存在的價值自我摧殘。
卡夫卡的懷疑虛無主義就表現為此種心理狀態并最終導致目的/結果/存在價值的不確定性。依據這一法則條文,人將走入一個極大的虛空當中,然而這一“虛空”不可觸摸,只是無限模糊無所依附的空間或極端含混抽象的詞語,因此,生命的本能與靈魂的無所皈依將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人的存在就陷入了苦苦掙扎與無奈妥協的兩難選擇之中。約瑟夫·K一方面要活,確定自己的合法自由地位,另一方面又先驗地感覺找不到方向,尋覓不到靈魂的真正救贖路途,如此一來,他只能從屬于這種模糊判決法則,只是漂浮在審判程序過程上的一塊木頭,個人的辯護與反抗已毫無意義可言。
卡夫卡坦言:“……凡是有真正的、耐久的價值的東西,都是來自內心的禮物。人不是從下往上生長,而是從里向外生長。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條件。這個條件……是不斷地通過斗爭去爭取的對自己和對世界的一種態度。有了這個條件,人就能自由。”[2]這與《訴訟》尋求自由的答案是相悖的,約瑟夫·K過多地關注外部世界,想從外部開始擺脫“被捕”的遭際,對于內心的迷惑、精神困境及模糊之法沒有清醒的審視。只是在模糊地采取無效的手段去爭取自由,罪惡意識從外到內逐漸由肉體折磨飄向精神虐待。K沒有清理出爭取自由擺脫罪行的透徹頭緒,內心的模糊性成為前行的絆腳石。可怕的是,他并沒有明確的想法去挪動它,對于精神而言,K已經陷入模糊與朦朧,判決只是早晚的事,所有的行為都成為審判程序的被動協和,奔走、反抗、拯救都僅僅是無效的辯護。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K尋求自由的價值。《訴訟》中K的結局是這樣的:K在兩位執法者的壓挾反抗(本能)著時候,出現了比爾斯特納小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態度完全從本能的反抗墜落到屈服順從:“……K也并不在乎,重要的是他已經意識到反抗毫無意義。即使他反抗,給那兩個人制造一些麻煩,并以此使他的生命延長一刻,那也算不上什么英雄行為。”以后的步伐K都是遷就配合,甚至欣然赴死,直到屠刀進入他的心臟并“轉動了兩下”。如果K反抗,就不會那么輕易地被處死,或許能從他最后的抗辯中體現出存在的價值,然而K的想法出人意料:“K現在清楚地知道,或許應該由他自己來盡這項義務,趁著那把刀在他的頭頂上方傳來傳去的當兒,自己把刀奪過來插入自己的胸膛。”[2]這近乎自盡毫無反抗的死恰恰應驗了卡夫卡的話:“我們僅僅是虛無主義思想,它在上帝的頭腦中慢慢升騰起來,我們是自盡的思想。”[2]卡夫卡用悲劇的腔調揭示了人類精神之法的本質,指出精神世界里的彷徨與無助,渴望在自己創造的法則中超越靈魂的朦朧與模糊。
綜上所述,卡夫卡作品《訴訟》包含一種模糊判決法則,條文是原罪感、疲勞意識和懷疑及虛無主義。原罪感是模糊判決法則之基。因原罪感而感到疲勞,因疲勞而陷入懷疑與虛無,人在這種意識下,喪失了走出困境的決心,模糊了生與死的價值,疲勞、懷疑與虛無由此轉化而來,罪惡意識在模糊法則中決定其他條文,也最終規定人的方向。
人類的合法存在必須在適應現實法則和模糊法則之后才能得以確認,人類的愉悅生存必須遵守現實法則和模糊法則。卡夫卡向后者所做的奔突具有開創性,但對其探索并沒有完成,人的原罪意識、內心的曖昧性、精神的迷惘和靈魂的無所附著決定了人只是一個痛苦模糊的存在,用這些條文來判決人的存在是對人類精神困境的一種超越。但卡夫卡并沒有指給我們解決這一困境的路途,只是讓我們注意到人類精神世界的模糊存在。
[1]鄭克魯.外國文學史(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葉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