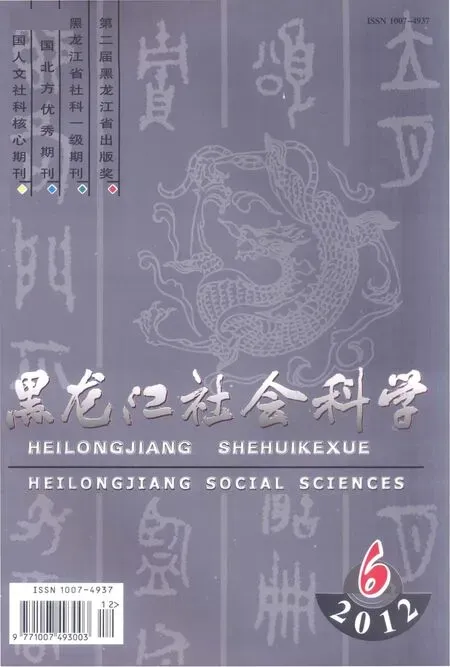圖形—背景理論在唐詩中的認知解讀
(哈爾濱工程大學 外語系,哈爾濱150001)
一、引言
以英國諾丁漢大學Stockwell為代表的認知詩學(cognitive poetics)理論在20世紀末迅速興起。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認知詩學是認知語言學與文學評論相結合發展而成的一種新的作品解讀工具,更加注重讀者在閱讀理解文本過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機制,力圖將一系列與認知有關的語言結構與語言運用理論應用于文本的研究,來理解文學作品的結構和作品被讀者感知的效果之間的關系。圖形—背景理論源于心理學,被認知詩學加以廣泛應用。它是以凸顯性原則為基礎的一種理論,“圖形”是認知當中較突出的部分,是注意的焦點,“背景”相對于圖形來說,在認知當中凸顯程度較低,是圖形的環境,是認知當中的參照點。Stockwell認為閱讀過程是圖形和背景不斷形成的過程,是不斷產生令人震撼的形象(images)和回聲(resonances)的過程,文學的語篇特征、含義和聯想意義正是建立在這一動態過程之上[1]。
作為漢語詩歌的文本典范,唐詩的研究方法已向文學、史學、美學或三者相結合的多維視角發展。但從認知學的角度,尤其從圖形—背景關系的角度對唐詩進行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本文試圖把認知理論中圖形—背景理論的基本思想應用于對唐詩文本的解讀,從方位詞在唐詩中體現出的圖形—背景關系入手,結合認知詩學對文學作品結構和被讀者感知的效果之間的關系論述,探討唐詩中圖形—背景關系的體現方式以及對詩歌意境的作用。
二、圖形—背景理論的基本思想
1915年,丹麥心理學家魯賓(Rubin)首先提出圖形—背景理論,該理論后由完形心理學家借鑒用以研究知覺及描寫空間組織方式。完形心理學家認為知覺場總是被分為圖形和背景兩個部分,“圖形”是指認知或感知中較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點;“背景”相對于圖形來說,是圖形的環境,是為突出圖形而襯托的部分,是認知或感知中的參照點。當我們觀看周圍環境中的某個物體時,通常會把這個物體作為知覺場上凸顯的圖形,把環境作為背景[2]。例如,當我們看到墻上有一幅地圖這樣的情景時,“地圖”通常會被認為是圖形,“墻”則是背景。人們語言上的表達方式也反映了這種關系。
(1)A map is on the wall.
(2)The balloon is above the house.
(3)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在上述句子陳述中,map,balloon,book顯然是作為圖形體現,wall,house,table作為背景。這些例子說明圖形與背景之間在句子結構中存在一定的空間方位關系,也就是說圖形—背景之間的關系在語言中可以由上下、前后、里外等方位介詞來表達。反言之,方位介詞的意義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圖形—背景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為什么人們在日常表達時通常說“地圖在墻上”而不說“墻在地圖后面”,說“書在桌子上”而不說“桌子在書下”?根據完形心理學家的觀點,圖形的確定應普遍遵循“普雷格郎茨原則”(Principle of Pragnanz),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物體(不可分割的整體)、小的物體、容易移動或運動的物體用作圖形;而面積或體積較大的物體,位置較固定、不易移動的物體則作為背景[3]。在此基礎上,為對上述問題進行認知解釋,Talmy給圖形和背景分別列舉了定義特征和聯想特征,定義特征是支配人們選擇圖形和背景的決定因素,而聯想特征則是參考因素[4],進一步增強了圖形—背景理論的認知解釋力。
三、圖形—背景理論在唐詩中的體現方式
圖形—背景理論獨特的凸顯與被凸顯、襯托與被襯托的關系,被認知詩學恰到好處地應用于文學作品的解讀,尤其是解讀詩歌中的典型句式。唐詩中久為傳誦的上乘詩作無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許多意境都是通過具體意象的圖形—背景關系體現的。因此通過圖形—背景理論來分析詩歌句式,對于詩歌的理解和感知很有幫助。
1.通過空間方位體現
空間方位包括“上”、“下”、“前”、“后”、“中”“旁”等。空間會隨著觀察者視角的變化而變化,參照點不同,空間方位就會發生變化。王維的作品《鳥鳴澗》中“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的詩句為讀者勾勒出夜間春山的寧靜優美。詩中圖形—背景要素相互轉換,花落、月出、鳥鳴這些動態的圖形反襯并映射出作為背景的春山的幽靜。“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一句更是將圖形和背景進行多次轉化。通過月亮、山鳥、春澗各個獨立并相連的要素構成了一幅動態的畫面。從圖形—背景理論分析,此句話中月亮既是圖形又是背景。“月出”是圖形,其背景是夜空中的云彩或者是遠處的地平線,月出這一動態被凸顯,處于焦點位置。但很快,圖形與背景的位置發生轉變。“驚山鳥”又將“月出”作為了背景,鳥兒作為一個大的月亮背景中的圖形,從睡夢中驚醒,月亮便成為了動態山鳥的背景。“時鳴春澗中”的主體是山鳥,在大背景月亮、小背景春澗中,山鳥仍然充當了凸顯的圖形。通過對“出”、“驚”、“鳴”等動態的描寫反襯出春山的幽靜,體現出詩人與環境相契合的淡泊心境,進而感受到盛唐時代和平安定的社會氣氛。
2.通過時間關系體現
雖然圖形—背景理論最初是用來研究人類對二維和三維意象的感知,但它也可用來解釋一維時間軸上的事件。具體來說,圖形是指在時間上的方位是可變換的事件,具有相對性;背景是指參考性的事件,在時間方位上相對固定,參照它可以確定圖形的時間方位。圖形傾向于構成一個有界的封閉物,它越封閉,其作為圖形的突出程度就越高。相對于背景來說,圖形在時間上較短,背景在時間上較長。圖形與背景的區別與語言中“時間事件”結構之間的對應關系可以抽象出一個基本的認知原則:較長的、在時間上可包容的事件作為背景;較短的、在時間上被包容的事件作為圖形[5]。根據圖形和背景的這一特征,我們就可以討論概念范疇中圖形與背景的區別是如何反映在語言的“時間事件”結構中的。
唐代詩人王維的詩作《山居秋暝》中有這樣的詩句“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這首詩寫出了清新、幽靜、恬淡、優美的山中秋季的黃昏美景。王維所居輞川別墅在終南山下,故稱山居。一場秋雨過后,秋山如洗,清爽宜人。“晚來秋”可以看做是圖形,而“空山新雨”則是背景,二者由時間詞“后”所體現出來。此詩以一“空”字領起,格韻高潔,為全詩定下一個空靈澄凈的基調。既然詩人是那樣的高潔,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個稱心的世外桃源。這首詩一個重要的藝術手法,是以自然美來表現詩人的人格美和一種理想中的社會之美。詩人通過對山水的描繪借物言志,含蘊豐富,耐人尋味。而詩句中的這種自然之美可以通過圖形—背景理論的時間關系體現出來。
3.通過動詞體現
圖形—背景關系除了被用來解釋介詞的意義以外,在語言學研究中還有很多其他的運用。持凸顯觀的認知語法認為,如果我們將主謂補(包括賓語或狀語)視為圖形—背景分離這一普遍認知原則在語言中的體現,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在一個簡單句中,主語對應圖形,補語對應背景,動詞表述的則是圖形與背景之間的關系[6]。在語言中,將你想突出出來的成分放在主語的位置。
唐詩中大量動詞都體現了典型的圖形—背景句法結構。如李白的作品《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詩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語法結構為主狀謂式,這兩句著意描寫友人“西辭”,“孤帆遠影”相對于“碧空”,“長江”相對于“天際”,都是圖形背景的關系。“盡”和“流”字的傳情之筆,更是寫出詩人的主觀感覺,他此刻心馳神往,追隨友人而去了。這兩句似乎是寫景,但在寫景中包含著一個充滿詩意的細節。詩人把朋友送上船,他的目光望著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漸模糊,消失在碧空的盡頭,表現出目送時間之長。帆影已經消逝了,然而詩人還在翹首凝望,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蕩蕩地流向遠遠的水天交接之處。“唯見長江天際流”,是眼前景象,但又不是單純寫景。詩人對朋友的一片深情,正體現在這富有詩意的神馳目注之中。詩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浩浩東去的一江春水。總之,這一場極富詩意的離別,被詩人用絢爛的陽春三月的景色,將“孤帆”置于“碧空”的背景中,將“長江”置于“天際”的背景中,極為傳神地表現出來了。
4.通過形容詞體現
唐詩講求韻律與意境,精練和美感,有時一句詩中并未出現方位詞或動詞,而是通過形容詞體現圖形和背景。王安石的作品《泊船瓜洲》中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被人廣為傳頌。傳統的分析認為“綠”字從修辭上講是一種移覺手法,將不容易傳達的聽覺、感覺轉化為視覺,既見出春風的到來,又表現出春風到后江南水鄉的變化,一派生機,欣欣向榮,給人以強烈的美的感受。在利用圖形—背景理論進行分析時,根據定義特征和聯想特征,“春風”通常被看做圖形,“江南岸”作為背景,這種解釋相對比較簡單,只是機械地使圖形、背景與詩句句法結構部分一一對應。難以體現“綠”字的動態性,也難以體現出作者的情感傾向。聯系王安石寫作此詩時的背景正為1075年再次北上拜相之際,此處的圖形—背景分離可有其他選擇。當春風“綠”了江南岸的時候,江南岸是逐漸被染綠的,體現了春風的動態。當江南岸完全被綠色覆蓋時,江南岸被凸顯,成為了圖形的選擇,而與之對應的北上的目的地則成為背景。江南岸的凸顯,映射了江北岸的蕭肅。這種圖形—背景的選擇更容易理解作者當時的心境,詩人1070年拜相,推行變法,后變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皇親國戚和保守派的聯合反對,不能在繼續改革下去。1074年詩人罷相。1075年,二次拜相。此時作者通過凸顯一派生機和活力的江南岸,反映出詩人想通過自然界現象的強烈對比來寄托自己對仕途的擔憂。果然,復拜相后,王安石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于1076年再次辭相,后于1086年郁郁而終。通過分析作者圖形和背景的選擇,可以更為準確并深入地把握詩作的含義。
四、結語
漢語與西方語言相比獨特性明顯,其中唐詩是尤為獨特的語篇形式,通過營造意境來表達感情。詩人表達意境的過程就是用簡短的語言構建一幅圖畫的過程,常見的自然事物或感受通過構建過程被賦予深層次的含義;讀者誦讀詩歌的過程則是通過作者的語言對讀者大腦中固有的意象進行激活,使圖形和背景在讀者心中不斷形成并轉變的過程。通過圖形—背景理論,讀者會對唐詩有更深入的理解。當然,根據讀者彼時的具體環境和心境的影響,以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結果,但無論所選擇的圖形是什么,由于它的凸顯作用,使讀者有可能產生和詩人相同的感受,也有可能產生不同于詩人的感受,這都是圖形選擇的不同所帶來的不同效果。因此,正確判斷選擇圖形是理解唐詩的關鍵,這不僅僅要靠圖形—背景的表征,而且要靠詩歌的寫作背景、作者當時的心境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來判斷。圖形—背景理論的基本原理看似簡單,但作為認知詩學的重要概念,若將其靈活運用到唐詩的藝術分析中,會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應用價值。
[1] STOCKWELL,P.Cognitive Poetics:Introduction[M].London/NY:Routledge,2002:73.
[2] 梁麗,趙靜.圖形/背景理論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116-119.
[3] 匡芳濤,文旭.圖形—背景的現實化[J].外國語,2003,(4):24-31.
[4] TALMY L.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 I[M].London: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315.
[5] 梁麗,陳蕊.圖形-背景理論在唐詩中的現實化及其對意境的作用[J].外國語,2008,(7):31-37.
[6] 藍純.認知語言學與隱喻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