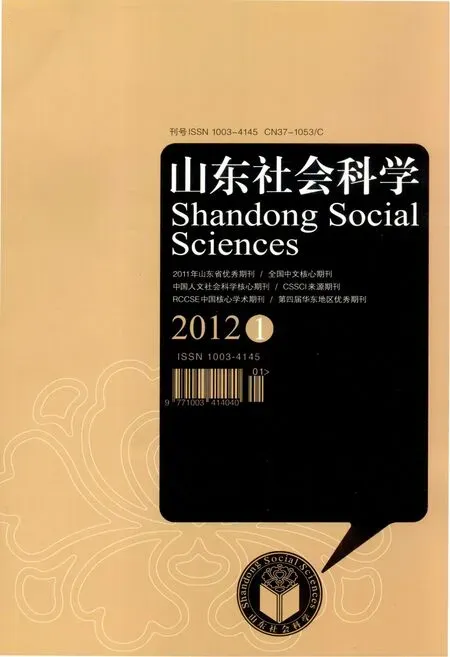基督教景觀的城市空間演化與影響研究
——以明朝中葉以來的上海基督教教堂為例
魏良臣
(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陜西西安 710127)
基督教景觀的城市空間演化與影響研究
——以明朝中葉以來的上海基督教教堂為例
魏良臣
(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陜西西安 710127)
自唐朝以來,基督教想傳入中國的行動就從未停止過,但由于統治階級的原因以失敗告終。隨著國門被戰爭打開,基督教真正傳入中國是在明朝中葉后,并在中國落地生根,逐漸發展起來。本文選取了最具代表的實宗教體景觀——教堂,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城市的相關因素對其分布規律及空間演化的影響,剖析基督教在上海乃至中國的發展情況。
宗教景觀;布局演化;上海基督教堂
一、研究地與研究時期的選擇
(一)研究地選擇:上海
上海,坐落于中華大地的東南,憑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良好的水運條件,在鴉片戰爭前夕就已經成為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商業樞紐。隨著《南京條約》簽訂,上海成為中國首批涉外港口,外國人可以通過上海進入中國內地游歷、通商、傳教,英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往來。因此,上海外貿經濟發展迅速,為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充實的理論基礎。此外,江浙一帶的南京等地遭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城市動蕩不安,上海由于政策的原因成為當時中國相對安全和平穩的傳教城市,提供有利的傳教環境,避免了戰爭對教堂及傳教具有的毀滅性影響。
(二)研究時段的選擇:明朝中葉后
由于中國封建儒家文化的沖擊及政治局勢的變動,早于明朝的數次傳教運動之間缺乏傳承,最終以失敗告終,其中的借鑒意義相對較弱。根據史料可證,天主教于明中葉傳入我國,而新教于天主教傳入后兩百年后再傳入上海。上海第一所基督教教堂的原型也是在該時期(1640年)建成,所以可以基本確定基督教最早是在明朝中葉傳入上海。因此我們的調查研究以明中葉為節點,講述明朝中葉至新中國成立,上海基督教堂的布局與演變。
二、基督教教堂各時期分布規律
(一)上海市基督教教堂的總體發展態勢
基督教伴隨著其第三次大規模的在華傳教行動,于明代初期傳入上海(新教則是在第四次傳教行動中,由傳教士普魯士人郭士立傳入上海)。盡管基督教入華已久,但由于國人深受孔儒之道的教化,加上歷代帝王的政策打壓,基督教一直無法在我國真正扎根。
隨著1842年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通上海等五個通商口岸,正式授予了外國傳教士在上海設立教堂、醫院、學校并進行傳教行為的權利,但基督教整體發展態勢緩慢,至1850年,上海僅3間基督教教堂(圣三一堂、第一浸會堂、圣母圣心堂),且建筑簡陋、人數稀少,經常需要修繕。隨著國人對這一外來文化的認可度逐漸加深,基督教不斷壯大自身。1843年至1899年仍是上海基督教教堂的快速發展階段,教堂數量迅速增長,全市教堂總數達300余所。1900年至1927年,由于租界界線在列強的計謀下被逐漸打破,教堂的受眾面域空前提升,加之“五四”時期學生與工人階級對基督教的推崇,基督教進入空前繁榮階段,全市教堂總數達600多所。1928年至1949年期間,基督教教堂的成長在政治、戰爭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艱難發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基督教的自立運動受到很大的挫折,教堂到1935年只剩下200多處,1938年日軍侵入上海后,許多教堂損毀于戰火之中,其數量銳減。
(二)各時期教堂分布規律
1.萌芽期(1640—1842)
隨著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上海既是南北洋海運中轉港,又是江河海水運樞紐,在國內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早期的上海還不能算是核心城市,但是已經具有了空前的發展潛質。與此同時,實時的許多官員都接納了基督教,第一位傳教人為明代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啟,歷史上常以1608年徐光啟引入天主教作為上海天主教的起始時間。此時基督教在上海開始萌芽,為以后的成長打下的堅實的基礎。
2.移植期(1843—1899)
伴隨著上海不斷融入國際貿易,外商在上海投資開辦船舶修造、繅絲、軋(棉)花和打包等加工廠,并投資棉紡織、日用輕工業、印刷等行業。同時杭州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負面影響,最終導致江南地區城市中心等級的重新排序。因此上海成為地域發展核心,各國先后辟設租界,整個城市由華界地區和租界地區組成,城市建設相應獨立進行,形成多方經營,各自為政的格局。1853年的小刀會起義等民間起義運動在客觀上推動了租界的迅速擴張,從此,租界內的人口增加與面積擴大形成相應的循環模式。正是由于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城市對基督教這一外來文化的需求增長,導致了文化從不同地域移植至上海租界,租界同時保證了上海的教堂未被戰火波及,帶來了近代上海教堂的繁榮。
3.轉型期(1900—1927)
《馬關條約》的簽訂對于外商而言是一個轉折點,企業從原來的從商品輸出演變為資本輸出,工商業不斷擴大生產能力。此時上海已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與全球100多個國家300多個港口城市有貿易往來,對外貿易約占全國50%。當時上海工業資產總額約占全國40%,工人人數約占全國43%,工業產值約占全國50%,市鎮經濟依都市區市場需求而相應調整,工業型市鎮出現。工業的發展使得上海經濟空間繁榮,人均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市民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加大,使得基督教的群體不斷擴展。同時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讓清朝政府將國家富強的希望放在西化改革上,政策上接納外來文化,基督教也因代表西方文明而備受推崇。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深入,“民主”與“自由”的大旗高高舉起,國內揚起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技術的風潮。在這一背景下,基督教得到巨大的推崇,教堂也在上海落地生根,茁壯成長。該時期為基督教在上海發展最為迅速,生長最為健康的時期。
4.艱難期(1928—1949)
抗日戰爭爆發使得上海經濟全面停滯,從根本上改變了上海城市發展的走向。1937年八一三事變,上海經濟損失慘重,隨后日軍侵滬行動爆發,上海航政局內遷。由于日軍實行經濟統制,因此上海內河航線幾至全部中斷,發展幾乎停滯。全市市政公用設施因原租界地區自成系統,網絡支離分割,基礎設施更是殘缺不全,城市建設基本停頓。戰爭時期,教堂或毀于戰火,或被日軍占用,損毀非常嚴重,教堂數量銳減。抗戰勝利后,由于因內戰等原因,市政公用基礎設施建設處于修復和維護狀態,基督教依舊沒有復蘇。1946年開始的大規模內戰又使教堂復興雪上加霜。直至其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后,才結束了上海跌宕起伏的百年近代史,同時也終結了轟轟烈烈的近代上海基督教堂建設運動,教堂逐漸從城市中淡出,最終淹沒在城市化的進程中。
三、影響基督教教堂分布的因素
(一)城市經濟發展
上海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經濟的繁榮,可以說上海經濟的增長與基督教的發展息息相關。經濟進步使得上海更加具有文化的兼容性,越來越多的外商流入上海,不同的文化在上海各界交融,而宗教正是其直觀體現。城市經濟發展為教堂提供了物質基礎、文化環境、傳播渠道,在經濟正向增長這一背景下,人們有精力去思考在物質生活意外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生活,教堂也隨之興起。早期由于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傳教士的文化活動客觀上促進了上海文化的近代化。正因為上海具有兼容并蓄的品性,使傳教機構更愿意在上海建立據點、開展其經濟活動,進一步促進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發展,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促使上海宗教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步提高。無論使得上海在經濟上取得突飛猛進的原因是什么,無可否認,上海整體出色的經濟狀況使得教會有資本除直接傳教外,辦了不少科技、教育、衛生、出版、慈善事業,使城市多元化發展。
(二)城市空間形態、貨運交通
上海交通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航運、鐵路的建設使上海逐漸成為遠東中心城市。1915年,上海租界已擴大為32.82平方公里,為原面積16倍。20年代之后,市區已經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華界南市,閘北,浦東,江灣等多個地區。此時的上海,已是完全開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興的城市由于西方商業的介入而誕生。此外,戰爭使其他江南城市幾乎無一例外遭受到破壞,上海因有租界的庇護,未受到戰爭的摧殘,江南區域內大量人口、資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這個通商口岸快速成長。至1920年,已建成的港碼頭岸線長10.48公里,航線通達100多個國家300多個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國內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港口使教堂沿河流支流集聚,并在租界區內大量分布。此時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己基本形成,城市進入了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租界內的教堂也大量的重建、改建,穩步發展。
(三)城市人口變遷
自殖民者在上海劃分租界以來,外僑人口數量一直呈穩步上升,租界地內的人口密度卻也隨著租界的擴大而增加,租界人口逐步占據了上海人口的大部分。傳教士基數龐大,他們除了創辦教會,從事傳教活動外,也開辦醫院、學校和慈善事業,各國教會也派遣教士自由開設學校以加速基督教的傳播。而伴隨著華人大量嵌入遷入租界,西方的宗教具備了與中國人交流更好的機會,華人在租界內居住歷史,可分為“華洋分居”和“華洋雜居”兩個時期。租界開辟初期,實行“華洋分居”,禁止華人在租界內居住,1853年9月小刀會起義軍攻占上海縣城后,大批華人進入租界避難,打破了“華洋分居”的禁例,華人大量入居租界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了龐大的人口基數。
隨后由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破壞,上海的經濟發展以及城市建設轉入低谷,幾經波折最終徹底崩潰,伴隨的是基督教的發展突然基本停滯,新建教堂不多,且形式較為簡單。戰爭不但對基督教在上海的繼續傳播產生了嚴重阻礙,還對其已在上海取得的成就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特別是八一三事變后,江浙大部分地區先后淪陷,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淪陷,虹口、閘北等地區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K901
A
1003-4145[2012]專輯-005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