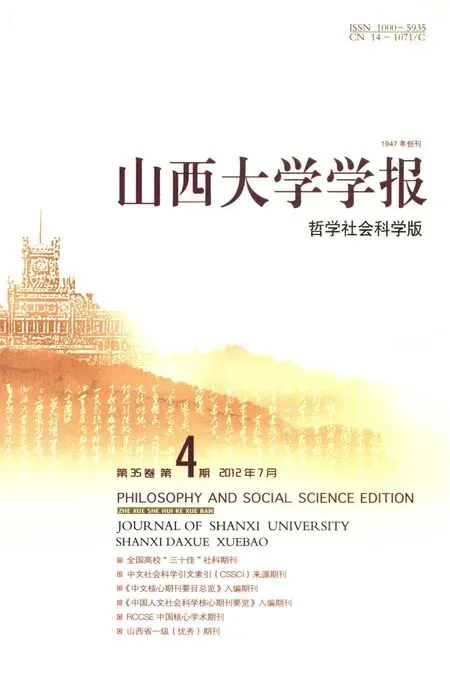漢斯·約納斯關于醫學倫理的哲學辯護
李軍紀
(山西醫科大學學報編輯部,山西太原030001)
·科技哲學與科技史研究·
漢斯·約納斯關于醫學倫理的哲學辯護
李軍紀
(山西醫科大學學報編輯部,山西太原030001)
醫學與人文學的交匯是當代科技的重要特征和發展趨勢,醫學倫理學的快速發展是這種交會的重要體現。文章分析了德國著名倫理學家漢斯·約納斯從哲學層面對醫學倫理學的辯護,包括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論證,在此基礎上,漢斯·約納斯對醫生的技術責任和人類責任提出了道德要求。
漢斯·約納斯;醫學倫理學;醫學與人文
當今生物醫學技術快速發展,基因工程、干細胞治療、器官移植、克隆技術等在臨床上的應用日益廣泛,由于這些新技術對人體的影響復雜隱秘,風譎云詭,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倫理學家的高度關注,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生物醫學新技術的利益和危害各抒己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觀點。然而,醫學倫理學的討論是以研究對象的利益保護為基礎,采用價值推斷和道德標準審查的方法,試圖建立相關的行為規范。對于哲學家來說,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生物醫學倫理何以可能,這些道德標準和倫理規范建立的基石是什么?它或許僅僅是道德學家無病呻吟?還是政治集團的御用工具?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承繼了他的老師海德格爾的智慧,以他自己的方式對生物醫學倫理學進行了哲學的思考。在《技術、醫學與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中,他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對生物醫學倫理學的可能性進行了辯護。約納斯提出,病人的自主性決定了醫學是以病人為目的的,醫學的最高目的就是服務并尊重病人。醫學作為一種科學具有可選用性和不確定性,因而在具體實施時必須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1]。約納斯還對醫生和研究人員的醫療責任和人類責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從本體論上看,病人的自主性與目的性決定了其身體利益不可侵犯
生物醫學的對象是人體,這個活躍的有機體是以自身為目的,它具有自我組織和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能力。在醫療活動中,病人主動借助于醫生的幫助期望實現自我的平衡和完善。約納斯認為,病人是治療的目標結構中的全部[1]。類似于建構主義理論的學習過程,醫生治療病人的過程是病人自覺利用一定的醫療幫助,來實現身體狀態的健康和功能的恢復。在這個過程中,病人是積極的、主動的,而醫療條件是被動的、是被重新構建的。在自然哲學家看來,健康是人的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與自然和諧、互利、平衡,人在自然中享受和滋潤著自身的成長和繁殖。而這種平衡的破壞就會造成不適、痛苦和災難,病人通過主動尋找醫生的幫助而恢復健康的自然狀態。
尊重病人的自主性是所有醫療活動的基礎和前提。病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是生命進化的結果,是人類作為高級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自主性表現在病人選擇治療方法的自主性,病人選擇治療目的的自主性,病人選擇一定方式處理自己身體的自主性。醫學研究人員和醫生的所有行為應該以人的價值和尊嚴為出發點和目的,它僅僅為病人提供一定的條件和環境。因而,以尊重病人為核心價值的醫學倫理學在本體論上得到了辯護。
二從方法論上看,醫學研究的或然性和醫療方法的可選用性要求取得病人知情同意
科學技術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徑,醫學作為科學技術的一個門類,擔負著認識治療疾病的責任。在這種認識和實踐過程中,科學家需要邏輯的推演,更需要直覺的天賦和經驗的積累,需要試驗性地采取不同的途徑把醫學知識推向前進。因而這種努力的結果是或然的而非必然的。同樣,醫術是醫生直觀天賦和經驗的結合。約納斯提出,醫生在診斷過程中,首先需要了解病人的特殊情況,關心病人獨特性和復雜性中的所有個體性要素,而病人的復雜性是任何分析性總結不可能窮盡的[1]。在這種情況下,醫生的直覺天賦和臨床經驗在醫學診斷和治療過程中就成為必然的和無可替代的。直覺天賦和經驗的結果表現為治療方法的或然性和可選用性,在臨床上,表現為任何臨床技術和方法都不是絕對有效的,即使已經臨床證實的技術也會因個體差異而出現陰性結果或者導致醫源性傷害。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醫學在科學的光環下,被大眾推崇為必然性和普適性的技術。每一個病人都希望醫學是經過嚴格的實驗驗證因而必定對自己是有效的和有益的。然而,即使施行正確的醫療技術對整個人群的有效率可能99%,對1%的具體病人個體來說,可能是花費了大量的錢財,治療卻失敗了。這種生物醫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缺陷不能也不應該回避,它是自然科學的固有屬性。由于它可能給人體造成傷害的事實,決定了醫生在施行醫療技術前,有義務和責任告訴病人可選擇的治療方法以及可能的傷害和后果,這項義務是醫學倫理的重要內容,是病人的價值和尊嚴得以保護的重要舉措,它在方法論和認識論層面上得到了辯護。
三醫生的職業責任
在自然哲學家看來,病人的身體與其他動物有機體的一樣,是眾多自然物中的一個,因此,醫學屬于自然科學。醫學像其他自然科學一樣,其研究對象人體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人體的生理和病理過程、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是自我實現和自我表征的。人體新陳代謝的客觀性決定了醫生醫療行為的科學性。醫生由于掌握了治療疾病的知識和技術,在面對病人時根據疾病的規律和自己的經驗提出正確的醫療建議。醫學規律的客觀性對醫生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使醫學診斷和治療成為可能,也為診斷和治療標準的制定提供了保證。由于人體新陳代謝的規律性和客觀性,醫生能夠努力使病人身體的結構和機能趨于自然健康狀態。另一方面,病人身體的客觀屬性免除了醫生在形而上學方面過重的負擔,減輕了醫生過于苛求的社會責任,它為醫生的醫療活動提供了職業道德的辯護。因為,作為醫學對象的人身體的客觀性,導致了醫生的責任在于身體形態和功能的自然標準,醫生只需要遵照醫學規律進行診療活動,只負責病人的身體結構和功能,不需要考慮病人的社會身份。病人的價值和身份不能成為衡量醫療活動的尺度,唯獨其功能的完整性是它的追求[1]。就像乘客乘船航行一樣,船長的責任是使乘客安全順利到達目的地,只要乘客付錢買了船票,船長不能以乘客的某種身份和使命而拒載。同樣,醫生在治療病人的時候,不需要考慮病人的道德身份或社會價值,也不能因此而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醫生被賦予的目的和權力只是病人肉體的完整的自然功能,除此之外,醫學別無它求。因此,醫學的科學性質需要醫生擔當努力發現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解除病人身體上的痛苦和功能上缺失的責任。同時,醫生的科學家身份也免除了對病人道德審查和價值判斷的義務,醫生只對醫療行為本身負責。
四醫學的人類責任
醫術的醫學責任是比較清楚的,它就是我們前面談到的醫學技術對病人身體的責任。醫生為了病人的利益而治療病人,而病人的利益是由自然標準來定義的,例如病人的器官形態和功能完好無損,所有器官的功能處于醫學自然狀態,醫生為此所做的各種努力都可以得到倫理學的辯護。
然而,在技術進步和社會文明進步的今天,病人和社會大眾的愿望與醫學原初所追求的病人“利益”標準發生了偏離或者矛盾。例如,妊娠與分娩原本是人的正常生理功能,按照病人利益的自然標準,不需要由醫生進行干預,因為節育和墮胎是一種非自然的手段,甚至是違反自然規律的行為。因而,有些觀點認為節育和墮胎是不道德的。然而對于已經診斷具有遺傳性疾病的懷孕,對于人口過多的貧窮地區的母親,對于被強奸而懷孕的少女,等等,這些正常的妊娠和分娩過程卻對個人、家庭和社會卻造成了不幸。在這種語境下,醫生為滿足病人的要求,擺脫貧困和痛苦,究竟是施行社會意義的善,還是踐行醫學誓言中的不傷害原則;施行這些婦女的醫學自然狀態,而不顧其社會生活的不幸?在此,醫學技術倫理問題已經轉化為人類責任的倫理問題。
現實給醫生提出了嚴峻的問題:醫生在人類社會責任面前擔當什么責任?他能否只得到醫學的技術標準的倫理辯護還是必須把醫學技術的責任放在次要位置,而首先擔負社會文化或病人的愿望和幸福。
如果醫學完全服從于病人和社會文化的愿望和需要,那么,在當今社會多元文化和多種社會價值標準的情形下,醫生選擇何種倫理規范?是俗世的幸福還是神圣賢明的理想,是西方文化中浮士德式的追求還是還是東方佛教的普世仁愛。約納斯認為,“這些倫理爭辯必須在決斷的天平上一同被估量。”“人類倫理學家在此承認一種對立,在這種對立中,任何決斷都意味著一方或另一方的犧牲[1]。”例如,在避孕藥丸的使用中,一種倫理觀點認為醫生可以只關心其醫學上有無危險,而藥丸的使用是私人的事情。另一種倫理辯護提出,醫生的人類責任是反對避孕藥丸,因為這些藥丸不加區別的供給會助長了享樂主義社會的性泛濫,導致了社會風氣的腐化。
對于約納斯來說,醫生不僅是病人的代表和責任,醫生是社會的代表和公共健康的服務人員。醫術的責任超出了健康而涉及幸福和不幸這一維度,超出了病人而涉及全體民眾,超出了正在活著的人而與下一代有關,甚至涉及地球上人類的命運[1]。例如,人口的生育和繁衍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人類的命運。當下太多的世界人口已經超出了地球的負載能力,成為除核戰爭以外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在約納斯看來,解除這種威脅的辦法不能是某些思想家提出的突然災難以殘忍地謀殺兒童、婦女和民族,而應該是由醫學和醫術設計出人道的、在倫理上值得贊賞的方法來限制出生。換句話說,醫生的行為必須放在公眾利益的維度上考慮,而不能僅僅在個體倫理學和醫療維度上加以考慮。
五關于生與死的倫理思考
現代醫學的進步,尤其是細胞生物學、器官移植技術和干細胞研究的發展,使人類生命的期限被延伸得超過了自然的標準,并且似乎隨著生物醫學的進步,人類的壽命被延伸得越來越長。但是,人類的壽命可以被無限延長嗎?這種延長是好事還是壞事?對此,約納斯提出了人的必死性的觀點,并且對人的必死性的意義進行了辯護。他認為人的死亡與繁殖具有平衡的普遍意義,即沒有死就沒有生。從俗世的社會意義來說,如果無限制地延伸人的壽命,意味著放慢了增加新生命的速度,結果就會造成日益增長的老齡化人口中年輕人的比例日益降低,這對人類社會來說,不是好事,是受到了損失,不是善,而是惡。其次,一個老齡化的人口通過先行占有社會資源肯定阻礙了年輕人的發展,這樣的社會形態對年輕人是不公正的。再次,約納斯提出,人類的希望在于新生的東西不斷出現,表現在年輕人的直率和熱情中,表現在持續不斷地創造各種不同的東西中,而所有年輕人的優勢只有以老年人的死亡為代價才能得到。
關于生與死的哲學思考,古今中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約納斯相呼應的中國文化的人生追求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必死性是自然不可抗拒的規律,已成為我們不二的選擇和命運。然而,從古代的長生不老崇拜到中世紀的煉丹術,到現代醫學的基因工程和器官移植,人類追求延長壽命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約納斯這位思想大師則提醒我們,人類是否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如果人的死亡是必然的,科學對于延長壽命的研究就是無益的和徒勞的。
約納斯對于醫學倫理學的辯護無疑離不開其哲學思想和價值判斷。作為上世紀著名的倫理學家,約納斯從哲學的層面批判了科學自由觀念和研究自由的假定,論證了醫學的道德追求和倫理責任,他認為現代醫學研究的關鍵詞是責任、幸福和未來,而不應該僅僅追求自由、健康和壽命。約納斯睿智的論證和縝密的思考對于我們重新審視醫學技術、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尚德厚道的醫學人文情懷具有重要的意義。科學中的人文關懷是科學的最終目的,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只有踐行對病人的尊重,踐行病人的知情同意,才能得到社會對醫生的理解和尊重,也才能實現其人道主義救助和人文關懷的愿望[2]。
[1]Jonas H.技術、醫學和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M].張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113-226.
[2]李軍紀,王洪奇.論生物醫學科研中科學道德情感的培養[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5,18(5):39.
Hans Jonas’Philosophical Argument for Biomedical Ethics
LI Jun-ji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The confluence of medicine and humanitie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ethic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is conflue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mous German ethicist,Hans Jonas’philosophical arguments for biomedical ethics,including those in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On this basis,Hans Jonas proposed a moral requirement for both doctors’techn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ir human responsibility.
Hans Jonas;biomedical ethics;medicine and humanities
R-02
A
1000-5935(2012)04-0007-03
(責任編輯李雪楓)
2012-04-26
李軍紀(1965-),男,山西陽城人,山西醫科大學學報編輯部編審,主要從事科學技術哲學和科技期刊編輯出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