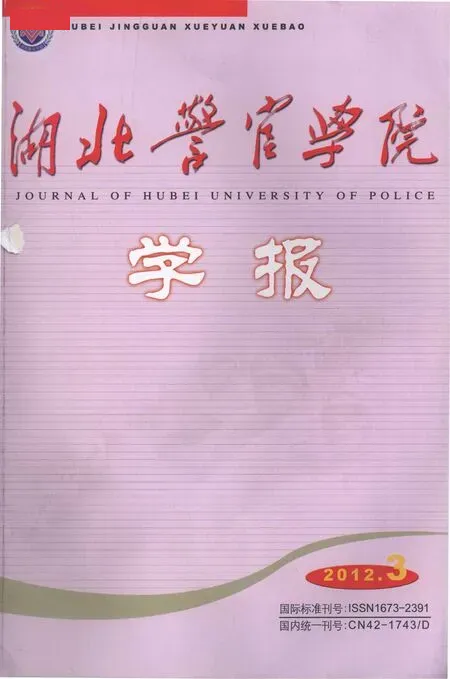論非法證據及其排除范圍
林睦翔
(韶關大學 法學院,廣東 韶關512005)
論非法證據及其排除范圍
林睦翔
(韶關大學 法學院,廣東 韶關512005)
司法解釋雖對非法證據作出界定,但對排除范圍的限制有不妥之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排除的證據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都要排除。在確定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時不應考慮是言詞證據還是實物證據,而是要看非法證據侵害的法益的性質和違法行為的性質。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范圍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證據立法議題,引起了理論界、立法機構和司法實務部門的普遍關注。各種證據立法建議稿,無不涉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問題。一種全面引進排除規則的立法努力正在興起,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國未來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其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非法證據的性質和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問題,這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的前提,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立法課題,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爭論
(一)何謂“非法證據”
“非法證據”是一個有爭議的法律概念,學術界尚未形成明確統一的認識,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非法證據就是合法證據的對稱,“符合法律要求的證據材料,就是合法證據,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證據材料就是非法證據。”[1](2)“凡是不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收集、固定、審查的材料都是非法證據。”[2](3)《訴訟法大辭典》的解釋指非法證據是“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材料”,包括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證據形式不合法以及收集證據的程序不合法。(4)“非法證據應當界定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的享有調查取證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以違法的方式取得的證據材料。”[3]第(1)種和第(2)種觀點雖然對非法證據概念的表達有所不同,其實二者對非法證據范圍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對非法證據范圍作了最寬泛的劃定,認為非法證據包括:收集主體不合法的證據、表現形式不合法的證據、來源不合法的證據、違法收集的證據、違法固定的證據、違法審查的證據。第(3)種觀點所確定的非法證據的范圍相對較小,除要求收集主體、證據形式和證據來源要符合法律外,只將違法收集的證據涵蓋在內,沒有包括審查程序違法的證據。第(4)種觀點的違法證據的范圍最小,非法證據只是違法收集的證據,包括法定收集主體超越權限收集的證據、違反收集程序得到的證據和采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證據。總的說來,“非法證據”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來說,“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違反國家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關于收集證據應遵守之原則、程序和權限,采用違法方法取得的證據。從廣義上來看是指,證據的內容、形式、收集主體、程序、方法和審查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材料。廣義的非法證據概念考慮的是法律對證據的一般要求,狹義的非法證據概念則是從非法證據排除的角度來界定。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限度
非法證據應予以排除,這是現代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準則。但是不是所有的非法證據都要排除?如果不是全部排除的話,究竟要排除到什么程度?對此,大體上有以下幾種觀點:(1)廣義非法證據排除說。該說持廣義非法證據概念,只要證據在收集主體、來源、形式、收集、固定、審查任何一方面不符合法律規定,就是非法證據,非法證據不能成為定案根據。當然,對非法證據要區別不同的情況,做出不同的處理:對于違法收集和審查的證據經過補辦必要的法定手續之后,使它們變成合法證據,然后可以用以定案;對于某些違反法定程序收集而造成了不可彌補缺陷的材料,不能作為合法證據使用;采用嚴重的違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材料,更不能作為定案的合法證據。[4](2)狹義非法證據排除說。該說認為,非法證據的排除應限定在違法取得的證據,也就是法定主體違反法定權限、程序,采用法律禁止的手段收集的證據。在堅持狹義非法證據排除的學者中,對排除范圍的認識也存在差別。一種觀點認為,非法證據原則上不具有法律效力,應當予以排除,但又存在若干例外,非法證據可以不予排除的情形有:排除非法證據可能會危及國家重大利益的(如國家安全、政權與統一);司法人員出于過失或情況緊急,缺少或未履行某些具體手續而不涉及公民人身權,或者對公民人身權侵害顯著輕微,將其排除不利于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以侵犯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獲得的實物證據,被告人申請采用的;非法證據材料為無罪證明的;綜合各種因素(如非法取證行為時的條件、違法的嚴重程度、行為人主觀心態、案件的性質及危害程度等)而應當采用的其他情況。[5]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應當確立起全面、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包括非法言詞證據一律排除和非法實物證據的原則排除。從打擊犯罪的角度考慮,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應當設立若干例外,例外情形的范圍應當界定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利益時不適用排除規則。[6]再一種觀點認為,對非法取得的證據因類型不同要區別對待,違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應當排除,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不應當排除。因為人的主觀性的言詞很難辨別真偽,采用非法手段獲得這些言詞證據潛在的虛假性和違法性遠遠大于通過相同方式獲得的實物證據的虛假性。違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可靠,容易造成冤錯案件,而實物證據具有較強的客觀性,雖然收集違法,但仍可以作為定案根據。
二、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限定及其缺陷
刑事訴訟法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或采用法律明確禁止的手段收集的證據的證據效力并無明文規定。直到1998年,兩高的司法解釋才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出初步規定,并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加以明確。《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第1款規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得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界定非法證據的性質和范圍時,采取了一致的標準,明確規定“非法證據”的性質是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并將禁止采用的非法方法限定為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方面。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要排除的不是任何形式的非法證據,僅僅是通過上述手段收集的“言詞證據”。筆者認為,司法解釋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規定存在以下不足之處:
第一,司法解釋將違法取證的行為限制在“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訊問行為,范圍過窄。這樣規定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曾作出解釋:“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嚴重違反法律,侵犯人權,事件發生后會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我國已加入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依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7]這一解釋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是嚴重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并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二是中國已經加入聯合國有關國際公約,因而應承擔起禁止酷刑的國際法律義務。但是,嚴重侵犯人權并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偵查行為,絕不僅僅限于刑訊逼供等非法訊問行為。中國除了加入聯合國有關禁止酷刑的國際公約以外,還簽署了更為重要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后者更是確立了包括不受任意逮捕和羈押、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等在內的很多公民權利。無論是從保障公民權利、消除惡劣影響,還是從履行國際義務的角度來看,排除規則的制裁對象都不應僅僅限于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訊問行為。偵查人員侵犯公民權利的情況除了刑訊逼供等非法訊問行為以外,還有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竊聽、非法辨認、非法拘捕和羈押等種種表現形式。非法搜查、非法竊聽行為更多的是侵犯公民的隱私權,非法扣押行為不僅侵犯公民的隱私權,還有可能侵犯公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這些非法搜集證據的行為不僅為刑事訴訟法明文禁止,而且也被憲法列為違憲行為。如果通過這些違法手段所獲得的證據不予排除,則不能對這些違法行為進行有效的程序性制裁,公民的上述憲法權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第二,將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限制為非法言詞證據,未將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納入排除的范圍。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物證、書證和視聽資料等實物證據,只要查證屬實,法院仍可以作為判決的根據。可以想象,如果對警察以刑訊逼供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法院不予排除而照常使用的話,則刑訊逼供取證行為還是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另外,非法取證行為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如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竊聽、非法查詢凍結、超期或變相羈押等,很多實物證據是通過這些非法的方式獲得的。如果偵查人員通過這些違反法定程序的方式獲取的實物證據,不包括在排除范圍之內,偵查人員就可以隨意地采取非法手段獲取實物證據,這樣必然損害程序正義。
第三,現行司法解釋所限定的“非法證據”的范圍過于籠統,給實際操作帶來困難。首先,對究竟什么是刑訊逼供缺乏明確的界定。如果按照司法實務界的普遍理解,刑訊逼供主要是指偵查人員采用拷打、肉體折磨方法獲取供述的行為,那么,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殘酷的精神折磨,這算不算刑訊逼供?偵查人員長時間剝奪嫌疑人吃飯、飲水、睡眠、休息甚至強迫其服用精神藥物等方式進行訊問,這算不算刑訊逼供?其次,司法解釋規定,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一規定也是含混不清。是不是所有的威脅、引誘和欺騙行為都一定是非法呢?偵查人員采取威脅、引誘、欺騙行為到何程度才屬于刑事訴訟法所禁止的非法行為?司法解釋沒有對非法方法的危害程度、其對言詞證據影響程度、可操作的標準等作出明確規定。筆者認為,一定要理性區分威脅、欺騙和引誘的合法與非法,法律應該對非法方法的內涵和外延予以清楚地提示。因為在偵訊策略中采用一定程度的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是普遍存在并具有一定的許容性的,甚至合法的威脅、欺騙和引誘恰好是偵查、訊問的謀略和技巧的體現。對這些行為不加區分地統統認定為違法顯然是不合理的。
三、對我國確定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建議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范圍的確定必然涉及訴訟價值的選擇和考量。非法證據的排除,特別是那些具有客觀性、關聯性證據的排除,必然會增加指控的難度,如果排除的是關鍵證據,還可能導致檢控方證據體系的崩潰。因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然對實體真實的實現和控制犯罪訴訟目的的實現造成消極影響。但如果不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不能對偵查等人員的違法行為進行有效制裁,不利于公民權益的保障。因此,“非法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應當確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刑事訴訟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這相互沖突的兩大價值目標之間如何選擇、協調的問題。”[8]由于法律文化傳統,以及特定時期控制與保障人權的需要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同一國家不同時期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時,存在差異。我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應綜合考慮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制約因素,根據一定的科學合理的標準,在不同類型的案件中,針對違法性質輕重的不同,確立相應的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既不能過寬,也不能過窄。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排除的證據是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所獲得的證據;二是采用法律所明確禁止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非法證據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取證主體、證據來源、證據形式、證據收集、證據審查判斷等各方面,只要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理應屬于非法證據。但并非只要是非法證據就應當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范圍。我們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目的,是對公共侵權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和不正當使用,也是為那些遭受公共權力侵害的公民權利提供保護和司法救濟。就刑事證據而言,刑事訴訟中的侵權行為基本上是發生在證據的收集程序,如非法訊問、非法搜查、扣押等。或許有人問,如果是取證主體、證據形式、來源等不合法,則如何處理?這些證據能夠使用嗎?當然不能夠使用,但這些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解決的問題,而是因為這些證據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自然不具有證據能力。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排除的證據是偵查、檢察、審判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雖然,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在刑事訴訟中也享有一定的證據調查權,但由于其行使的權利不具有公權力性質,其證據調查行為本身不可能對公民的人身、財產進行強制,也不會對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侵害,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應當適用于辯護人等違法獲得的證據。在西方各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的“非法證據”是偵查人員非法取得的證據,取證主體不包括法官。其原因在于,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沒有證據調查權,法官不能收集證據,因此,根本不存在法官調查取證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法官雖然享有證據調查權力,但法官調查取證時,有控、辯雙方的同時參與,能夠有效地防止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大陸法系國家采取警、檢一體化模式,檢察官領導、指揮偵查,非法偵查的實施主體包括警察和檢察官。在我國,不論是偵查人員還是檢察、審判人員都享有證據調查權,都存在非法取證的可能性,所以在確定非法證據的取證主體范圍時,不應局限于偵查人員。
第三,并非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都要排除。在我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應將排除范圍限定在侵犯和剝奪公民憲法性權利所獲得的證據,或者直接損害了當事人的基本權利所取得的證據。可以將排除的“非法證據”分為兩類:一類是憲法性侵權所獲證據;一類是非憲法性公共侵權所獲證據。所謂憲法性侵權就是指調查取證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性權利。此種證據應視為最為嚴重的非法證據。非憲法性公共侵權是指偵查人員的行為沒有明顯違反憲法,但侵害了公民的一般性實體權利和程序性權利,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違法取證行為。
第四,在確定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時不應考慮是言詞證據還是實物證據,而是要看非法證據侵害的法益的性質和違法行為的性質。非法獲取實物證據的行為與非法獲取言詞證據的行為在性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對國家法治秩序的破壞和公民權利的侵犯。如在非法搜查、扣押時使用暴力強行扣留他人物品或強行搜身,造成被搜查人人身傷害,或對被搜查人人格的侮辱、尊嚴的破壞等侵犯的不僅僅是公民人身權利,更是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挑戰憲法權威。如果對于侵犯公民憲法權利而獲得的實物證據加以采用,實際上就是對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行為默許和縱容,其危害的不僅僅是公民的隱私,更是對憲法尊嚴的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和存在價值并不是在于排除不真實不可靠的證據,而是為了防止對公民權利的非法侵犯,這就是為何對那些在客觀性和關聯性上沒問題的證據仍要排除的原因。其實,中國的法官們也認識到偵查人員在收集實物證據時如果“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應當將證據加以排除。法官們認為:“對非法收集的言詞證據以外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未規定法律后果,是因為此問題比較復雜,有些嚴重的犯罪,比如危害國家安全罪,各國都采用了一些較為秘密的偵察方法,有時難免侵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訊自由等權利,對這些犯罪不處罰,又會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法院對上述證據一概不作為證據,恐不符合實際,對此問題如何規定,還需要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后,作出決定。在有關部門作出規定前,我們認為,對于有關機關或者個人非法收集的實物證據,如果嚴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或者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排除。”[9]
[1]張子培.刑事訴訟法(政法袖珍文庫)[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157.
[2][4]周國均,劉根菊.刑事證據種類和分類的理論和實務[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282-285.
[3]左衛民,劉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完善[J].法商研究,1999(5):56.
[5]張惠芳,管曉靜.非法證據的效力探討[J].政法論叢,1999(4).
[6]左衛民,劉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完善[J].法商研究,1999(5).
[7][9]熊國選.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釋疑[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51.
[8]謝佑平.刑事訴訟國際標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35.
D925
A
1673―2391(2012)03―0054―04
2011—11—15
林睦翔,河南項城人,韶關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