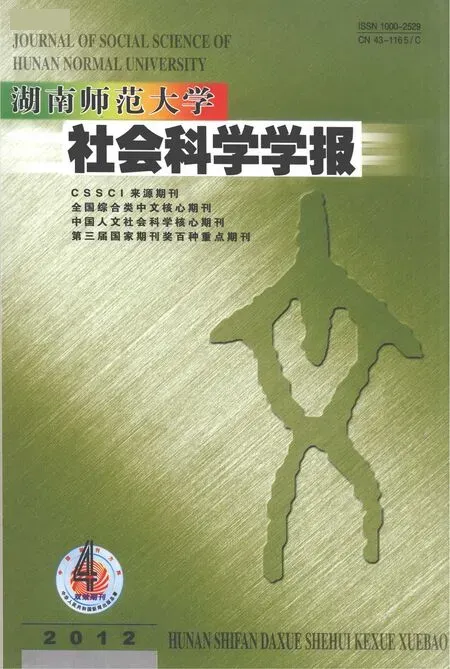技術哲學從經驗轉向到文化轉向的發展及其展望
林慧岳,丁 雪
技術哲學從經驗轉向到文化轉向的發展及其展望
林慧岳,丁 雪
技術哲學研究突破“經典時期”的困境后實現了其“經驗轉向”。經驗轉向過程中,在現象學的酶促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文化傾向。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從一個文化的多元視角來開啟技術哲學的新的研究范式,通過對技術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影響進行雙重聚焦,從細節上描述技術與文化的互動,關注人的價值和人的生活世界,提供解決技術社會問題的哲學思維。
經典技術哲學;經驗轉向;現象學;文化轉向
20世紀80年代,技術哲學研究開始在我國興起。與此同時,國外技術哲學正發生所謂的“經驗轉向”并在“經驗轉向”中發展了現象學的分析方法。在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轉變中,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突顯,表現了“經驗轉向”后的技術哲學向文化轉向的趨勢。
一、經典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
19世紀下半葉,伴隨著工業革命和人類技術活動的不斷擴展,人們開始對技術進行系統的哲學思考。德國哲學家卡普(Ernst Kapp)《技術哲學綱要》(1877)是技術哲學的第一部專著。至20世紀后半葉,“歷史性缺席”的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家族的“遲來者”開始引人注目,技術哲學研究逐漸增多。技術哲學雖然較晚實現建制化,但流派繁多,觀點林立。卡爾·米切姆(Carl Mitcham)在其著作《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89)中回顧了經典技術哲學的發展歷程,將其概括為工程學派技術哲學和人文學派技術哲學,表征兩種不同的主要技術哲學研究范式。
工程學派技術哲學旨在通過對技術本身的定義、工作原理、操作程序及技術效果的整體描述實現對外部世界的解釋。工程學派的興起與工業革命造就的機器大工業時代密切相關。科技活動的巨大成功使人們普遍相信利用技術的手段可以實現人類社會美好生活的愿望。工程學派的哲學家肯定了技術的合理性并對技術的發展持積極的樂觀態度。卡普在其“器官投影說”中將技術看作是人體器官或人體系統的外部延伸,他細致地描述了技術的內在結構與有機體結構的相似性,以說明機械的逐步完善化實踐符合有機生物的發展理論[1](450)。另一位德國哲學家德紹爾(Friedrich Dessauer)則在其《技術哲學》中高唱技術贊歌,認為“技術產品改變世界的力量跟使人去發明、去追求技術創造的命令是不一樣的。”技術是“凡人在塵世中最偉大的體驗”[1](473)。技術發展的合理性和技術之于人類社會進步的強力推動得到了當時大多數技術哲學家們的肯定,工程學派技術哲學對于技術的態度是樂觀的,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于人類征服自然和構建理想社會將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他們大都只停留在技術對社會的單向的、積極的、淺層的影響作用層面,對技術活動中的負面作用考慮甚少,并主體性地忽視技術與社會的深層次文化關系。
與工程學派恰恰相反,人文學派技術哲學是一種從文化、宗教、政治等人文學科的角度對技術進行解釋和批判的研究[2],這個流派的技術哲學從技術以外的多元化視角來評判技術的社會影響。人文學派的形成和時代的發展脫不開關系。伴隨工業的大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技術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開始顯現,引起技術哲學家的關注和反思,對于技術產生的消極社會后果的批判成為20世紀技術哲學研究的主流。技術批判的結果是許多哲學家由對于技術的盲目樂觀走向了悲觀主義。技術哲學家紛紛聚焦技術對于人、人類社會和世界關系的影響及作用的分析和解釋研究。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了人類社會對“巨機器”的盲目依賴問題。芒福德所指的巨機器或巨技術,就是與生活技術、適用性技術、多元技術相反的一元化專制技術,其目標是權力和控制,其表現是制造整齊劃一的秩序[3],芒福德認為克服這一問題的出路是回歸人性和生活。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技術的追問》(1954)中將技術的本質定義為一種人類無法掌控的“座架”,技術使人類與自然世界分隔,海德格爾想以此提醒世人,在貌似中立的技術背后,還隱含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真切關系[4]。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單向度的人》(1964),從意識形態角度對技術進行了社會政治批判,他強調現代技術社會的單向度化,無所不在的技術控制使得這個社會喪失批判性[1](6)。埃呂爾(Jacques Ellul)則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技術自主論”,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生活于其中的技術環境,并且技術進步總是喜憂參半、后果難料的,在埃呂爾的技術哲學思想中體現著明顯的辯證思維。技術批判運動表明,以前研究中淺層的技術與社會關系需要發展成深層的技術與文化的關系,文化因素成為技術哲學反思的新的要素。但是,人文學派技術哲學的“文化”是狹隘的,這表現在他們對技術理解的單一性上,他們視野中的技術是抽象的大寫技術“T”,而不是處在具體的、活生生的人類實踐中的技術。
到20世紀中后期,一些技術哲學家的態度發生變化。他們對于技術不再是完全的批判,而是更注重技術之于人類社會的實用性,他們不再以整體化的一般技術作為研究對象,而是進行對具體技術的經驗性分析。伯格曼(Albert Borgmann)、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溫納(Langdon Winner)和伊德(Don Ihde)等人的技術哲學研究突破了經典技術哲學時期的研究規范。漢斯·阿切特胡斯在《美國的技術哲學:經驗轉向》一書中看到了技術哲學所遇到的困境和當代技術哲學研究重點所發生的轉移,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5](26-27),以建立新的技術哲學研究范式。
技術哲學之所以發生經驗轉向,是源于其研究綱領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固有缺陷[6]:1)將技術作為既定物進行整體分析;2)片面強調技術的負面影響;3)夸大了技術的自主性。“經驗轉向”致力于打開技術的黑箱,以向具體技術的經驗描述回歸為基礎,客觀理解技術與社會的共同進化。“經驗轉向”得到了技術哲學研究領域的普遍認同。技術哲學的研究回歸到了對于具體技術的經驗性描述,并從多角度對技術進行剖析和透視,研究技術內在結構與功能的關系、技術與研發者/使用者主觀意向間的聯系問題。技術哲學研究的這一重大轉變,比起之前對于技術的負面社會效應的批判所引發的技術悲觀主義而言,對解決現實問題有著積極的作用。向技術問題的經驗研究回歸,不僅包含了對技術本質的哲學理解,還包含了對技術與社會關系的哲學分析。這種由整體向具體、由一般理論向案例分析的研究范式轉變,要求對技術本身和技術外在關系進行文化反思,進一步要求技術哲學必須溢出狹隘的人文批判,走向對技術文化的全面研究。這樣,無論是忽視文化因素的工程學派技術哲學還是簡單理解文化與技術關系的人文學派技術哲學,在經驗轉向中都吸收到了向前發展的理論營養和找到了精細化的分析方法。
二、現象學酶促下“經驗轉向”向“文化轉向”的發展
經驗轉向后的技術哲學看到人類文化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但遺憾的是未能確立文化維度作為新的分析框架,從而實現對當代技術的全面解讀;也未能提出技術文化哲學的具體方法,來解決當代技術與社會的種種問題。
當代技術哲學的研究面臨著幾大問題:本體論問題、認識論問題、倫理問題和方法論問題[7],這幾大問題正構成了現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綱領。本體論解決的是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的問題,包含了技術的物理屬性和文化屬性,屬于器物層面;認識論和倫理解決的是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式是什么的問題,屬于精神層面;方法論則解決了技術哲學研究的實踐問題,屬于行動層面。在文化的框架內完全可以覆蓋當下技術哲學各個領域的研究。伊德認為,技術是被歷史和文化所嵌入的[8]。作為亞文化的技術與文化是共同進化的,文化的嵌入性要求將技術與文化視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
技術哲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現象學的研究傳統。海德格爾認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根本性問題是技術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是一種關于技術的本體論問題,他開辟了從現象學的視角考察技術本質的先河[9]。海德格爾認為技術的本質應該從技術所面向的“周圍世界”中尋找,“如果我們要尋求樹的本質,我們一定會發現,那個貫穿并且支配著每一棵樹之為樹的東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樹,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樹木中找到的樹。同樣的,技術之本質也完全不是什么技術因素”[1](301)。他將技術理解為一種與此在世界相聯系的現象,將技術與人類生活的意義聯系起來,用現象學的方法對技術和技術活動進行人文維度的解釋,將技術之“技術因素以外的”人類文化因素(歷史的宗教的藝術的)與技術的互相作用展現出來,展現了技術本質的人類文化性。
如同生物學“酶促”(enzyme catalysis)的激活效應,現象學在經驗轉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從技術的外部描述技術的本質,但忽略了技術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從伯格曼開始,技術現象學的研究深入到技術內部,為技術哲學經驗轉向的實現提供了有效的途徑。技術哲學在解決當代社會問題時,運用現象學的方法對基因技術、超聲波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結構、原理及社會影響進行案例分析,透視技術發展的各個環節,提煉技術的文化價值,彰顯技術的人文社會意義。
將現象學用于技術哲學研究有幾大不同的方向:伯格曼的技術人工物向度、德雷弗斯的人工智能向度、伊德對人與技術關系具體分析向度。[9]在技術現象學的分析中隨處可見文化分析的印記。
伯格曼為美國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研究的開山鼻祖,他認為“美國主流哲學的重心正在由追問現實的具體性向主要技術問題的哲學分析轉移”[10]。伯格曼對人類社會的信息技術進行了現象學的分析,并區分了三種信息:自然信息、文化信息、技術信息。每種信息以自己的方式構成了人與現實間的聯系[11]。伯格曼將“技術人工物”作為技術研究的出發點,主張在對現代具體技術的經驗描述基礎上進行哲學反思。在《技術與當代生活》(1984)中,伯格曼描述了早期社會中技術的文化作用,伯格曼認為,技術是人類世界諸多要素的聚集物,展現著人類世界的文化;然而,伯格曼也指出,現代技術改變了人類參與現實的方式,技術人工物無法全面地體現人類的文化,甚至導致了人與世界關系的某種分裂,當代人工制造物具有不可逃避的社會的、文化的、倫理的、道德的諸多問題[12]。只有在對技術的經驗性分析過程中引入文化維度分析,才有可能使人類更好地控制技術發展的進程,規避技術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然而,伯格曼認為主流哲學中還沒有建立完善的文化分析框架,但是,潛在于現代哲學中關于技術爭論的文化推動已經顯現,并成為現代美國哲學的特點[10]。
德雷弗斯選取現象學的角度對人工智能進行剖析。對于人工智能這一現代高新技術,德雷弗斯認為幾乎無法實現,因為從現象學經驗性分析的角度,諸如人類情態、技能、心理等一系列文化實踐的背景,都無法以虛擬的計算機規則或語境進行具體描述,“非定理的或非概念的經驗,諸如信仰、推理、判斷等,如何能夠在實踐中使之與命題表現相一致,是個巨大的問題”[13],計算機無法模擬人類社會以文化為基礎構建的社會網絡是其無法實現的根本障礙。德雷弗斯以椅子為例,說明了任何技術產品的存在都是以一系列有形或無形的人類文化設置為前提的,“使某物成為椅子的是它的功能,使它能起坐物的作用的是它在全部實踐環境中的地位。這有預設了有關人類的某些事實(疲勞、人體彎曲的方式),一種文化所決定的其他設備(桌子、地板、燈)的網絡和技能(吃、寫、開會、演講等)的網絡[1](348)。按照德雷弗斯的觀點,任何一項技術的發明都首先應當在人類文化的環境中做評估,缺失文化實踐的背景,擬議中的技術就不可能有進展,因為文化因素是決定技術是否可能實現的內在條件。德雷弗斯對于人工技能具體技術的分析,將人類的文化因素作為技術考量的內景,顯示了文化之于現代技術的決定性作用。
伊德發展了技術哲學的現象學研究,提出了技術哲學的后現象學研究綱領。后現象學結合了實用主義的諸多理論,堅持強調以現象學的“變更”作為分析工具,在實踐中采取“經驗轉向”的研究方法,深入案例研究或表象下的具體問題分析[14]。根據伊德的觀點,技術不可能從它所置身的背景關系中抽離,技術是一種關系性存在,這就使伊德將技術哲學的分析深入到了技術背后廣闊的人類社會文化背景之中①。換言之,技術與人的關系深層次顯示出的是技術與人類文化的關系。伊德選取了所有古代文化中都存在的技術,弓和箭,分析了這一技術在不同地域及歷史背景中的差異,形象地說明了技術與不同文化情景的相適性要求。伊德認為,技術在協調人與世界關系的過程中,不僅僅是改變著人類活動的習慣,更使得技術形成一種技術文化,進而改變著人類的思維模式,人類越來越相信和依賴技術構建出來的“真實世界”,伊德用成像技術“使不可見的顯現”證明自己的觀點。
受伊德后現象學的啟發,荷蘭技術哲學家維爾貝克(Verbeek)指出,后現象學的方法使研究技術如何在道德決策的基礎上實現人們對現實感知和解釋的具體化成為可能[15]。將后現象學與倫理學相結合,維爾貝克對產科超聲技術進行了案例分析,說明了在技術文化中技術的道德中介作用,提出了技術的道德和道德的技術兩大問題。人類文化背景中的技術如何發展?技術文化籠罩下的人類何去何從?要想解決好這些問題,文化是唯一的切入點,它涵蓋了技術存在的社會、歷史、倫理及各門自然科學等諸方面背景因素,只有對技術進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視,才能從根本上了解技術和掌控技術。
現象學的發展由胡塞爾的先驗論、海德格爾的本體論,經過經驗轉向發展到伊德的后現象學,其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的作用日益凸顯。現象學和技術史的發展為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先導作用。
任何人類經驗都是“歷史”的經驗,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也不能忽視事物的歷史。遠德玉認為“技術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技術是客觀的存在同主觀的能力相結合的產物,技術是主體與客體相結合而形成的一個動態過程。沒有過程便無所謂技術”[16]。技術哲學研究應當在技術研發的動態過程中展開,并且應當在此過程中全面地展現技術與人之間的互動。技術的發展史也是人類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發展史,是進行技術的哲學反思的基石。技術是一種實踐過程,其本身具有文化實踐性,“技術史界出現了新的技術史研究動向:準備用技術人造物作透鏡來觀察更廣泛的歷史問題,來理解塑造技術的過程也如何成為塑造社會、政治與文化的過程”[17],近年來,技術史研究領域也發生了其自身的文化轉向,從技術文化史的角度開展對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技術史與技術哲學的關系如同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關系,兩者完全可以類比。如果說科學的外史研究與科學哲學的社會歷史轉向的關系反映了某種內在聯系,那么,技術史的文化轉向與技術哲學文化轉向則是從形式到內容的完全一致。
借鑒現象學的分析技巧,經驗轉向的技術哲學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各個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文化性偏轉,它們不僅顯示了文化因素在當今技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技術發展對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各種潛在的與顯見的、長期的與即時的影響。經驗轉向催生現象學運用于技術透視,技術不再是單純的、赤裸裸的工具,而是現實生活方式,是構成豐富多彩的世界的主要環節,技術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技術構成了技術文化奏鳴曲的旋律交替和生活世界圖景的色彩變幻,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必然導致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18]。
三、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展望
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還處于“正在進行中”。在對具體技術進行描述分析時,“技術”和“文化”不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分析要素,而是處在人—技術—文化的相互關聯中。人—技術—文化各要素之間的互動,共同構成了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技術文化”。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首先是技術哲學研究對象由單一的技術拓展到“技術文化體”,在技術與文化的關聯中將技術的文化分析與文化的技術理解結合起來。其次,技術哲學文化轉向的方法論變革是文化分析維度的引入。技術是最古老的人類實踐活動,它和人類文化是一種共生的關系,技術的文化分析可以借鑒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的分析。馬林諾斯基認為一個文化過程涉及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人工制品、標準化的行為方式和象征性動作[19](135),這實際上包含了器物層面、制度與行動層面和精神層面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因而,技術哲學文化轉向不僅僅分析具體的技術物,更要揭示技術的文化關系和文化價值。
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既是研究范式的轉換又是研究方法的變革。在當代社會變革和技術問題日益增多的轉型期,技術哲學文化轉向有重要意義。
第一,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對技術價值取向進行后現代的詮釋,力圖克服工業化時代技術的單一經濟價值和線性作用模式的缺陷。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主義在普遍主義的視域之內,命題和規范的有效性被設想為是以它們與理論和實踐的人類理性標準的匹配為依托[20],后現代主義則突破普遍主義的確定性特征,為相對的、或然的和普遍的非確定性爭取生存空間,消解了技術決定論下的同一性和齊整性。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在價值取向上采取后現代性的多元化價值路徑。后現代主義的技術價值是經濟的、人文的、社會的、生態的、審美的等目標的集合,文化轉向從一個文化的多元視角來開啟技術哲學的新的研究范式。
第二,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是技術文化哲學,在技術文化體中實現對立面的平衡。當下,人類正處在“技術”的時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新興能源及材料技術、生物技術、海洋技術、空間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著社會文化價值觀并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技術發明人,人也發明技術,兩者互為主體和客體。”[21]文化是人及人的活動的文化,技術是人與世界實踐關系的產物,在人—技術—世界關系中的技術哲學,通過對技術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影響進行雙重聚焦,從細節上描述技術與文化的互動。在“技術文化體”范式下,實現科學與人文、理性與感性、物質與精神、解構與建構、控制與引導等諸多兩極分化的和諧與平衡。
第三,文化轉向后的技術哲學更加關注人的價值和人的生活世界。當代技術與文化的共生性決定了技術過程中技術與文化之間以其合力的形式影響著人類社會。技術活動的不確定性往往使其活動后果難以預料,技術的文化價值導向作用就顯得十分必要。在當代,經濟活動規模越大與資源枯竭越快、技術制品使用越多與生態環境越惡化、社會物質水平越高與人的精神狀態越迷失是社會發展中的“悖論”。破解這些問題需要從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文化維度來思考,文化轉向的技術哲學提供了一種理解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的思維方式和新視角,代表著一種回歸至本真狀態下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學。
第四,文化轉向的技術哲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技術哲學只有走出形而上的單一通道,為技術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思路和方案,方能有所作為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克努斯(Kroes)提出了技術人造物的二重性理論,認為技術除了本身的物理屬性之外還具有不容置疑的社會屬性。“一方面,他們是自然物體或者進程,擁有特殊的屬性,其行為受(因果關系的)自然法則管理。另一方面,任何技術產品的本質方面是它的功能;……當我們結合意向性活動和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的因果活動相反)時,這一功能可以被講作是一種社會屬性。”[22]技術哲學應當致力于“構建技術哲學的社會,在社會中為積極地行動維護一條通道,避免形成有限的技術哲學團體。”[23]技術哲學不能僅僅停留在哲學家的理論研究,而應該深入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提供解決技術社會問題的哲學思維。
注 釋:
① 2011年9月,本文作者林慧岳應唐·伊德教授邀請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哲學系訪學,在聽了作者“中國技術哲學的文化轉向”介紹后,伊德認為,他在1990年出版的《技術與生活世界》一書的cultural hermeneutics部分,專門討論了技術與文化的關系并和本文作者有相同的觀點。
[1]吳國盛.技術哲學經典讀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
[2]吳致遠.經典技術哲學階段性特征探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11):61-65.
[3]吳國盛.芒福德的技術哲學[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30-35.
[4]康 敏.來自技術的危險——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追問[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2):48-51.
[5]唐·伊德.讓事物“說話”:后現象學與技術科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高亮華.論當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兼論分析技術哲學的興起[J].哲學研究,2009,(2):110-115.
[7]陳 凡,朱春艷.當代西方技術認識論研究述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3,(3):40-43.
[8]曹繼東.技術文化觀的現象學解析[J].哲學動態,2009,(4):77-82.
[9]陳 凡,傅暢梅.現象學技術哲學:從本體走向經驗[J].哲學研究,2008(11):102-108.
[10]Albert Borgmann.The Here and Now:Theory,Technology,and Actuality [J].Philosophy&Technology,2001,Vol.24,Num.1:5,6.
[11]Verbeek.DevicesofEngagement:OnBorgmann’s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J].Techné,2002,Vol.6,Num.1:72.
[12]Daniel Fallman.A different way of seeing:Albert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J].AL&Society,2010,Vol.25,Num.1:59.
[13]HubertL.Dreyfus.Refocusing thequestion:Can there be skillful coping without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s or brain representations?[J].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2,Vol.1,Num4:422.
[14]Don Ihde.Introduction:PostphenomenologicalResearch[J].Human Studies,2008,Vol.31,Num.1:1.
[15]Verbeek.Obstetric Ultrasound and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A Post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Human Studies,2008,Vol.31,Num.1:13.
[16]遠德玉.技術是一個過程——略論技術與技術史的研究[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189-194.
[17]陳 凡,陳玉林.技術史的“文化轉向”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1):114-117.
[18]林慧岳,黃柏恒.荷蘭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及當代啟示[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7):31-36.
[19]馬林諾斯基.科學的文化理論(黃建波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20]胡長栓.表達生存焦慮的懷疑論——一種反思現代性科學中的后現代主義[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3):75-79.
[21]舒紅月.現象學技術哲學及其發展趨勢[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1):46-50.
[22]Peter Kroes.Technical Function as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J].Techné,2001,Vol.5,Num.3:1.
[23]Durbin.Philosophical Tools for Technological Culture:Comments from an ActivistPerspective[J].Techné,2003,Vol.7,Num.1:40.
On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Empirical Turn to 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Its Prospect
LIN Hui-yue,DING Xue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of the“classic age”,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ealized its“empirical turn”.Under the enzyme catalysis of the phenomenology,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hows obviously a cultural tenden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empirical turn.The culture-turn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rings about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e that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rom the detail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cares about value of human and the life world,and provides the mean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solve the technical social problems by dually focusing o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class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empirical turn;phenomenology;cultural turn
林慧岳,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南 長沙 410003)丁 雪,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湖南 長沙 410003)
(責任編校:文 建)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荷蘭技術哲學后現象學綱領與當代技術哲學文化轉向研究”(09BZX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