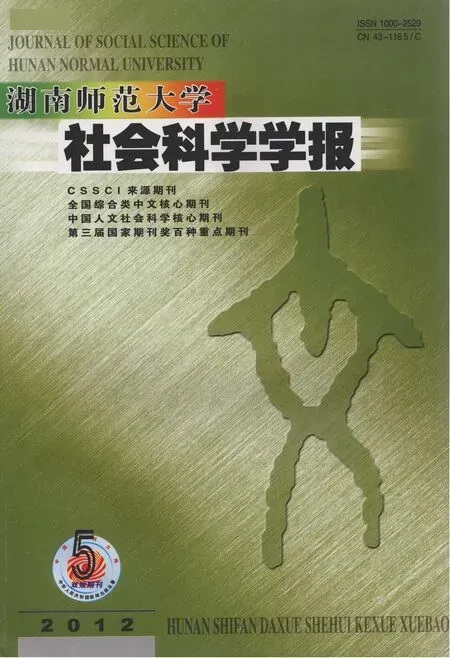從“蛇”圖騰到國家的產生
謝 穡
從“蛇”圖騰到國家的產生
謝 穡
在原始宗教中,動物圖騰是其重要內容之一。狩獵時代的“蛇”崇拜是圖騰的最初形態,由“蛇”圖騰向“龍”圖騰的變遷,實際上是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結果。“龍”的泛化,人類社會也從原始混沌狀況進入有序的分工階段,氏族首領也被作為英雄崇拜。實際上黃帝處在一個人神共處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疆域已經超出了遠古部落的界限,結成聯盟的形式,所形成的封建“酋邦”,已經初具了國家的形態。
蛇圖騰;龍圖騰;黃帝崇拜;國家的產生
在舊石器時代,生產力水平很低,無法解釋自然界的一些現象,只有將某種動物或者植物作為祖先或保護神進行崇拜,相信它們有種超自然的力量,后來過渡為各個部落的原始宗教形式。任何存在物都有其合理性,和宗教一樣,圖騰崇拜同樣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作為一種神秘的宗教現象,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首先,圖騰是氏族的象征和符號,是凝聚氏族成員的精神紐帶和標志,被其成員奉為神靈,他們認為圖騰物與自己的祖先有關。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圖騰也是宗教的起源,宗教與圖騰的關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也是世界民族發展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現象。這種因圖騰崇拜所產生的宗教與氏族制度,顯現出人類進步的階段性與延續性,在人類文明與國家的起源過程中有著里程碑的作用。第三,圖騰表現出人與人、人與動植物之間的某種特殊關系。在抵御自然災害的過程中,圖騰不僅把人聯合起來,也把人與環境結合起來,動植物作為圖騰對象,是因為他們有這種力量,并且可以依靠它們聯合成員共同抵抗自然所帶來的危險。弗洛伊德認為,圖騰是“人類最古老的無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被認為遠比神的觀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產生還要早。”[1](72)可見,氏族社會就這樣在圖騰崇拜中不斷發展壯大,為后來的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奠定了基礎,也為國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一、對蛇的敬畏與龍圖騰的興起
在原始宗教中,對動物的崇拜是其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原始人生產力水平低下,在自然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又無法解釋一些自然現象,于是便對某些動物的奇異能力產生崇拜和幻想,希望借助它們對抗自然。選擇哪種圖騰物取決于對抗自然的需要。由于繁衍生存離不開水與森林,毒蛇便成為傷害人類的主要動物,于是,他們便對蛇和一些相關物產生了敬畏和崇拜,并發展成為原始宗教的一種形式。
上古時以蛇為尊有很多記載。如,《楚辭·天問》記載“女媧有體,熟制匠之?”就是將女媧作為象征蟠蛇圖騰。”相傳伏羲也認為自己是母性始祖與蛇媾合的結果,以蛇始祖;《山海經·海內經》記載,黃帝軒轅氏也認為自己是象征云氣的“四蛇相繞”而生,等等。文物發現,在山東嘉祥武氏祠漢代畫像石刻中,伏羲、女媧是蛇身人首模樣;四川新津寶子山漢代石棺畫像中,伏羲、女媧手捧日月,亦是蛇身人首模樣;河南南陽漢代畫像石刻中,有羲和捧日圖,也是蛇身人首。同樣,其女媧捧璧圖,還是蛇身人首。這些都說明上古時期蛇被認為是人類的始祖而受崇拜。
《山海經》中對蛇的記載有很多:如:“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2](59)。“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山海經·中山經》:“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其邑大水”[2](113)。可見上古時期人們最初在洪水泛濫的時代對蛇類產生恐懼,被視為五毒之首,這是在自然條件惡劣、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下無法抗拒的恐懼心理反映。歷史上的越族,即居住在南方的民族,對蛇的崇拜就很明顯。在新石器時代蛇就已經是他們的圖騰對象,甚至認為蛇就是他們的祖先,實際上,這種崇拜是對祖先神靈的一種追憶,也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敬畏。
同時,遠古時代部落的發展與人口的繁衍密切相關,人越多在自然力面前的生存力就越強,人口增長成為部落存活的首要條件。于是,生殖器的崇拜便油然而生。蛇作為生殖崇拜對象,具體化為女性生殖器的隱喻與象征,這一點在女媧的“人首蛇身”的形象特征上體現得最為確切。據史料記載,女媧摶土造人并“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這是其作為母神的生殖繁衍功能的體現。遠古人類所選擇的女陰象征物,如魚、花木,爾后循著象征女陰——象征女性——象征男女配偶——象征吉祥等這樣一條脈絡演進。但要注意的是,蛇的象征并非單線演進,而是分化為兩個方向,一種是繼續以蛇的形象在后世流傳,另一種是以龍的形象流傳。
漢族也把蛇列為“五顯神”,“五大家”,即狐貍、蛇、刺猬、鼠、黃鼠狼而進行崇拜,漢族的這種崇拜是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中所說的“崇拜是由禁忌轉化來的”。隨著漢族農耕經濟的發展,土地成了漢族賴以生存的基礎,但是自然災害仍然不斷,人們為了祈求人畜平安和農作物豐收,所祭祀和供奉的注意力也就由起初的蛇圖騰轉向了龍圖騰。關于龍圖騰的起源,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曾說過:“龍圖騰,不拘它局部的像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魚,像鳥,像鹿也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態卻是蛇。大概圖騰未合并以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后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并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于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3](703)龍這種虛構的動物如同鳳凰一樣,在結合了眾多動物身上美好的特性之后,就以正面價值形象流傳。
蛇圖騰被龍圖騰所取代,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人類已經從原始狩獵的混沌狀況進入到農耕定居的分工時代,人類思維也由具象向抽象的轉變。不再單單是某種圖騰了,它還兼有水神(雨神)的職責,而且還代表著上天的意志。龍圖騰之所以受到到各氏族部落的崇拜,是因為他們將龍作為主宰雨水之神。農業生產形成以后,雨水成為影響農業的關鍵性因素。而各個氏族、部落生存繁衍都需要農業,出于對雨水的需要和對水神崇拜。這時候的龍已被神化,它超越了部落的界限,受到不同部落、氏族的普遍崇拜。可見,先民對于龍的崇拜其實是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相結合的產物。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龍圖騰慢慢泛化。有些是因為氏族、部落祭祀水神的需要,有些是因為一些部落或民族意識到自己的圖騰有許多不足,需要改換新的圖騰,還有的是因為長期受到主體民族和大民族的影響主動或被動地吸收其他民族的圖騰物。
由蛇到龍的圖騰是個復雜的融合過程。形成這個過程的原因很多:首先,在人類社會從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原先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圖騰崇拜已經不單純是母系社會的特征,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氏族社會的首領也以英雄的形象被崇拜,這時的“龍”形象也逐漸豐富起來。其次,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認識,蛇圖騰的內涵也跟著發生變化,而龍圖騰經過千百年的洗禮和民族融合,已經遠遠超出了蛇的意義,而注入了民族宗教的內涵。
二、龍圖騰的文化意義
一切圖騰都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龍崇拜也一樣是生產力發展的表現。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分析了圖騰的歷史感和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指出圖騰與宗教一樣是物質生活的產物,反映出人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而已。因此,無論是蛇圖騰還是龍圖騰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意義:
首先,龍圖騰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那個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無法理解一些自然現象,對自然抱有屈服和敬畏的心態,渴望得到超自然力量的保護,于是,便產生了對龍的崇拜。由于農耕的需要,龍圖騰作為某種宗教形式是大多數氏族所共有的特征。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凝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生活方式,這種關系逐漸衍生為氏族制度。原始先民從采集到狩獵再到農耕的生活方式,反映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人類社會的文明步伐。一切文化、宗教和圖騰物也是物質發展的附屬物,從原始狩獵社會到農耕社會,人們也從“馬犬圖騰”到“蛇龍圖騰”。農耕需要跟水打交道,需要趨利避害,戰勝水害與利用水力,于是產生了對龍的圖騰崇拜,將龍視為自己的先民或者精神寄托。
中國古代確實存在著龍圖騰,傳說太昊伏羲氏對龍的圖騰就比較可靠,《太平御覽》七十八卷的《韋書·詩含神霧》記載,華胥氏就是伏羲的母親,在“雷澤履大跡”,踩了一個很大的腳印,于是生了伏羲,所謂雷澤就是古人觀念當中雷棲息的地方,后來《山海經》說雷澤有雷神,這個雷神是“人頭龍身”,兼有人和龍的形體特征,就說是“華胥氏履大跡”,生伏羲,雷神就是伏羲氏的男性祖先。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雷雨對人類的影響極大,人們為了抗拒水災而虛幻化出對龍的崇拜,以戰勝水患。
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證明龍崇拜是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古代歷法都是物候歷,根據各種物象確定季節,非常巧合的是春雷始震,地下的蜇蟲便開始蘇醒了。它倆在時間上是吻合的,蛇和雷又聯系在一起了。但是這個聯系有個契機,就是古人確定季節的依據,這個依據見于《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說皇帝以云紀,以水紀,以龍紀,以鳥紀,以云紀就是看天相、看氣候,以水紀就是根據水的漲落來確定季節,以鳥紀就是根據鳥的遷徙確定季節。非常巧合,太昊氏是以龍紀,實際上就是根據蛇類的蜇伏和復蘇的時間來確定季節。蟲動為春,蟲蟄為冬。實際上這個季節也就是現在的驚蟄節,就是春天的開始,它一般在二月初二左右,“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人們將這個節氣視為龍抬頭節,將它視為百蟲之長,這里的龍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蛇的影子。后來人們把這個蛇理想化,神秘化,于是出現了完全意義上的“龍”。甲骨文這個“龍”字,就是在“蟲”字上面加個“王”,蟲中之王為龍。所以龍本身并不存在,它的原型是蛇。對龍的圖騰崇拜也是農耕發展的需要,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先民們需要一個崇拜物去戰勝天災,特別是水患。
其次,龍圖騰也成為民族團結的旗幟,是部落的保護神。龍圖騰在中國古代一開始是太昊氏把它作為族徽,把它作為旗幟,但很快它就成為各個部族的共同信仰。所以,龍、蛇一類的動物,就獲得了一種普遍性的意義。在古人看來,族徽的意義在于保護,如果是龍圖騰的氏族就會得到龍的保護,龍就會為他們消災祈福。
龍作為保護神可以從民間“灶灰攔門辟災”的風俗中得到印證。據說春天開始的時候,人們會在房前屋后撒灰,目的是將毒蟲擋在門外,并且將灰撒成龍的形狀,利用龍的威嚴驅趕毒蟲,達到避邪御兇的目的。這種古老的習俗是崇龍習俗最原始的文化形式。我國至今仍然保持著對龍的崇拜,現在人們在節日里玩龍燈、舞龍獅也是例證。
由于人類社會已經從狩獵過渡到農耕,因此對水的趨利避害就特別關心,這時對龍的圖騰就有著需要水神保護的意義。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民間“汲水”習俗得到印證。在原始風俗中,龍是吉祥物,汲水就是要將龍請進屋來,早晨忌挑水就是為了避免抵觸龍頭,而招來水、旱之災。山西出土的4 000多年前的一個彩陶盤,盤底就繪制了一條口銜麥穗的蟠龍。顯然,這都是將龍神化,將它視為了掌管水的水神,向它祈求風調雨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曰:“龍,水物也。”《淮南子·地形》在解釋“瓏”字說:“禱旱玉也,為龍文,從玉從龍。”可見,古人確實把龍作為水神。民間至今還有這樣的民謠:“二月二,龍抬頭;大倉滿,小倉流;”“金豆開花,龍王升天;興云布雨,五谷豐登。”
第三,龍是君主和力量的象征。龍圖騰不僅僅是氏族的旗幟,而且也是君主和力量的象征。龍圖騰的時代也是英雄崇拜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龍對氏族首領權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部落首領往往借助“龍”的形象來聯合和控制各個部落。如,伏羲、炎帝、黃帝、堯、舜都跟龍聯系在一起。部族首領都將自己作為龍的化身,發展到以后的帝王也稱自己是龍子,代天行道,享受九五之尊。周王自稱天子,利用人們對龍圖騰崇拜鞏固自己的統治,以英雄的形象出現。秦王就開創了“龍”皇帝的歷史,“龍”彰顯著皇帝的威嚴。就連出生貧寒的劉邦,也編造出感龍而生的神話,將自己與“龍”威聯系在一起。這些神話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形成了封建等級制度,加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這個時候的“龍”已經具有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可見,當國與家,地緣政治與血緣關系結合的時候,龍圖騰便從純粹的宗教意義匯入了政治內容,國家觀念也從氏族宗教中派生出來。在以往的封建體制的權力體系下,“龍”作為一種精神對氏族成員起著引領作用。在后來的社會形態中,家天下的私有制使得歷代統治者在“龍”旗下繪制著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在過去出土的很多文物中都繪有“龍”的圖像,這些圖像在這里并不完全代表宗教意義,而是在宗教中所折射出的王權意識和國家制度形態。特別是“龍”旗,不僅僅是對宗教意識的彰顯,更是王權在宗教旗幟下的運行。經歷歲月流轉而成為中華民族共有圖騰的“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的象征。中國歷史上,龍對國家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權威的穩定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由龍圖騰到黃帝崇拜
蛇圖騰所處時代應該屬于母系社會,在紅山文化遼西牛河梁發現的女神廟和女神頭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逐漸過渡到英雄時代,古代的黃帝實際上就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因此,黃帝時代應該就是父系時代。中國古代的很多神話,反映了那個英雄輩出時代男性的社會作用。龍圖騰所對應的農耕文化,需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特別是水、火和各種野獸的侵襲,女性的力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于是男性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得到提升。在龍山文化時期的很多塑像,就是英雄崇拜的縮影。這時的人文始祖都賦予了龍的形象與精神,他們智慧多謀、能征善戰,給部族帶來繁榮和興旺。史料記載,龍圖騰首先在太嗥部落,該部落以龍命官。《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郯子語“太嗥代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民。”司馬遷《補三皇本紀》太嗥皰犧氏:“有龍端,以龍紀官,號曰龍。”《通鑒外記》記載“太嗥部落官號有飛龍、潛龍、居龍”,等等。這些不同的龍,既是官號,也是各氏族的圖騰名稱。可見,太嗥部落無疑是一個以龍為圖騰的部落,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龍,這也是區分不同部落的徽記。而黃帝軒轅氏則是那個時候各個氏族集體崇拜的英雄,他們也將黃帝視為龍。《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軒轅之國,人面蛇身。”《史記·天官書》說:“軒轅,黃龍體,”《淮南子·文訓》說:“中心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已”。《河圖稽命徵》、《漢書人表考》俱說黃帝“龍顏有圣德”、“河目龍顏”。《淮南子·天文篇》也說:“共黃龍,其獸黃龍。”《史記·禪書》又說:“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來”。可見黃帝氏族是以“龍”為主體崇拜的。聞一多考據認為,黃帝的姓“姬”,在上古時期,“姬”通女又通巳“姬”是“女”和“巳”的組合,為“女巳”,認為巳等于大蛇,這類大蛇又被人們稱作龍,被黃帝部落奉為圖騰。這些認識,將龍蛇混為一統。實際上他們都已找到黃帝氏族包括孕黃帝的母族都崇拜蛇,但由于割舍不了“龍”,所以蛇仍歸類于龍。
父系時代是一個人神共處的時代,這個時候的黃帝完全是神化了的英雄,他的出現具有很大神話色彩,黃帝已經被神化。如《帝王·世紀》中就有這樣的說法:“(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于壽丘。長于姬水,因以為姓。日角龍顏,有圣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4](169)。這些都說明父系社會人們對英雄的崇拜,將龍與黃帝聯系在了一起。黃帝時代正是從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的時期,黃帝就是那個時代的氏族英雄,他帶領氏族成員,對抗惡劣環境,發展農耕,種植稻谷,治療瘟疫,制約炎帝,評定蚩尤,統一了幾大部落,成為第一個被萬民愛戴的真“龍”。
自此以來,人們對黃帝就倍加推崇,許多神話、歷史多有褒詞。先秦諸子也對黃帝十分推崇,“世之所高,莫若黃帝”[5](69)。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都將黃帝視為上古帝王,他們對黃帝的描述極力推崇,簡直到了神化的地步。《史記·五帝本紀》對黃帝是這樣描述的:“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黃帝處在一個人神共處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疆域已經超出了遠古部落的界限,真正到了封建酋邦時代,部落間也結成了聯盟的形式,已經初具了國家的形態,黃帝實際上就是各個部落聯盟的盟主,因為,黃帝酋邦實力最強大,他可以收復其他部落。《史記·五帝本紀》有云:“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黃帝酋邦在“龍”圖騰的宗教精神下,以自己強大的力量收復了其他酋邦,并且帶領他們共同去應對自然,改善生產,繁衍生息。正因為如此,黃帝也才真正成為各部落愛戴的盟主,此時的龍圖騰也遠遠超出了母系時代的內涵,不再是泛化的、多元的、神性的共生形象,而發展成為具體的、個別的圖騰對象,龍圖騰形象在這個時候得到了真正的統一,龍的替身就是部落首領或氏族英雄。英雄個人與圖騰物的統一,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社會分層出現,國家制度也在圖騰的統一下逐漸完善。可以說,黃帝作為圖騰物的化身,以其超越的能力融合各氏族力量,戰勝惡劣環境,在古人的心中是人神合一的化身。黃帝的出現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那個時候生產力的發展需要一個英雄人物,農耕經濟的“水”文化,也需要將龍作為圖騰物。可以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與水抗爭的歷史,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女媧、大禹還有黃帝都是治理水患的英雄;龍圖騰崇拜的演變史,也是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從蛇圖騰,龍圖騰,到黃帝崇拜的過程,就是中華民族與自然抗爭,民族融合的過程。到這個時候,民族國家的出現應該說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龍圖騰,黃帝崇拜的必然結果。
四、黃帝崇拜與國家的產生
從龍圖騰的母系社會到英雄崇拜的父系社會,人類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社會生產也由無序的混亂狀況逐漸向社會分工過渡。作為父系家庭軌制開創人的黃帝,從維護氏族利益出發,本能地去適應農耕需要,在龍崇拜的宗教旗幟下,建立起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氏族制度,盡管在那個時代原始先人們還認識不到氏族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有了國家制度的因素,但是,它對于氏族的生存和繁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龍崇拜的產生,英雄與黃帝的出現,使人類由對自然的敬畏轉化為與自然的抗爭,盡管這種力量還很微弱,但也還是部落在黃帝的旗幟下有組織的有序行為。到此時,人類社會實際上已經進入到了比較高級的階段,國家制度也在不知不覺中產生。
這個時代,圖騰崇拜不單純表現出對自然的敬畏,而且還表現出宗教精神,圖騰意思的弱化,社會生產生活也由原來的狩獵向農耕轉向,先民們必須依靠主動的有組織的生產才能保證氏族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對龍的圖騰與對黃帝的崇拜,實際上都與農耕有關。在南方地區,也許早在距今11 000萬年到9 000年前,圖騰崇拜、宗教的革命實際上是與農耕文化相聯系的。比如南方的農業族群,也由以蛇為崇拜的叢林佃獵漁捕收集族群演化而來,當他們進入長江流域后,形成了以湖南為中間的稻作農業,這些稻作族群,生存于河道湖泊及池沼地帶,常常碰到的就是鱷魚的攻擊,而鱷魚和蛇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鱷魚是水中最使人敬畏的精靈,南方的稻作族群,將火的力氣、蛇的神圣都賜予了鱷魚,形成了蛇化的鱷龍,所以,可能西水坡“龍”就是南方龍的原型,伏羲族群的后裔太昊氏族在與東南族群結合的過程當中,繼啟了伏羲時代的虎崇拜。
至此可以認為,“龍”字的構造也是對黃帝族系文化的反映,龍的造型也體現了昊鳥族系的文化精神。由先古到夏代,就沒有過一條相同的龍。考察得知,屬于夷系族群的商族顛覆黃帝族系后,為了統治的需要,在龍崇拜的宗教上,仍然采用黃帝族系的“龍”字,而在造型上則由黃帝族的潛龍變為鱷龍,此龍絕非彼龍,它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精神。自此華夏龍文化才得以定型,國家制度也才有了雛型。可見,“龍”圖騰的變化過程表現的是圖騰統一的過程,反映出圖騰的衰落過程和國家的形成過程。
圖騰的變遷是宗教改革和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人神關系發生轉變,人的關系得到調整,父系社會的英雄再現使黃帝得以成為仁君,給國家制度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從此,圖騰文化便不全是事功鬼神,轉而關注圣王統治與教化民眾,圖騰崇拜也開始從神性的社會秩序中分離出來,去關注發展生產與生活。臺灣學人林安梧先生認為,中西宗教觀念的分野,正存在于不同方式的“絕地天通”之中。中國雖區分“天人之際”卻并不絕對隔絕之,它以道德實踐為首出,認為道德實踐是通天徹地的,能縫合天人之間的疏離,所以中國走的是“連續的路”、“天人合一之路”,是“因道以立教”。反之,西方是以斷裂的方式實現“絕地天通”,于是乎它必須通過一種“道成肉身”的中介連通天人,所以是“立教以宣道”[6](5-20)。
龍圖騰的弱化,龍形的變遷實際上是各個民族大融合的結果,也是國家制度逐漸建立的結果。考古發現,中國原始社會中的圖騰崇拜物,有蛇、牛、馬、羊、鹿、鳥、魚等。但在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知其族屬和所在地域了。有《山海經》的記載,我們才能夠窺出一斑:在桑干河、汾河流域,是龍(蛇)圖騰崇拜的“有熊國”,其圖騰崇拜物之所以不稱“蛇”而謂“龍”,或許就與“有熊”部落方國的建立有關。在這個以“龍”為吉祥物的古國之中,分別有與“龍”崇拜世代通婚的“西陵氏”族團。西陵氏的原始圖騰崇拜物是“三青鳥”,其族團大約居住于汾河、渭河流域。正因為有熊國君娶“西陵氏女”做正妃,其所生之子為嫡出,在后來五帝時期的選賢任能禪讓帝位之中,就占有優先地位。也正因如此,青陽、昌意,就都以鳥為吉祥物。“西陵氏”這一與“龍”崇拜之族通婚的氏族群團之中還包括有羊、馬、魚為圖騰物的氏族成員。比如我們所知的羌族,就以“羊”為圖騰崇拜物;在桑干河流域之北,有以圖騰“牛”、“馬”的民族,蚩尤就屬于其中的“牛”崇拜氏族;在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交界處,或者也包括河南,有以“豬”為圖騰崇拜物的氏族;在長江流域可能存在過以“獅”或“虎”為圖騰崇拜物的氏族。這些都說明,圖騰崇拜已不單純是某個民族的宗教意思,而且還包含著黃帝時代的民族大融合,這種融合是一種集體意思,是有組織的公共行為。
圖騰的弱化和黃帝權威的加強,以及社會生產力提高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的出現。伴隨著私有制而爆發的氏族間的掠奪性戰爭,使氏族出現分化和融合,受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圖騰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具有濃厚的神性價值,而具有了國家的意義。這時期的圖騰便具備了這樣的內容:一是繪制在軍旗上,作為軍隊的標記;二是作為姓氏的來源,限制近血緣者通婚;三是作為國家國徽(盡管那個時候不叫國徽)。從此,“龍”也就由最初的“蛇”形,逐步向以“蛇”為主體,發展為長著牛頭、鹿角、羊須、馬鬃、豬腿、鳥爪、魚鱗、獅尾形狀,綜合了各個民族的文化精神。這樣圖騰崇拜物注入了國家制度的內容,龍崇拜意義的變遷也是國家制度的興起。
結語:中華龍——世界精神的大融合
“龍”的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民族的歷史也經歷了從蒙蔽,到混沌,再到與自然環境主動融合的漫長道路,而進入世界大家庭。現在,“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標志與象征,成為一種民族精神。龍圖騰在產生和形成過程中融合了各民族的特征與精神,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標志。五千年歷史中,這條龍凝聚了地緣和血緣的文化基因,是千萬年來炎黃子孫的智慧與力量才使得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生生不息。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浩浩蕩蕩,璀璨奪目。這部文明史以龍的特性融合世界精神,發揚光大,彪炳千秋。中華龍以其兼容并蓄,以世界的目光造福眾生,成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圖徽和象征。今天的中國,繁榮昌盛蒸蒸日上,正以中華龍的姿態帶領56個民族融入世界民族長河,迎接未來和諧發展的曙光。
[1]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2]佚 名.山海經(任孚先,于友發譯注)[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3]聞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李學勤,張豈之.炎黃匯典:史籍卷[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5]莊 周.莊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M].臺北:明文書局,1996.
Generated from the Totem of the“Snake”to the Country
XIE Qiang
In primitive religions,animal totem was an important part.The“snake”worship was the initial form of the totem in hunting era,the changing from snake totem to the totem of“dragon”,wa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clan society to class society.“Dragon”general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original chaotic situation into the orderly stages of division chiefs as the hero worship.Actually Huangdi was in the period of coexistence of God and human,the territory in this period had exceeded the ancient tribal boundaries,and had formed feudal chiefdom that had begun to take the shape of the country.
snake totem;dragon totem;worship of Huangdi;production of the country
謝 穡,湖南女子學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湖南 長沙 410004)
(責任編校:文 心)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詞的女性特質研究”(2010YB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