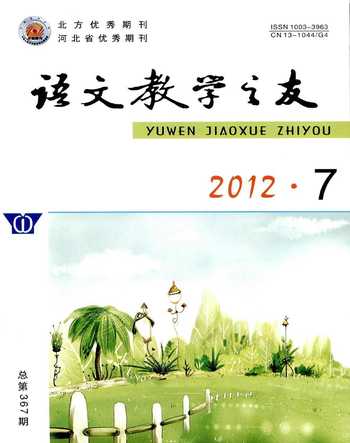有聲當徹天 有淚當徹泉
馬志英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是蘇軾在妻子王弗死后十年即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時所作,開悼亡入詞的先河。金代王若虛《澽南詩話》評價蘇軾的詞說,“眉山公之詞短于情”,然此詞字字浸著血淚,其情深、其意真可達天地,詩人痛心裂肺之狀如在目前。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曾用“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評贊此詞,情殤是本詞的主調。林語堂《蘇東坡傳》有這樣一段話,“王弗天資聰穎知書懂詩,在務實際、明利害方面,似乎遠勝于丈夫,而且頗有知人之明。蘇東坡與來訪的客人談話之時,王弗總是躲在屏風后屏息靜聽……蘇軾的麻煩在于看不出人的短處,而王弗經常會給他一些忠告,比如要提防那些過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失去此等賢內助,對蘇軾來說,是多大的傷痛也許只有他自己明白。加上當時就任的密州,偏僻窮苦不說,又有連年的旱災蝗災,為政十分辛苦。密州上元節火冷燈稀的蕭肅氣氛更讓詞人暗生懷舊情愫,因此在密州清寒的夜里他忽然夢到了亡妻,醒來后記錄下來,文學史上就有了名垂千古的悼亡詞《江城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詞題中的一個夢字,明白地顯示了蘇軾的內心。夢在中國文化語碼中是作為現實的對立面存在的,是自由精神世界的一種指代,尤指精神世界中能夠抗拒黑暗現實的心靈力量。《莊子·齊物論》里說“昔者莊周夢為蝴蝶”,夢見己身化為蝴蝶即是對現實擠壓身心的否定,是自我能夠掙脫束縛的明證。現實越壓抑夢境越是美好,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寫一覺醒來,先前的仙境洞天全部消失,“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詩人用煙霞來形容夢境的綺麗與純凈。《行路難》里有“忽復乘舟夢日邊”一句,日邊是指太陽旁邊,太陽則是一國之君的代稱,夢見經過日邊則表示受到朝廷的重用,但現實卻正是不入朝堂被冷落的處境。
中國文學作品里寫到的夢境大都是現實的反面,表達的是在現實中未能實現的愿望和未能獲得滿足的心意。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夢境中的閑潭落花含有歸家之意,是游子苦苦思念故鄉卻又不能化為現實的哀怨。晏幾道《鷓鴣天》“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別后的相思苦痛只有在夢中相聚時得到撫慰。既然夢與現實世界相去甚遠,為什么還有記下來的必要?因為夢境是自己所愿,是珍貴的瞬間精神滿足,記錄保存下來,算是給日漸被現實折磨得蒼老的心靈一種短暫復原。
蘇軾夢見了什么,詞的下片寫到“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原來是故鄉,是亡妻。故鄉、亡妻與現實有著怎樣的沖突對立呢?密州遠在故鄉千里之外,自己在那里缺親少故,懷舊多少能帶給他一些溫暖,于是曾經與亡妻在故鄉共度的幸福甜蜜隨之翻涌出來,然而生死相隔兩重天,時間已經過去整整十年。
十年的變化很多很大,亡妻現在怎么樣了,詩人只能去猜去想卻得不到驗證,所以他用“茫茫”一詞寫十年時間隔離和生死空間隔離造成的兩不相通,你不知我,我不知你,雙方世界在對方那里都是模糊不清的。用“茫茫”并不新奇,白居易的《長恨歌》里就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關鍵在那個看似尋常的“兩”字。白居易的“兩”字指的是兩處地方,是物質形態的處所,蘇軾的“兩”字突出的卻是雙向情感世界的悲傷與絕望,生者不知死者、死者也不知生者。蘇軾寧愿相信妻子仍然活著,只不過與他不在同一個空間,所以他認為自己與妻子的思念是同時發生的,自己怎樣思念妻子,妻子也是如此思念他。但是思念再怎么強烈也沖不破陰陽的界限,也無法知曉對方生活的世界。這首悼亡詞之所以不同凡響,就在于蘇軾所寫的是“兩情”、“兩廂”的惦念,而非一方對另一方的單向傾吐,兩情的抒情空間遠遠大于單方,情感的豐富度也絕勝于后者,“兩”帶給讀者的心理體驗是均衡完整的。“兩”為駢為偶,是應是和,是形態與意念的雙重完美,是中國偶合文化追求的上乘境界。屈原《離騷》里用“兩美遇合”(君臣攜手)借指政治理想,李清照《一剪梅》用“一種相思,兩處閑愁”來表達兩情相悅,“兩”字完全消融了單向傾訴角度不自覺產生的怨氣,顯得平和深婉。
妻子故去帶來的無期遺恨是“不思量,自難忘”,“不”是“不用”,“自”是“一直”,對亡妻的思念不用著意去想,一直都是難以忘懷的。“不”與“自”寫的是詩人難以中斷的無意識的思念,不管想還是不想,思念就在那里不來不去,仿佛從來不需要去想,但永遠也不會消除。詩人思念亡妻,想對她一吐衷腸,然而“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孤”指孤單,王弗死后,遷葬于四川眉山,葬在蘇軾母親墳塋的旁邊,應該說是有人相伴,為什么非說孤墳?自己也有繼妻王閏之陪伴,為什么要說無處話“凄涼”?這里的“孤”不是泛指,而是專指,專指夫妻間失偶后的孤單,是孤雁南飛,是孤掌難鳴。對亡妻來說,是墳塋中的孤零,對詩人來說,是心靈的孤寂。雙方都沒有昔日伴侶近在咫尺的相陪,都是形單影只的找不到可訴說的對象。“凄涼”一詞既指身體的寒冷,又指內心的悲傷。蘇軾要和王弗訴說的悲傷到底是什么?僅僅是夫妻分離的痛苦嗎?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凄涼”一詞多指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痛苦。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巴山楚水之所以是凄涼之地,那是因為自己是貶謫之身,二十三年的貶謫歲月能不凄苦辛酸嗎?杜甫《寄彭州高適虢州岑參三十韻》“故人何寂寞,今我獨凄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寂寞”“凄涼”表面指分別,實指到老都不被用的悲傷。蘇軾的《雨夜宿凈行院》“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凄涼”更是明確地指出凄涼與名利場有關。詩人想對亡妻訴說的凄涼不是一般的悲傷,而是被迫卷進變法革新派與守舊派斗爭漩渦之中,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不斷地被放外任,左遷、流放,歷盡蒼桑,備嘗艱辛的仕途之痛。這種輾轉的人生使得自己發生了許多變化,“塵滿面,鬢如霜”,如今“縱使相逢”你也一定認不出我來。我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意氣揚揚吟詩作賦的青年才俊了,有的只是顛沛流離的衰老面容罷了。“塵”指塵埃,在漢語語碼中,塵有兩種感情色彩,一是中性,如“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一是貶義,如“風塵”。此處用“塵”偏在貶義,既含旅途艱辛之意,又有污濁使物蒙光之蘊,是蘇軾對仕途起落顛簸的不滿之聲、不平之氣。
既想見你又不想讓你看到今日落魄之我,夜來的幽夢讓我懷著兩難的心理見到了久別的你。“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幽夢”指夢得很沉,很深,身心與現實完全脫離,所以又稱魂魄之夢,蘇軾《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我的魂魄又回到了故鄉,你正在小軒窗下對鏡梳妝,曾經的幸福又重現在我的面前,也許我們又回到了當年,相逢后卻是“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終于見面可以訴說了,為何“無言”?一是想說的太多,不知從何說起,所以無言;二是雖然生死相隔,你我心里自有感應,不需多說,所以也無言;三是好不容易得以一見,不愿訴說不幸讓對方傷心,因此更無言。只有流不盡的珠淚靜靜地撫慰著彼此孤苦的心。此后一別,“料得年年斷腸處”,就在“明月夜,短松崗”。“斷腸”是指悲痛到了欲絕的境地。常建《嶺猿》“杳杳凄凄清且切,鷓鴣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合斷腸。”李白《青溪半夜聞笛》“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情。”《學古思邊》“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腸斷皆因情,相思之情不得故腸斷。你我的斷腸之處就在短松崗,短松崗是指王弗的墓地。墓地種植松柏,取松柏長青歲寒不凋之意,寄托永生長存之意。這是特有的中國語碼,《孔雀東南飛》里“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就是這種用意。本來寫腸斷短松崗就足夠了,交代了妻子和他共同的盟約,然而蘇軾偏偏多用了一個“明月夜”,明月夜是個非常特別的語碼,常常是思人、懷人的代指。不必說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也不必說張九齡的《望月懷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單說《詩經·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夜就是相會的佳期。蘇詞的情深就在這個“明月夜”上,越是美好的明月夜,我的心越在短松崗上傷悲斷腸,良辰美景與思之永不見構成的劇烈反差怎不讓人涕淚滿面?
全詞用樸實無華近似白話的言語,寫實情真,記夢意深,虛實相間之中傳達出難以解脫的絕世情殤,也讓我們看到了作為豪放詞人情真意婉的另一面。
參考文獻:
[1]林語堂《蘇東坡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清朱孝臧編年《東坡樂府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