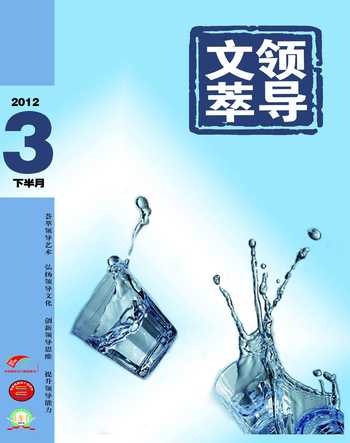政治道德之必要
周保松
讓我們從最常識的地方談起。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這些制度,由國家制定,并要求我們每個人無條件服從。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另一方面卻也建立了秩序,使我們好好活在一起。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個體,就有正當的權利問: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制度為什么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們服從?同樣地,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也有責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是什么。一個不公正的制度,無論多么強大多么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會有缺失,都很難得到公民真心擁戴,都很易出現正當性危機。
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說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某些道德要求。這些要求不是源于暴力、謊言、恐懼,而是基于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這些理由得到公民廣泛的認可,這樣的國家才足稱為具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不少人卻認為,政治的本質,是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是區分敵我階級斗爭,是不談價值只論權術。所以,以道德來要求政治,其實誤解了問題的性質,是不務實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往往好心做壞事。我并不否認,這些現象都存在。
政治會出現,因為我們想活在一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在孤島,我們不需要政治。想活在一起,因為通過分工合作,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一起,卻難免有沖突,因為人總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資源,但資源卻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為獨立個體,在正常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們的集體生活遂恒常處于這樣的狀態:不同個體有不同訴求,這些訴求往往彼此沖突。雖然有沖突,但又希望活在一起,我們于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令人們能夠好好活在一起。這些方法,就是一組組的規則。這些規則,形成我們所稱的制度。在現代國家,憲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規則,并以此界定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要有約束力,就需要強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國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范圍內,有權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并擁有壟斷性使用武力的權利。
由此可見,政治離不開權力,因為需要有武力來維持制度。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不是最自由的狀態,而且很可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無法可依無理可言的戰爭狀態。所以,即使從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卻不可能是赤裸裸的權力,因為政治正是希望透過制度來建立秩序,擺脫以暴力方式來解決紛爭。故此,政治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行使才具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并確保行使權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權監督。道德的觀點,和政治的終極關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而我們的發問,不是從階級、政黨、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體的角度來問,而是從“我”的角度來問,而“我”是活在當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對生命有追求的實實在在的人。這個我,面對巨大的國家,看似渺小,但作為自由人,我并不是天生就須接受別人的統治。我總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問:如果國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嚴,不能助我實現潛能,并活出屬于我的人生,那我為什么要服從?國家又憑什么來統治我?這是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她給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這正是盧梭當年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說,只有國家將“力量轉變為權利,服從轉變成責任”,權力才有正當性可言。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是建構和形成政治道德的過程。
如果以上所說有理,那么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政治現實主義就站不住腳,因為他們鼓吹的,正是一種將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后視政治純粹為權謀利益之爭的活動。在這種觀點下,政治和絕大多數沒有權勢的我們是不相干的,它只是屬于少數權力精英的秘密游戲。
既然政治離不開道德,那么不同的政治理論,不管什么派別,就有必要將辯論聚焦于此。一個合理的政治理論,必須回答以下問題: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公民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和義務?社會財富該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樣才算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關懷和尊重?
最后,或許有人說,即使這些都有道理,現實政治的衰朽腐敗卻實在教人無奈厭倦。剛過世的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哈維爾曾在1986年一篇文章這樣寫道:“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么蒼白的事實。”
很不幸,這是我們今天的處境。也正因為此,我們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