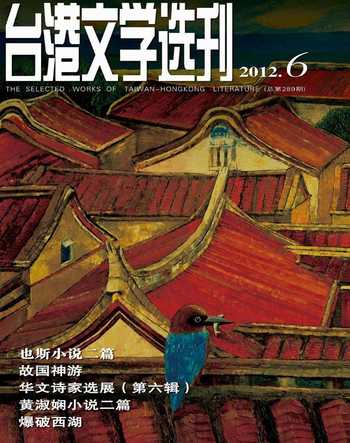跨越文學與藝術極限



吳德亮,臺灣花蓮人。臺灣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臺灣《新聞周刊》總編輯、《自由時報》綜藝版主編、電臺藝文節目主持人等,曾舉辦油畫、水彩、攝影個展及大型藝術展演多次,曾獲臺灣優秀青年詩人獎、中國時報文學獎,作品曾入選多種海內外文學選集、年度詩選、初中語文輔導教材等。
禪語如金(綜合媒材 / 壓克力顏料 / 24cm×80cm / 2011)
結束禪機滌煩的對話,茶幾上一壺東方美人正悠悠釋出七分著蜒的豐姿。客家先民疼惜浮塵子叮咬后的殘芽萎葉,意外成就茶葉醉人的蜜香,不正是“無心恰恰用”的般若智慧嗎?我一躍而起,用壓克力顏料在金色繪板上化作蜂鳥,并寫詩如下:
自東方
美人飽滿的
壺中
以禪為境
汲取蜜香
2007年春天,有關方面為我舉辦了多領域創作個展《千手繆思》。這個個展結合了詩、散文、繪畫、茶藝與綜合媒材,詩人好友須文蔚教授當時曾為文指出:
“在當代文化產物中,作者的身份越來越模糊,因為媒體越來越復雜,在藝術的領域中,文字、繪畫、雕塑與音樂的鴻溝越來越深。偏偏現代社會又是一個視聽媒體導向的文化環境,各種新的整合型藝術創作,‘作者很難定義為提供整體創作的單一個人,個性、風格與視野也就不復存在。
“但德亮卻以全方位的創作打破了現代作者面臨的困境與僵局,在他的系列作品中,以圖像與文字交互構筑的世界,清楚地表現出獨特的風格,而且用不同藝術類型的表現手法,充分彰顯出作者的終極關懷,讓有興趣鑒賞藝術者有機會更認識鮮活的創作理念,這種經驗是相當難得的。”
個人以為:詩書琴棋畫,看似不同領域的藝術表現,在古代中國,卻不過是文人必備的“基本功”罷了。撇開王維以降的“文人畫”不說,東晉精于詩賦、書、畫的顧愷之;唐代擅長建筑、工藝、繪畫的閻立本;北宋文學、繪畫、書法兼精的大才子蘇軾,以及米芾、黃庭堅。至于元代的趙子昂;明代的唐寅、董其昌;清代的八大山人乃至近代的齊白石等,無一不是悠游于各種創作領域的千古風流人物。
即便在西方,從古希臘、文藝復興至近代,稱得上“大師級”的藝術家也多擅長各種媒材的創作,同時揮灑于文學、繪畫、建筑、科學、雕塑、裝置藝術等不同領域,如達芬奇、米開朗基羅、達利、畢加索等,為世人留下一連串美麗的驚嘆號。
但曾幾何時,多領域或稱“跨界”的創作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蛇猛獸,在似是而非的“專業”要求下,運用不同媒材往往被視為異類,甚至以“樣樣通、樣樣松”譏之。1998年“全方位藝術家聯盟”在臺北策辦“跨世紀多元藝術互動展”,同仁跨越繪畫、文學、雕塑、裝置藝術、音樂、數字影像的大型展演,盡管在當時風起云涌,卻也引來不少爭議。
所幸跨越新世紀以來,隨著多元社會的日趨成熟發展,藝術家的觸角又紛紛伸向繽紛的各項領域。官方主辦的“臺北詩歌節”出現了以影音動畫凸顯文字張力的展演。臺北大學也首開風氣創辦“數字文學獎”;明碁電腦(BenQ)公司更與中國時報集團合辦“真善美獎”。除了透過文字的駕馭,抒發或彰顯創作者的情感、意象與陳述外,也相當程度地考驗了21世紀數字時代,創作者必須兼具的影像、后制,或構圖、美學表現等“現代基本功”。
因此在21世紀的今天,不僅文學與藝術可以經由不斷跨越、磨合而再造,媒材與素材的選擇當然也能天馬行空:無論被棄置的舊砧板、洗衣板,或電腦拆下的IC版,甚至用以包普洱茶的茶票紙,都可以成為我創作的媒材。
不斷持續地求新求變,才是檢驗藝術家的惟一標準;而不在單一或復數媒材之間作繭自縛,才能自在馳騁于無限可能的創作領域。
我已經悄悄觀察好幾天了,每天下午約莫三時,一只漂亮的蒼翡翠就會好整以暇,停棲在挺拔燕尾拱托的屋脊上,悠然地享受它的鮮魚大餐。
那是一處由傳統閩南式建筑群所構成的古老聚落,除了村口正對宗祠的大池塘,位置也距離海邊不遠。天氣晴朗時總能透過閣樓高處的花格窗,瞧見對岸迤邐連綿的陸地,有時還隱約可見朦朧霧氣籠罩的樓宇;是我每次前往金門寫生或教學最常住宿的地點。
金門民宿與臺灣各地民宿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古色古香的閩南式建筑。近年金門民宿經過臺灣公園管理處耗費巨資整修,再逐一被交予能提出相當理念的民眾經營。許多百年老厝不僅大致恢復了舊時的輝煌風貌,且大多可以稱得上是“千萬豪宅”了。
尤其讓我感興趣的,是臺灣本島難能發現的蒼翡翠,在金門卻是四季可見的普通留鳥。暗栗褐色的頭頸加上大片翠藍的背羽,與臺灣常見的翠鳥,或同屬翡翠科的黑頭翡翠、斑魚狗等明顯不同,讓人一眼就可輕易辨識。這也是繪畫偏愛用藍的我,最鐘愛的鳥種之一了。
不過,獨來獨往的翡翠,一向出沒于魚塭、埤塘、溪流或海岸的密林中,尤喜棲息在水域旁的樹梢伺機捕魚;即便“午休”時間也會盡量避開不可信任的人類。這樣大膽地將自己暴露在屋宇的棱線上,與我近距離地邂逅,機率甚至還低于樂透彩的大獎吧?就連細小不太對稱的赤足,僅憑肉眼也可望個清晰。看我躡手躡腳地準備腳架與高倍鏡頭,它卻一派輕松地繼續幽雅地吃魚,仿佛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幾天后我起了個大早沿著海岸漫步,忽有“滋——”的嘹亮哨音響起,藍寶石般璀璨的身影剎那在眼前閃過,如沖破拂曉的閃電般掠過水面,隨即隱沒消失在茫茫大海上。那不就是蒼翡翠嗎?稍稍回過神來的我,盡管無法確認它是不是屋頂上的新朋友,仍感到些許別離的悵然。
果然當天下午就不再發現翡翠悠然用餐的身影了,是例行性的飛行鄰近海域覓食嗎,抑或直接飛向對岸的廈門呢?央得周邊洋樓主人的同意,我爬到二樓屋頂上,模擬翡翠停棲的高度與視角望向海邊,主人告訴我,依航向對岸的直線距離約兩公里推算,蒼翡翠依循當地居民小三通的模式,頻繁往來兩岸捕魚,這樣的假設應是可以成立的。
我想起多年前愛妻病危時,窗口竟日流連不去的紅尾伯勞,更加珍惜這樣不尋常的際遇。很想多留幾天看看蒼翡翠是否返回,卻仍勉強自己收拾行囊趕回臺北,因為當天正是妻的忌日。
從一紙風塵仆仆的
茶票中,蘇醒過來
我是異幟后
終結混沌,驚醒黎明
磅礡如無量山悠悠
回蕩的第一餅
曾經翻山越嶺
打瀾滄江去
卻在六十年后的今天
還歌京城的天價拍賣
取一道滔滔奔雨的飛瀑
汲一井激情蕩漾的泉水
以深藏的朱泥
汝窯的蓋碗
用栗紅透亮的茶湯
點絳沉睡已久的唇
點數四周靈閃如星
驚艷的眼
金晃晃的油光層層
輪回杯緣的湯暈
舌鋒出鞘,挑起
酥酥谷雨滋潤的春尖
七分茶氣撼醒三分
抖擻的熟韻
澎湃今夜臺北
喧嘩的魂縈舊夢
仿佛還在勐海的記憶中
系馬,在車間外晃蕩
馬鈴叮當,不斷
傳送曬青的幽香
陽光飽滿的山頭
還有溫柔的叮嚀:
一甲子后的今天
在“非食不可”中
說“贊”
注:紅印標示的是1949年后大陸第一餅普洱圓茶,今日盡管已在北京拍出數十萬天價,但茶友仍慨然分享,特別取下茶票紙以茶汁沾顏料繪寫出瞬間的感動,并取Facebook諧音謂之“非食不可”。
大肚里有船
航行茶湯無遠
弗屆的水域
當春天在龍井
綻放飽滿的新芽
西湖蜜綠的水面
旗槍徐徐釋出
雨前的圓潤
邀月色共舞
地震來時我正向北
從神奈川直入富士山
用玄米輕推
搖醒靜岡不識
愁滋味的煎茶
風們都靜止后
轉向芒種的峨嵋
與浮塵子共謀
吻醒東方
美人金色
琥珀的幽雅
白露之前
經巖礦茶海
西進瀾滄江
汲取千年
古茶樹的日月精華
成就普洱谷花
紅濃透亮的繽紛
霜降未至
忍不住非洲
狂野的聲聲呼喚
航向肯尼亞
用紅茶灼熱的激情
溝通味蕾與枯腸
小雪的大稻埕
風采依舊
以綠葉紅鑲邊包裹
醇厚的航行日志
豐滿而不失婀娜
而那凍頂余韻
都留在大肚里
佛家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雖算不上虔誠信徒,看見刀痕累累的破舊砧板卻也不忍丟棄,順手拈來就是一個絕佳的創作媒材,從早先單純的繪畫到后來費心雕刻彩繪,始終樂此不疲。
砧板上的創作本以各種食用魚為多,希望呈現“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驚心意象,且為了彰顯破舊砧板原有的滄桑,每番創作總是在砧板上直接刻繪主題,背景從未刨光或涂色,保留完整的斑剝原貌,也因此畫面上的刀痕依然清晰可見,粗獷卻也不失真趣。
有天泡茶時突發奇想,既然所用茶盤多為自己創作,或陶板或木塊,不同材質皆可欣然與茶共舞,砧板自然也可以變身融入茶席之中,為茶品做不同詮釋。
但擺放茶具的容顏可不能過于粗陋草率,我破例將砧板上層刨光磨平,再以噴漆做底。彩繪完成后唯恐木質無法承受茶壺之熱,先將中間挖開一個方形凹槽,再將白色磁磚以釉上彩繪制,高溫焠煉后嵌入,就是一塊完美的茶盤了。假如不掀開底部瞧個究竟,很難想象它原先是一塊曾經千刀萬剁的砧板吧?
磁磚上手繪的是臺北承恩門,那是臺北府城僅存的輝煌了;下方背景則是臺北即將消失殆盡的老舊眷村屋舍。我雖非懷舊之人,但每天身處喧囂的都市叢林一隅泡茶,總得為自己保留一方凈土吧?也題了首短詩如下:
用茶湯盈盈
照映
府城的
輝煌
完成后用壺藝名家三古默農手制的巖礦壺來泡茶,特有的陽明山櫻花樹灰幻化的釉色,飽滿的藍妝點天空的白,繽紛的意象為肌里分明的砧板茶盤更添豐姿熟韻。在悠悠茶香中,我懷抱感恩的心,大地萬物皆有可用,即便是不堪使用的舊砧板,一樣可以再現風華,為品茶更添一份感動,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