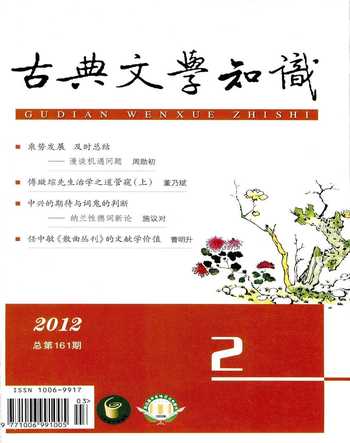曹操為什么寫詩譏諷鄭玄之死?
徐克謙
曹操創作的詩歌中有一首題為《董逃歌詞》的樂府詩,詩中唱到:“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見《三國志》卷六裴松之注所引《英雄記》)大意是說即使那些平日德行完美的正人君子,也難免遭遇不測,并舉鄭玄(字康成)、郭景圖兩人的意外死亡為例。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曾引用這首詩說明曹操文章風格的清峻、通脫,說他膽子大,寫文章沒有顧忌,連當時不久發生的事也可以入詩(《魯迅全集》卷三)。不過,如果我們了解了漢末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曹操與鄭玄之間的關系,就可以看出這首詩其實意含譏諷,且以他人的不幸死亡作消遣,正表現出曹操性格中氣量狹小、尖刻不厚道的一面。
鄭玄(127—200)是東漢末年著名的經學大師,比曹操年長二十多歲。他遍注群經,集兩漢今、古文經學之大成,在當時堪稱是一位“大師”級學者。關于鄭玄的死,《后漢書·鄭玄列傳》記載是病死的,享年七十四歲,沒有明說跟吃酒有關。故后人有以為曹操此詩不可靠,或認為“行酒氣絕”之說純屬曹操杜撰,并非事實(王利器《鄭康成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版)。不過,筆者認為,病死和喝酒死這兩種說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無法兼容的。因為情況完全有可能是:他本來已經有病,再加上多喝了酒,導致猝死。
那么鄭玄既然有病為什么還要喝酒?在哪里喝的酒?根據《后漢書·鄭玄列傳》的記載,鄭玄最終是死在袁紹軍中的,此前他已經有病,夢見孔子召喚他,自知活不久了。當時曹操與袁紹軍事斗爭已到最后關頭,即將在官渡拉開決戰。此時,袁紹派他的兒子硬是把已經生病的鄭大師拉到他的軍中來,為他站臺助勢。估計是軟硬兼施、威逼利誘都用上了,鄭玄被糾纏得沒辦法,只好就范。既然是“請”來的貴賓,到了軍中就難免有酒宴招待,有酒宴就有“行酒”,也就是敬酒勸酒的環節,跟我們當今一些地方的酒文化其實相差不多。當時敬酒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酒宴上某個地位比較高的人物“起為壽”,相當于如今宴會上某個尊長者舉杯說:“我敬在座的諸位一杯,就不一一敬了。”俗話說就是“一梭子把大家都掃了”。在這種情況下,那時在座所有的人就要“避席伏地”,或至少在原位“半膝席”,以表示不敢當。但通常只有席上最尊貴的人物才可以這樣“起為壽”。其他人就只能走到別人的坐席前一個一個的敬,這就叫“行酒”。鄭玄是被強行請來的“大師”,居然還要“行酒”,足見袁紹對他的禮數不高,對大師只是利用,并非真正尊重。這正可以印證《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所謂“紹延征北海鄭玄而不禮”的說法。
“行酒”是勸別人喝酒,但自己也得喝。鄭玄酒量本來是比較大的,據說能飲酒三百馀杯而不醉。有一次袁紹為鄭玄餞行,想把鄭玄灌醉,可是鄭玄從早喝到傍晚,“溫雅之容,終日不怠”。然而越是酒量大的人越是容易忽視飲酒的潛在危險。這最后一次,他已是重病在身,在軍事強人的宴會上卻還得違心地應酬“行酒”,或許身心交病,加上酒力攻心,導致突然死亡,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于那個郭景圖,史書無載,生平不詳,不知何許人也。但既然與鄭玄并提,想來也是當時一位以德行著稱的知識分子。他意外地死在桑園里,這的確有點不太體面。因為“桑園”這種地方,自古就是男女偷情私會之所。所謂“桑間濮上”,就是男女幽會的隱語。《詩經·衛風》有《桑中》一首,就是專門反映男女私奔的。一位文人士子猝死于桑園之中,足以引發人們對其個人品行的想象。但是把這種事寫進詩歌,則恐怕決非出于同情或哀悼的用心,而是明顯帶有譏諷嘲笑的意味。
然而,不管是死于酒宴,還是死于幽會,這些都是別人的不幸。市井之人把它作為飯后茶馀的談資說笑一番也就罷了。而作為一代梟雄、治世能臣的曹操,卻要幸災樂禍地把它們編成樂府歌來演唱,則不免有點非同尋常,且顯得有點刻薄不厚道。那么曹操為什么要寫這首詩譏諷鄭玄之死呢?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曹操此詩實包含幾分嫉妒和嫉恨的意思,他嫉恨鄭玄一直對自己不冷不熱,最后居然被自己的對手袁紹拉了過去。
曹操是當時的政治軍事強人,而鄭玄不過是個研究經學的書生,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什么關系?對這個問題,必須聯系漢代的社會政治文化來看。漢代崇尚經術,儒生的政治地位之高,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之大,遠非后代儒生可比。自高祖劉邦聽了儒生陸賈一番話,明白了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之后,儒生的地位便開始攀升。到武帝“獨尊儒術”之后,經學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儒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影響力也越來越顯赫。在某些情況下,儒生的支持,哪怕僅是象征性的支持,往往能成為新上臺的統治者政治合法性的一種證明。所以新上臺的統治者或想要上臺的統治者,往往要拉攏儒生,特別是有名望的儒生,包括隱士,來為自己站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劉邦有意要廢掉太子劉盈(惠帝),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呂后和劉盈就聽從張良之計,請了“商山四皓”來為自己站臺,四個老儒往那兒一站,居然就讓劉邦覺得太子翅膀已經硬了,扳不倒了,最終只能以一首《鴻鵠歌》安撫戚夫人,說你兒子沒戲了,將來你的主子是她姓呂的(見《史記·留侯世家》)。后來像王莽、光武帝劉秀,直至東漢后期那些陸續上臺的小皇帝以及他們背后的支持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都要想辦法拉攏一些名儒、隱士來為自己站臺,這已經成了漢代的一種政治文化。
也正因為儒生政治地位相對比較高,所以一些儒生敢于以名流自居,公然向中央權威叫板,于是導致“黨錮事件”。但所謂“黨錮”也不是針對所有儒生和士人,只是針對那幫結黨的“清流”,涉及面雖然不小,但對涉案的許多儒生而言,處罰主要不過是不讓他們做官而已。而即使經歷了“黨錮事件”,到了東漢末年靈帝以后,爭奪政治權利的各派勢力,仍然還是要想方設法拉攏名儒或隱士來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加碼。這種政治文化依然存在。
鄭玄在桓帝時期也受“黨錮”牽連,不得做官。不過,對鄭玄這樣本來就不想做官、只想做做學問的人來說,不讓做官,豈不是正中下懷?于是他在不受外部干擾的安靜環境中潛心學問十馀年,終于成了一代經學大師,被當時人譽為“經神”。但是由于他所研究的這個學問,也就是所謂“經學”,本身就是和政治脫不了干系的,再加上他作為名儒和經學大師的名聲,就使得他最終不得不被卷入政治漩渦。到東漢靈帝后期,“黨錮”已解,而鄭玄聲名卻大振,便自然成為各路軍事豪強想要搶奪的人物,因為他們都想要拉攏這位大儒來為自己站臺,以證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據《漢書·鄭玄傳》記載,先是大將軍何進要征辟鄭玄出來做官。鄭玄不得已只好去。雖然受到何進的禮遇,但鄭玄不肯受朝服,而以幅巾見,并且只住了一個晚上就溜了。然后是將軍袁隗上表推薦鄭玄為侍中,鄭玄以老父去世、喪服在身為由推辭了。董卓廢少帝劉辨立獻帝劉協后,以公車征召鄭玄等,鄭玄沒有響應(見范曄《后漢書·荀爽傳》)。董卓遷都長安后,朝廷公卿舉薦鄭玄為趙相,但鄭玄以道路因戰亂被阻隔為由未赴任。當時其他一些地方政要,也對鄭玄給予極高的禮遇,如北海相孔融在鄭玄的故鄉高密縣特立一“鄭公鄉”,并且建造過一座“通德門”以表彰他的德行。徐州牧陶謙也在鄭玄逃避黃巾之亂來到徐州時,給鄭以熱情接待,待之以師友之禮。而在陶謙死后,劉備以平原相領徐州牧,也與鄭玄過從甚密,形同師友。甚至連當時造反起義的黃巾軍,對鄭玄也是禮遇有加。據鄭玄本傳記載,當鄭玄在建安元年(196)從徐州返回高密縣的途中,遭遇一伙黃巾軍,有數萬人。為首的得知遇到的是鄭大師,居然立即下馬叩拜,并且傳令下屬,任何人都不得進入鄭玄故鄉高密縣騷擾。高密縣就因為有了鄭玄,在東漢末年戰亂中竟得以免遭造反派的劫掠。由此亦可見著名儒生在當時的影響力。
曹操也和其他豪強一樣試圖拉攏鄭玄,但鄭玄好像不太給曹操面子。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遷都于許,鄭玄并未在曹操手下任職,也沒有去許都。但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一些禮儀制度方面的問題,如關于帝后之父伏完朝拜禮儀問題,要不要恢復肉刑以代死刑的問題等,確曾主動去征求鄭玄的意見(事見杜佑《通典》卷六十七及《后漢書·應劭傳》)。而當曹操與袁紹爭權奪利到了白熱化階段的時候,雙方都加緊了對鄭玄的拉攏。袁紹在冀州帶兵,大會賓客,曾特意派人把鄭玄請去做座上賓,并且推舉鄭玄為“茂才”,上表舉薦他為“左中郎將”。而與此幾乎同時,曹操則趕緊唆使漢獻帝,以公車征召鄭玄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并下令所經過之地的地方長官要送迎。但是鄭玄卻并不給曹操面子,竟以病自乞還家,根本就沒去上任。
然而最終,就在曹、袁對決的官渡之戰開戰前夕,鄭玄卻又被袁紹派其兒子拉到袁軍中去了。盡管鄭玄可能是被強迫拉去的,但這仍然使曹操感到難堪,咽不下這口氣。直到得知鄭玄死在袁紹軍中,然后其喜也可知,竟然把這事譜寫成樂府小調,在酒席上演唱以解氣,以宣泄對鄭玄趨就袁紹而不是依附自己的怨恨。從這件小事,可以窺見這位一代梟雄,也有心胸狹窄、為人刻薄的一面。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新 書 架
“衣缽相傳,學脈延續。”鳳凰出版社最新推出《卞孝萱文集》(全7冊),總結其一生
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學術界提供查閱的便利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借鑒。《卞孝萱文集》收入
《劉禹錫年譜》、《元稹年譜》、《唐代文史論叢》、《冬青書屋筆記》、《現代國學大師學記》、《冬青書屋文存》等著作,另收錄文章120余篇,分編為“文史考論”、“隨筆雜記”、“序跋書評”三個部分。
《卞孝萱文集》(全7冊),精裝大32開,定價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