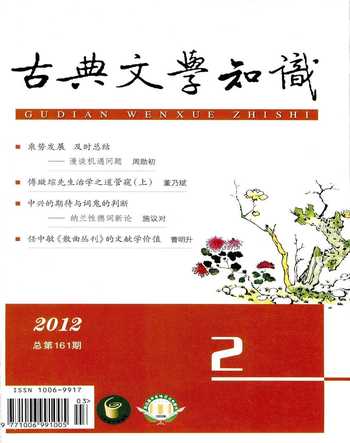陸機《文賦》在韓國
楊焄
近人駱鴻凱曾說:“唐以前論文之篇,自劉彥和《文心》而外,簡要精切,未有過于士衡《文賦》者。……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賦》,陳文之法式莫備于《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廢也。”(《文選學》附編二《文選專家研究舉例》)將《文賦》與《文心雕龍》相提并論,足見陸機此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其對于后世的影響并不僅限于中國本土,也波及到周邊的漢字文化圈國家。在韓國歷代各個不同的文化領(lǐng)域中,就能發(fā)現(xiàn)所受《文賦》影響的種種痕跡。
一、 《文賦》與韓國歷代文學創(chuàng)作
早在唐代末年,新羅文人崔致遠(857—?)在其作品中就已經(jīng)多次化用了《文賦》中的辭句。例如,在奉新羅真圣女主之命而撰寫的《無染和尚碑銘》中說:“大師于有為澆世,演無為密宗;小臣以有限么才,紀無限景行。弱轅載重,短綆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顧。決叵使山輝川媚,反贏得林慚澗愧。”一方面表露對無染和尚的無限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對于由自己來承擔撰寫碑文之責表示信心不足。其中“山輝川媚”一語即約取自《文賦》中的“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陸機原意指佳句處于文章之中,雖無與其相稱者,但仍猶如石中藏玉、水中含珠一樣,可以使全篇熠熠生輝。崔致遠則借用來贊譽無染和尚德行出眾,足以映照世間。另如在《智證和尚碑銘》中,崔致遠說到撰寫該文:“事譬采花,文難消藁,遂同榛楛勿翦,有慚糠粃在前。”“榛楛勿翦”一語出自《文賦》中的“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于集翠”。陸機原賦中的這兩句緊隨著“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兩句,意謂平庸之句因為映襯著佳句而不致被刪除。崔致遠借用來謙稱自己文辭蕪亂,猶如未加修剪的叢生雜木。崔致遠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渡海入唐,隨后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進士及第,歷官溧水尉、淮南節(jié)度使高駢幕府都統(tǒng)巡官,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才重新返回新羅。或許正是在停留中國的十馀年時間內(nèi),接觸到了陸機的這篇賦作,從而得以借鑒其辭句。崔致遠在韓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首屈一指,被尊為“東方文學之祖”。他對于《文賦》的關(guān)注,乃至對于其中辭句的借鑒,自然也或多或少會影響到其后的韓國文人。
在崔致遠之后,韓國歷代文人在創(chuàng)作中化用《文賦》辭句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有些是直接借用陸機的成句或成辭。例如《文賦》正文一開始提到“佇中區(qū)以玄覽”。韓國文人紛紛將之援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如韓忠(1486—1521)《封建賦》云:“佇中區(qū)以玄覽兮,觀吹萬之物理。”沈彥光(1487—1540)《鼓賦》云:“佇中區(qū)而玄覽,索至理于渺冥。”金義貞(1495—1547)《寰宇賦》云:“佇中區(qū)而玄覽,收遠視于八纮。”雖然各篇內(nèi)容不一,每位作者卻不約而同地在自己賦作的開頭借用陸機的原文,隨后才引出后面的鋪陳描繪。《文賦》在論述各種文辭體式時以“詩緣情而綺靡”發(fā)端,自后“詩緣情”一辭也就成為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術(shù)語之一。在韓國文人的作品中也常常可見其蹤跡。例如洪彥弼(1476—1549)《次華使贈湖陰韻二首》其一云:“詩緣情性正非奇,亂派馀波更尚詞。”洪暹(1504—1585)《送別明仲歸覲》云:“詩緣情到無佳句,身為官忙阻別筵。”都用到了“詩緣情”一辭,雖然作者在創(chuàng)作之時未必刻意想要借用《文賦》的成辭,但受到后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有些韓國文人在自己的詩文作品中,有時并不直接借用《文賦》的成句、成辭,而是會對原文略作改動,或加以節(jié)略,然后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有時只對部分語句予以改動,而仍然保持原文的意蘊。例如鄭弘溟(1582—1650)《次歸去來辭》云:“頤情志于載籍,慶賾玄而鉤微。”“頤情志于載籍”一句模仿《文賦》中“頤情志于典墳”的痕跡是相當明顯的。有些文人則在改造、借鑒原文之余,對其本意還會有所引申或轉(zhuǎn)變。例如《文賦》云:“籠天地于形內(nèi),挫萬物于筆端。”而李德壽(1673—1744)《頌己賦》云:“騁藝林而振羽兮,凌學海而揚鬣。籠天地而挫萬物兮,蓋將齊光耀于日月。”《文賦》原文本是論述作者選材謀篇時的特點,李德壽則加以節(jié)取和合并,轉(zhuǎn)而成為對自我才能的贊揚和肯定。某些韓國文人并不僅僅把眼光局限在《文賦》中的個別辭句,有時還會對其中的大段描寫加以括。例如陸機在描繪構(gòu)思之際想象活動的情狀時說:“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接著又強調(diào)創(chuàng)作時需要借鑒前人著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然后說明遣詞造句時存在或難或易的不同情況,“于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lián)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這一大段析理真切、形容絕妙、層次分明的文辭就被韓國文人崔演(1503—1549)改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逐詩魔》云:“精騖八極,神游萬仞。窺蠹簡以剽盜,咀六藝之芳潤。……沈辭若游魚銜鉤,浮藻似翰鳥纓繳。”崔演用擬人的手法和戲謔的口吻,極言文士耽于詩文創(chuàng)作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將《文賦》原文略作修改后,就使之渾然一體地成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二、 《文賦》與韓國歷代文學評論
韓國文人在評論文學作品時也時常會受到《文賦》的影響。韓國學者許世旭在《韓中詩話淵源考》一書中曾提到高麗時期李奎報(1168—1241)的論詩主張和《文賦》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隨后又列舉了朝鮮時代眾多詩話類著作中的議論,來與《文賦》相關(guān)論述進行比較,充分說明《文賦》對于韓國歷代文學批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除了這一類內(nèi)在理路上的隱性影響之外,韓國文人在評論時有時還會直接借用《文賦》里的文辭。在某些場合中,作者會直接說明自己是引用了陸機的意見。例如鄭弘溟(1582—1650)《與趙善述論文書》云:“抑又念詞家才藻,固非一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者,勢有所不免。故昔者坡翁評子由文曰:‘吾弟高處,追配古人,拙處猶愧俗輩。陸士衡亦云:‘或受嗤于拙目。以古準今,若此類何限。而爭名者雖好議論,豈亦并與其所長而掩之乎?”作者批評文人相輕的世態(tài),尤其反對掩人所長之舉,并征引了中國的相關(guān)議論以為佐證。文中所引蘇軾之語出自《與子由弟》:“吾弟大節(jié)過人,而小事或不經(jīng)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隨后所引陸機之語則出自《文賦》。蘇軾的詩文在韓國歷史上備受推崇,早在生前,其文集就已經(jīng)傳入韓國。在高麗朝中期,甚至還出現(xiàn)過文士“專學東坡”的局面。鄭弘溟在征引蘇軾言論證明自己觀點時,連類而及陸機的《文賦》,足見此賦在韓國頗為文人所熟習。
更多的情況下,韓國文人并不加以說明而直接化用《文賦》的辭句。有些時候還沿用陸機原文的意思。例如任叔英(1576—1623)《感舊詩序》云:“緣情動興,采二儀之菁華;體物成章,飛一篇之炤爛。追陸機之賦,眷戀于遺存;視吳質(zhì)之書,殷懃于往昔。”“緣情”、“體物”取自《文賦》中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又如丁范祖(1723—1801)《拙齋洪公遺集序》云:“故其詩緣情設(shè)辭,雅俗雜出。而平澹醇質(zhì),不失軌法之正,盡可諷也已。”“其詩緣情設(shè)辭”一句顯然也受到《文賦》“詩緣情而綺靡”的啟發(fā)。又如權(quán)愈《茶山集序》云:“故意不稱物,詞不逮意,雖浮艷之聲,妖冶之色,間發(fā)于句字之間,而漂翻而無歸。”“意不稱物,詞不逮意”兩句無疑脫胎于《文賦》序中的“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有的作者在化用《文賦》原文時,對原意會有所引申或改變。例如尹舜舉(1596—1668)《睡隱姜公行狀》云:“公之文才,得之天賦。自幼少時,已有作者手,沈詞怫郁,浮藻聯(lián)翩。”化用了《文賦》中“于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lián)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數(shù)句,原文本是形容作者措辭時而順暢、時而艱澀的情形,這里則用以稱贊姜氏文學才能出眾。又如李萬遠(1736—1820)《訥堂遺稿序》云:“若訥堂金公,英才逸氣,苕發(fā)穎豎。”《文賦》原文:“或苕發(fā)穎豎,離眾絕致。”本是用來比擬突出超群的文句,李萬遠卻轉(zhuǎn)而用來表彰金氏的超邁俗流。另如李晚秀(1752—1820)《書〈竹石楓岳記〉后》云:“然以子瞻之慧,識匡廬之勝,應(yīng)接不暇,有不識真面之嘆。今子七日而周萬二千峰,自以為泠然善也。茍使山靈示以杜德機,則子之觀,得無近于一瞬而再撫四海乎?”《文賦》原文:“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本是用來形容思維活動的迅疾和自由,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李晚秀文中用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來做比較,言外對于《竹石楓岳記》作者的走馬觀花之舉似不無微諷之意。
三、 《文賦》在韓國文化其他領(lǐng)域中的影響
除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文賦》在韓國文化的其他領(lǐng)域中也有著一定的影響。韓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丁若鏞(1762—1836)在其《中庸講義補》中曾說:“蔡曰:‘本是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欲屬土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今案:七情之目,始見于《禮運》。原是喜、怒、哀、懼,不是喜、怒、哀、樂。班固《白虎通》又以喜、怒、哀、樂、愛、惡,謂之六情。而古今言六情者更多。《詩序》云:‘六情正于中,百物蕩于外。《漢書·翼奉傳》云:‘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陸機《文賦》云:‘六情底滯,志往神留。何必七情為天定乎?六情、七情之外,亦有愧、悔、怨、恨、懻、忮、恪、慢諸情,豈必七情已乎?經(jīng)云喜、怒、哀、樂者,略舉一二,以概其余。蔡說拘矣。”按《禮記·禮運》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明言有七種不同的情感表現(xiàn),而《禮記·中庸》卻云:“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只提及四種情感。后世儒家學者為了彌縫其間的矛盾,不免有各種牽強附會的解說,上文所引蔡氏之說即為其中之一。丁若鏞認為古人言及“情”時并無固定不變的數(shù)目。《文賦》中的“六情底滯,志往神留”二語本來是描繪文思艱澀的情狀的,但丁若鏞并不關(guān)注其內(nèi)涵具體所指,而是關(guān)注其字面,以此來證成己說,從而強調(diào)研讀儒家經(jīng)典不能膠柱鼓瑟。丁若鏞在學術(shù)上倡導實學,反對儒學者的“空理空談”,從以上所征引的這段議論即可見其學術(shù)視野并不局限在儒家經(jīng)典之內(nèi),對于《文賦》之類詩文評著作也有所關(guān)注。
韓國歷史上施行科舉取士之制,在考試策問時也出現(xiàn)過采摭《文賦》內(nèi)容進入試題的情況。例如朝鮮正祖李祘(1752—1800)在一道策問中曾提到:“頓挫清壯,《文賦》所稱;警誡切劘,東萊有言。則古人之論箴體者,果孰得而孰失歟?”按《文賦》:“箴頓挫而清壯。”清人方廷珪釋云:“頓挫,謂不直致其詞,詳盡事理。”近人徐復觀也認為:“頓挫與直率相反。”則“頓挫”當含有措辭委婉之意。而宋代呂祖謙則認為“箴是規(guī)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強調(diào)直言其事,以達到規(guī)諷警戒的目的。兩者彼此捍格,因而引發(fā)李祘的疑問,遂令應(yīng)試者對其間得失予以評騭。
四、 由杜甫《醉歌行》在韓國的接受看《文賦》在韓國的影響
唐代杜甫《醉歌行》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雖然清人何焯認為杜甫此說源于對《文選》李善注所引臧榮緒《晉書》的誤讀,但在此之前及之后,仍然有不少學者據(jù)杜詩來推斷《文賦》的創(chuàng)作時間。
杜詩在韓國歷史上流傳頗廣,影響深遠。在韓國文人的詩文中也常常可見運用這一典故的。有些是為了悼念早逝的亡者。例如成伣(1439—1504)《祭世通文》云:“綴句權(quán)輿于李賀之七歲,作賦發(fā)揮于陸機之二十。”按《新唐書》本傳謂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gòu)”。作者運用此典,并化用杜詩,旨在突出逝者才能之出眾。又如權(quán)好文(1532—1587)《金秀才三戒薤曲十四韻》云:“昔聞顏夭爭相惜,今見公亡我最哀。天上石麟曾孰送,人間玉樹早能培。迢遙藝苑當年志,籍甚聲名絕代才。文賦陸機堪自敵,平詩子建可追陪。”按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歷數(shù)當時作者,逐一予以評論。作者在此處與杜詩之典連用,將對方比作陸機、曹植,惋嘆其才能出眾卻不幸夭亡。另如全湜(1563—1642)有《挽趙棐仲翊》云:“聰明管輅右,文賦陸機前。”管輅精于卜筮,陳壽《三國志》評為“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這里與杜詩之典連用,突出逝者的智謀、文采超越管輅、陸機。再如吳始壽(1632—1681)《韓進士宗范挽》云:“修短由來不可期,如君早夭最堪悲。陸機未就文章賦,潘岳先題寡婦辭。”潘岳有《寡婦賦》,收入《文選》卷十六,據(jù)李善注云:“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孤寡之意,故有賦焉。”作者既用杜詩之典感嘆死者英年早逝,又用潘賦之典來比況自己賦詩哀悼。
也有借杜詩此典反襯,用以自傷年歲老大。例如崔昌大(1669—1720)《元夜分韻》云:“士衡《文賦》年,我年又加二。奈何愚蒙者,名實或殊異。回顧永傷慚,文理未森邃。如彼未琢玉,冀成清廟器。”感慨自己業(yè)已二十二歲,超過陸機創(chuàng)作《文賦》的年紀,但仍然一事無成。當然也有用杜詩此典來贊譽他人的,例如全湜(1563—1642)《示全上舍命龍》云:“科聲蘇轍后,文賦陸機前。翦拂吾門族,光榮我祖先。”《宋史》本傳稱蘇轍“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第”,詩人將之與杜詩之典合用,意在贊譽對方年少即成就功名、文采斐然,足以光宗耀祖。另如趙(1586—1669)《穌齋先生集后敘》云:“游關(guān)東詩,僅逾士衡《文賦》之年,而其老蒼奇健,奚謝晩年。”稱贊盧守慎(號穌齋)年方二十出頭,就已經(jīng)文章老成,與其晚年作品相較毫無遜色。
以上所述雖然不能直接說明這些韓國文人熟稔陸機的《文賦》,但也可以作為例證,說明《文賦》在韓國文壇所產(chǎn)生的間接影響。
中、韓兩國比鄰而居,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通過上文所舉諸例,不難發(fā)現(xiàn),上起新羅時期,下迄李朝晚期,陸機《文賦》在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以至其他諸多領(lǐng)域之中,對韓國文化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進入現(xiàn)代以后,韓國學界對于《文賦》的學術(shù)研究也逐漸展開。1985年,金世煥教授率先發(fā)表了《〈文賦〉研究——注釋一》,可惜這項注譯工作最終并未能完成。至2001年,車柱環(huán)教授發(fā)表了用現(xiàn)代韓語翻譯的《文賦》全本,并引起了一定的關(guān)注。2010年韓國年輕一代的學者李揆一又出版了專著《文賦譯解》,充分吸收和借鑒了中、韓兩國的研究成果,對全賦做了極為詳盡的注釋、翻譯和評析。這些成果勢必會引導韓國學界更為深入地研究《文賦》,而對于推進和發(fā)展我國的相關(guān)研究無疑也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