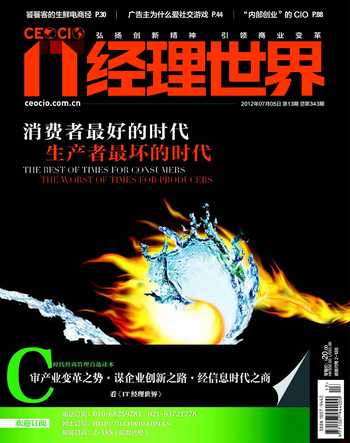歐洲杯場外的默克爾
劉西曼

最近一段時間,德國總理默克爾正在成為各大主流媒體的焦點。甚至有歐美媒體正在給她扣上一頂“亞歷山大”的帽子:導致二次衰退的人。究其原因,無非在于,默克爾堅決反對針對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過度救助,而是要求他們緊縮開支,通過控制赤字的方式來恢復經濟平衡。
德國為何如此固執?
歐洲杯看臺上的默克爾
默克爾的堅持有其道理:第一,如果僅僅是發行歐洲債券等方式刺激經濟,固然會有數字上的短期刺激,但未見得有實質的作用,這種純粹基于貨幣發行的刺激政策最多只能叫“瘸腿的凱恩斯主義”;其二,德國歷史上深受通脹之害,德國央行乃至歐洲央行的天職是控制通脹,如果把通脹這只老虎放出來,經濟也不增長,滯漲的結果未必好過當下。
但是,她的反對者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一方面,很多人認為,緊縮政策很容易讓目前的歐豬國家經濟更加低迷,從而造成雪崩效應,因此主張采取美聯儲式的救助,先度過短期危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顯著強于歐元區經濟,但是央行基準利率卻只有0.25%,日本經濟和歐元區相當,央行基準利率只有0.1%,但是歐元區卻要保持在0.5%,對通脹過于害怕是毫無道理的。
因此,我們看到,德國作為歐元區的金主不樂意掏更多的錢,而歐豬國家的政府只能以“你不下地獄我們一起下地獄”的態度作為籌碼去和德國談判。問題在于,27個歐盟國家當中已經有半數陷入衰退,甚至包括荷蘭、法國等也已經到了衰退的邊緣,2012年Q1保持了0.5%增長的德國也正在滑向臨界點,“救助派”勢力正在與日俱增,而默克爾正在走向形單影只的境地。
所以,我們看到,在G20峰會上默克爾成了獨角戲,而她回家之后就投身到自己熱愛的足球場,而這里,沒有那么多救與不救的糾結,有的只是德國隊摧枯拉朽的足球攻勢……但是,歐洲杯畢竟短暫,走出球場之后,默克爾依然要面對整個歐洲無法短期消解的經濟困局。
于是,走出球場的默克爾做出了第一個小妥協,歐元區四大經濟體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22日的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會議,同意動員大約1300億歐元(約合1600億美元)資金促進歐洲經濟增長,但就是否發行歐元區債券和更多主權讓渡仍存在分歧。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代表“積極救助派”,而德國代表“消極救助派”,不同之處在于,在法國經濟2012年Q1成為0增長之后,法國從德國的密友變為了對立一方。
德國的新賽場?
以前是救與不救的區別,現在卻正在變為怎么救的問題,雙方分歧在于“主權”。
德國認為,在推出歐元區債券、共同承擔債務風險前,歐元區國家需要讓渡更多主權,需要一個中央權力機構監管各個成員國的預算和經濟政策。換句話說,讓德國掏錢可以,但是,這個錢將來怎么花,不能由各國政府說了算,而是應該由歐元區的“中央政府”說了算——換言之,需要由出錢最多、權力最大的德國人主導。
但是,法國代表另一方認為,發行歐元區債券是團結的信號,法國也支持歐元區有統一的財政,但是,法國希望體現作為牽頭人之一的身份、但是又不是出錢的主角,只能一只腳站在意大利、西班牙一方祭出“團結”大旗。
機會與挑戰擺在德國的面前,默克爾站在歷史的門檻上。
我們知道,德國在歐洲歷史上一直處于一個很特殊的地位,一戰、二戰都是德國意圖統領歐洲但與傳統豪強發生利益沖突所致,但是,如今的德國又迎來了一個機會,就是在經濟主權上掌控歐洲的未來——這是一場不流血的角力。德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機會獲得主導權。
但是,德國本身又面臨著巨大風險,畢竟歐元區是一個和美國經濟規模相仿的大經濟體,德國不過擁有不到4萬億美元的GDP,只相當于歐元區的約1/4。如果讓德國全力救助其他歐元國家,按照規模算,就相當于讓美國的加州、德克薩斯州和紐約州三大最強的州救助美國整個國家,或者相當于讓美國救助全球,小馬能拉動大車?還是會也被拖入深深的泥潭?
也正因此,一臉冷峻的默克爾心里,未必不想全力救助并提升德國的地位,但是又戰戰兢兢,不敢輕易拿出底牌——畢竟,美國手里有一張大王、中國手里是一張小王,而德國只有一張A。
在走上這個新賽場之前,德國還需要如履薄冰、審時度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