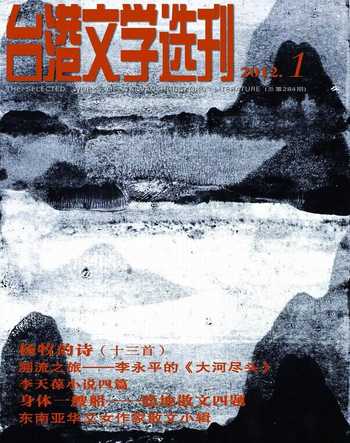大馬旅臺一九九○
有關馬華文學在臺灣的發展,已經有多篇論文作了相當完整的宏觀陳述,“神州”往往是其中最醒目的焦點,不管正面或負面的評價,任何論者都很難繞過它。最主要的因素莫過于史料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本身的傳奇性。以溫瑞安為首的神州詩社,是一個異常獨特的個案,嚴格來說,他們才是第一個馬華旅臺的文學群體。比他們更早以結社方式活躍于臺灣文壇的陳慧樺、王潤華、淡瑩等人,比較像是“結盟”形式的外僑詩社(迥異于神州以馬華詩人為骨干的“結義”),到頭來還是單兵作戰,雖然整體創作成果比神州更勝一籌,卻沒有激蕩出令人口耳相傳的故事。神州個案,已構成一個微歷史的研究,但它的封閉性很容易形成一種刻板印象——讓人誤以為那就是馬華旅臺作家群相濡以沬的典型。事實上,自神州以降,每一代的馬華旅臺作家,都是自由、自主、獨立的創作個體,他們只是因客觀形勢湊在一塊,在文壇與學界的論述中打造成一個馬華品牌。不管是結社或結黨,都已經是陳年舊事。比較糟糕的情況是:在某些不明就里的論述文章里,原本各自為政的馬華作家被歸納成同一個樣式,共同使用一套創作歷程、心理和故事背景,因而產生嚴重(或刻意?)的誤讀。
我們不妨選另一個樣本,來觀察神州以后的大馬旅臺文學發展境況。
“大馬青年社”恐怕是惟一的觀察樣本,表面上看來沒什么討論價值,但多年后回顧,卻有一些有趣的發現。這個社團隸屬于大馬旅臺同學總會,每年獲得一筆活動經費,主要作為推動“大馬旅臺文學獎”等藝文活動,以及編輯每年一期的《大馬青年》雜志。在大馬旅臺同學會的行政架構底下,它是一個文宣及言論功能取向的部門,一個純粹的大馬旅臺學生跨校社團。
一九八九年夏天,也就是大一暑假時,我被大馬青年社的中文系學長邀約加入,也只當作參與一般的社團活動,完全沒有立志要進行什么經國之大業或不朽之盛事。雖然我念的是中文系,但馬華文學在我的腦海里是不存在的,生平第一部馬華(純)文學作品集,是黃錦樹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送我的《龍哭千里》。當時我根本弄不清楚溫瑞安和神州是什么東西。除了此書,我在大一時苦讀的三百本詩集和散文集,全是臺灣文學作品。類似的閱讀趨勢,在大馬青年社的主力寫作者身上獲得廣泛的印證(就我個人觀察所得,他們在現代文學方面下的苦功,遠遠超過臺大中文系的本地同學,而且很快地拉開一大段距離)。
由于青年社太自由,以致有點松散,究竟誰是社長,究竟有多少成員也說不清,有些人只是來客串編務,有些則偶爾出現在讀書會,跟一般大學社團沒什么兩樣。這群散漫分子當中,包括了沉迷于楊牧散文的陳俊華和劉國寄、對書法與篆刻表現突出的林志敏和李干耀(兩人目前任教于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回國后成為馬華在地作家的廖宏強和林惠州,以及最后留下來在大學任教的黃錦樹、鐘怡雯、我、吳龍川等四人。上述十人當中,七人住在臺大男一舍,除了吃喝玩樂,就是埋首讀書。
這個社團的成員可說是當時大馬旅臺生在文學創作上的菁英分子。臺灣現代文學是大伙兒最主要的閱讀對象,尤其是楊牧作品,儼然成為小圈子里的圣經,很多人書架上都有完整的一套楊牧作品(我也不例外,當然還加上眾多臺灣重量級詩人的著作)。印象中除了黃錦樹,似乎沒有人閱讀或談論馬華文學,大陸新時期文學引進來的很有限,我們真正承接、吸收的是臺灣現代文學。從這案例來看,我們這一代大馬旅臺文學的形成跟馬華文學傳統關系不大,跟中國大陸也很遠,可說是臺灣僑教政策底下最意外的豐收。我們的文學基因極大部分來自臺灣文學,后來被收編(或主動投誠)為“在臺馬華文學”,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在大馬青年社成員的身上,可以清楚看見連結到臺灣現代文學母體的臍帶,這是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第二個現象,是對文學獎的熱衷。我對大馬旅臺文學獎的初次接觸,來自《大馬青年07·(第六屆)大馬旅臺文學獎專輯》,雖然那是小圈子里的文學競賽(投稿近百件),也算是大馬同學的年度大事。文學競賽意識在大馬青年社里相當濃烈,文學獎是相對公平的競技舞臺,參賽得獎主要是為了獲得臺灣評審的肯定和點評,對學徒期的旅臺寫手而言,很重要。當時我們可以參加的文學獎包括:臺大文學獎、師大文學獎等校園文學獎,以及某些地方性副刊和雜志社舉辦的征文比賽。不可忽略的,還是兩大報(編者按:指《聯合報》、《中國時報》)文學,那是很大的憧憬。我們正巧遇上臺灣文壇的“文學獎盛世”,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間,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等四人,一共獲得十二項次的兩大報小說獎,隱然形成一支大馬作家的得獎隊伍。接下來,就輪到馬來亞大學畢業后來臺就讀研究所的林幸謙,以及臺大畢業后返回新加坡的蔡深江,先后獲得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的中國時報散文獎,對大伙兒起了一定的激勵作用。大馬青年社結束之后,這股參賽意識熊熊燃燒了近十年。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主要由林幸謙(散文)、鐘怡雯(散文)、陳大為(散文與新詩)、黃錦樹(小說)在十年間密集得獎;除了十一項次的兩大報文學獎,還包括其他新設的文學大獎。第二階段的成果加上第一階段的累積,以及鮮明的赤道主題,強烈地形塑了馬華(在臺)作家的群體形象。
第三個現象最為獨特,圈子里總是彌漫著一股知識分子意識,有好幾位學長都希望能夠考上研究所(說不定在潛意識里都在期許自己將來能夠為大馬華社做些什么)。我特別記得,有一次正在念研究所的曾慶豹學長來演講時,大家好像看到偶像似的十分興奮。“知識分子”這四個字,在當時大馬旅臺同學心目中有著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從《大馬青年》的內容可以看出,純文學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養成。旅臺總會很重視對臺灣僑教政策的省思,對馬來西亞種族關系和華人政黨的問題探討,一如黃錦樹在《大馬青年07·編輯室報告》里所言:這本刊物的前四期,更強調“大馬青年意識”,強調對國家的關懷與了解,強調“使命感”(頁四)。在這一期,陳俊華寫了一篇談歷屆旅臺文學得獎作品的文章,有一段話很有意思:“這一代的大馬旅臺同學就是一群喝著渾濁的湖水長大的知識分子。生活在這么一個政治氣候陰晴難測的時代里,大馬旅臺知識分子背負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披掛著僑生的外衣,來到臺灣——這一塊彈丸之地、一個浩瀚博大的中華文化的縮影體——探求更高深的知識領域,他們的臉上有著遠比其他國家的大學生來得沉厚的憂郁氣質。或許這就是詭譎陰郁的馬來西亞政治氣候所致,或許這就是過早從上一代那里感染到失望和不滿的結果”(頁七)。這番話聽起來好像是革命宣言,但它很生動、準確地傳達出那個年代的“大馬青年意識”。在早期的旅臺得獎作品里,確實表現出陳俊華所謂的知識分子意識。他的觀察,可以放大到整個大馬留學生圈子,尤其在當時的大馬旅臺總會及其屬下的數十個分會的干部之間,確實有這樣的氛圍。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一向都很重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師生,被整個大馬華社賦予一股任重道遠的使命感,仿佛將華社的興亡全交付給中文系的讀書人。這種很強烈的“薪傳意識”,確實讓馬大學生心靈早熟,對旅臺同學的催熟作用略低。當時我的世界只有純粹的現代文學,我不知道該具備什么樣的知識水平才稱得上知識分子(也從來都沒想過要當),感覺上,比較像是具有社會運動色彩的文化評論人。在大馬旅臺圈子里,對華社的使命感確實存在,日常話題中經常談到“回去”之后的打算,或者“留下”來持續茁壯的企圖。這股使命感,不知不覺地滲透到文學創作里頭,當我們開始關心馬華文學的時候,留學期間大量閱讀的臺灣現代文學作品,自動成為馬華文學的對照,于是產生了后來的烽火。黃錦樹的燒芭行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把火的背后,有使命。
一九九○年六月出版了《大馬青年08》之后不久,大馬青年社就被大馬旅臺總會中斷了金援,被迫關門大吉。但它很湊巧地聚集過一批后來成為馬華重要作家的年輕寫手。嚴格說來,它并沒有真正造就過什么人、成就過什么大事,它僅僅見證了幾位馬華作家的學徒期,以及那個時代的氛圍。
短命的大馬青年社,很反諷地象征了旅臺文學“結社時期”的終結。由始至終,這個社團只是大馬旅臺同學會體制下的產物。這些年輕的校園寫手都沒有結社的興趣,權當作校園社團來玩,根本算不上“結社”;對我們而言,結社已經是舊時代的思維和產物。不過,很難避免的是,來自一代又一代旅臺人和馬華社會的使命感,不時會從四面八方滲透進來,在日常言談之間相互感染,特別表現在習作之中。至于知識分子的養成,我們那批人都沒有成為華社慣常定義下的知識分子,我們只成為純粹的文學研究者,投入日后的馬華文學研究。
在過去四十幾年中,三萬多名大馬旅臺同學當中,先后培育出數十位成為馬華文學主力的作家,對他們來說,留學臺灣的短短四年往往是整個創作生涯中最關鍵的階段,豐富的文學資源開拓了年輕寫手的文學視野,甚至決定了往后二三十年的個人寫作風格。當然,要在四年間融入臺灣社會是不可能的,只有極少數留下來繼續念研究所的同學,才有機會深入臺灣。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旅臺寫手帶走了屬于他的臺灣經驗,慢慢消化、融入日后的創作思維當中。說起臺灣,總是一番緬懷與不舍。
在九十年代成為碩、博士研究生,持續在臺灣的文學獎盛世中奮戰的,只有黃錦樹(1967-)、鐘怡雯(1969-)、陳大為(1969-) 、吳龍川(1967-)、辛金順(1963-)五人。前三人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文學獎的征途,在二〇〇〇年以后鮮少主動參賽。近十年以來在文學獎方面表現最突出的,首推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百萬首獎的張草(1972-),以及贏得第一屆溫世仁百萬武俠小說大獎的吳龍川,前者回大馬開業從醫(張草的創作質量都不錯,由于大馬身份不突出,所以經常被論者忽略),后者毅然辭去專任教職,留在中壢專心寫武俠小說。至于跟林幸謙(1963-)同屬“前六字輩”的辛金順,年少時即成名于大馬,來臺后奮斗了十余年,終于在旅臺的最后幾年拿下重要大獎,今年回大馬教書去了。
我們這些“大馬旅臺作家”,在近年的學術論述中慢慢演化為“在臺馬華作家”,有人說這是離散,有人說這是收編,也有人說我們始終擁抱著馬華主題,是因為無法融入臺灣社會。其實每個旅臺/在臺作家都是一個特殊的個案,大家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生涯都大不相同,誰都不能成為典型。就我所了解的,從雜志主編、補教老師、行銷業務、工地勞工、街頭工讀,都在旅臺眾人現實生活的歷練之內,這么多年下來,很難說跟臺灣社會不能融合(反而有時回到馬來西亞,會感到些許的陌生)。馬華主題是很重要的原鄉書寫,這里頭有很多過去的異國文化經驗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創作的豐富礦層,不能就此斷言作家的土地情感和寫作意識。
馬華旅臺/在臺文學的問題很復雜,有些東西連我們自己都弄不清楚,看來有必要進行更細微的個案研究,才能一一廓清。以大馬青年社來說,資料極為匱乏,只能憑印象和有限的文獻來寫。其實它是有故事的。一部沒有故事、只有文學議題和創作文本的馬華文學史,何其乏味。作為上世紀九十年代馬華旅臺文學的第一個切片,其中蘊含著許多值得探勘的細節。
(選自《臺灣文學館通訊》2011年12月號)
·責編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