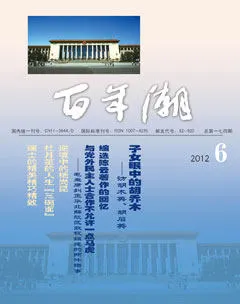外交生涯片斷追憶(續(xù))
編者按:本刊今年第2期刊登了中國駐越南原大使李家忠撰寫的《外交生涯片斷追憶》一文。主要回憶了他四次被派往越南工作期間的所見所聞。為了更全面地反映所親歷的中越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歷史,李家忠特續(xù)寫此文,作為對上文的補(bǔ)充。
炮火下的中國大使館
1965年春我被派到駐越使館工作時(shí),美國正逐步把侵越戰(zhàn)火擴(kuò)大到越南北方。面對這種嚴(yán)峻的形勢,大使館的工作也相應(yīng)做了調(diào)整,遵照國內(nèi)指示,所有外交官夫人和女工作人員都撤回國內(nèi),留下的男同志也都做了必要的準(zhǔn)備。當(dāng)時(shí)河內(nèi)的備戰(zhàn)氣氛越來越濃,到處都修建了防空壕和個(gè)人掩體。各街道都架有廣播喇叭,市民可隨時(shí)聽到美國飛機(jī)的動向。中國援越部隊(duì)為大使館修建了四個(gè)鋼筋混凝土的防空洞,每個(gè)可容納20多人。各辦公室和宿舍的門窗都貼上了紙條,防止一旦被炸時(shí)玻璃碎片四處飛濺。此外還準(zhǔn)備了蠟燭和火柴,防止停電。每人都配備了棉大衣和手電筒,便于夜間跑防空洞時(shí)使用。
不久,美國飛機(jī)便開始了對河內(nèi)和越南北方其他城市的大規(guī)模轟炸。大使館的工作秩序也隨之被打亂。每當(dāng)廣播中說“敵機(jī)距河內(nèi)50公里”時(shí),我們便要停下手頭的工作,準(zhǔn)備鉆防空洞。當(dāng)廣播中說“敵機(jī)距河內(nèi)20公里”時(shí),便要立即跑向防空洞。有時(shí)未等進(jìn)洞,美國飛機(jī)就已經(jīng)飛到市區(qū)上空,這時(shí)我們會聽到美國飛機(jī)投下炸彈的爆炸聲和越南高炮部隊(duì)發(fā)射炮彈的吼叫聲。待美國飛機(jī)轟炸過后,廣播中會通報(bào)說“敵機(jī)已經(jīng)遠(yuǎn)去”。這時(shí),我們再從防空洞中走出來,繼續(xù)工作,有時(shí)一天要跑防空洞兩三次。從1965年春到1970年春,我在越南工作5年,其間總共鉆過多少次防空洞,無法統(tǒng)計(jì)。
那時(shí)越南軍方尚不能及時(shí)掌握美國飛機(jī)從泰國烏塔堡空軍基地起飛的動向,每次都是中國情報(bào)部門了解情況后,立即通過中國大使館武官處,通報(bào)給越南軍方。1966年12月14日中午,大使館的同志正在食堂用餐,武官處的同志大聲說:“請大家快些吃飯,有情況。”我們便迅速做好了相應(yīng)準(zhǔn)備。下午3時(shí)許,多批美國飛機(jī)轟炸河內(nèi)市區(qū),其中先有4架美機(jī)在大使館上空盤旋,其中1架于3時(shí)24分向大使館俯沖,發(fā)射一枚空對地導(dǎo)彈,炸毀了大使館電影廳大樓西南角,樓頂被摧毀近一半,門窗玻璃全部粉碎。與大使館一街之隔的新華社河內(nèi)分社的門窗也大都被炸毀。幸虧大使館同志都及時(shí)鉆進(jìn)了防空洞,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后經(jīng)越南軍方專家鑒定,美機(jī)發(fā)射的是“百舌鳥”導(dǎo)彈。
下午6時(shí)15分,胡志明主席步行來到大使館,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問。朱大使、陳亮政務(wù)參贊和陳皓武官陪同胡主席查看了被炸現(xiàn)場。當(dāng)聽說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的人員都沒有受傷時(shí),胡主席連說:“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主席又詢問大使館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確保大家安全,大使館有沒有疏散計(jì)劃。朱大使一一作了報(bào)告。胡主席對朱大使和在場的中國同志說:“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們將繼續(xù)戰(zhàn)斗。”
12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發(fā)表聲明,強(qiáng)烈譴責(zé)“美帝國主義向中國人民蓄意進(jìn)行的嚴(yán)重挑釁行為”。那時(shí)正值“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許多外交文件都帶有濃厚的“文化大革命”氣息。聲明說:“美帝國主義竟然明目張膽地向中國駐越南的外交代表機(jī)構(gòu)開火,妄圖用戰(zhàn)爭恐嚇試探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戰(zhàn)斗到底的決心。美帝國主義真是瞎了眼睛,看錯了對象。越南人民是嚇不倒的,中國人民也是嚇不倒的。”“中國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的全體工作人員,對美帝國主義這一嚴(yán)重的戰(zhàn)爭挑釁行為表示最大的憤慨和最強(qiáng)烈的抗議。”他們表示“一定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爭取抗美救國斗爭的最后勝利,不惜作出任何犧牲,以完成祖國人民交給的任務(wù)”。
我所見到的胡志明
早在上小學(xué)時(shí),就聽地理課老師說,越南是社會主義陣營東南前哨,越南的領(lǐng)袖是胡志明。后來我學(xué)了越南語,又到外交部工作,心想總有一天會有機(jī)會見到這位領(lǐng)袖。
1964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率中國檢察院代表團(tuán)訪問越南,我從外交部被臨時(shí)借去為代表團(tuán)當(dāng)翻譯。越方知道張鼎丞是中國的老革命,接待十分熱情。
11月3日上午6時(shí),胡志明主席在河內(nèi)主席府接見張鼎丞檢察長和代表團(tuán)全體成員。之所以安排在早6時(shí),是因?yàn)楹飨刻烨宄?時(shí)多就起床了。那天胡主席身穿淺黃色咔嘰布中山裝,外面還披上一件黃色外衣,站在主席府大廳前臺階下迎候我們,并與大家合影留念。
作為翻譯,當(dāng)時(shí)我有些緊張,怕不能完成好翻譯任務(wù)。但胡主席毫無大首長的架子,舉止和談吐十分隨和,并且基本上都在講中文,就像和朋友與家人聊天一樣。他還站起來端著盤子,逐一請大家品嘗餅干,并介紹說這是主席府的廚師用木薯粉制作的。會見氣氛極為輕松和親切。
張鼎丞檢察長談到中國檢察部門存在的問題時(shí),胡主席說,中國存在的問題,越南都有,甚至中國沒有的問題,越南也有。胡主席還回憶起當(dāng)年他在中國上海從事革命活動時(shí)的見聞。他說,20世紀(jì)30年代的上海,有些人受英、法殖民主義思想的影響,崇洋媚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外國名字。有一個(gè)人本來姓白,卻改成姓“懷特”(White),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至今我仍珍藏著那次胡主席與全團(tuán)的合影照片。
1965年春我到駐越南大使館工作不久,中國鐵路雜技團(tuán)到越南訪問演出。朱其文大使特意在大使館安排一個(gè)專場,請胡主席和越南其他領(lǐng)導(dǎo)人前來觀看。那天,胡主席身穿一件越南農(nóng)民常穿的棕色短衫,腳上穿一雙用汽車輪胎改制的涼鞋——抗戰(zhàn)鞋。演出地點(diǎn)在大使館的電影廳。當(dāng)朱大使陪同胡主席步入會場時(shí),在場的大使館人員、中國留學(xué)生和在越南工作的中國專家代表共200多人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迎。朱大使請胡主席在前排沙發(fā)上就坐。但胡主席沒有立即就座,而是面向全場,舉起手示意大家先坐。可是大家非但沒有先坐,反而鼓掌更熱烈了。這時(shí),只見胡主席一下子坐在了電影廳小舞臺的臺階上。在場的人只好坐了下來,朱大使才將胡主席請到沙發(fā)上就坐。
胡主席與周總理夫婦有著深厚的革命友情。早在20世紀(jì)20年代,胡主席和周恩來就在法國巴黎相識。1924年到1927年,胡主席(當(dāng)時(shí)名為阮愛國)在廣州從事革命活動時(shí),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阮愛國還參加了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正因?yàn)槿绱耍飨瘜χ芏鱽矸驄D十分關(guān)心。大約在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的秘書瞿文爍到大使館見我,轉(zhuǎn)達(dá)胡主席內(nèi)心的不安。瞿秘書說,胡主席看到外電報(bào)道說鄧穎超同志已經(jīng)去世,但沒有見到中方的相關(guān)報(bào)道。這使胡主席非常為難,如果鄧穎超同志真的去世了,他一定要發(fā)唁電;但如沒有去世,發(fā)唁電肯定會造成誤會。因此請中國大使館幫助了解實(shí)情到底如何,并把結(jié)果告訴胡主席。
我把瞿秘書所談的內(nèi)容向大使館領(lǐng)導(dǎo)作了報(bào)告。領(lǐng)導(dǎo)感到非常為難,鄧穎超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大姐,突然向國內(nèi)詢問這樣的問題,實(shí)在不好開口,但這又是胡主席關(guān)心的問題,而且還等待答復(fù),最后只好如實(shí)向國內(nèi)報(bào)告。
幾天后,大使館收到了鄧穎超大姐的回復(fù)。我清楚地記得信中的第一句話是:“敬愛的胡伯伯,我還活著。”下面的意思是說現(xiàn)在的身體比前一時(shí)期還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感謝胡伯伯的關(guān)心,祝胡伯伯身體健康,希望能在北京與胡伯伯見面。
越南南方解放區(qū)之行
1974年6月,我作為外交部亞洲司翻譯,跟隨我國駐越南南方共和臨時(shí)革命政府大使王若杰,前往越南南方解放區(qū),參加該政府成立5周年慶祝活動。
越南南方共和臨時(shí)革命政府成立于1969年6月。它的成立完全是為了外交斗爭的需要,旨在爭取國際社會對越南抗美斗爭的廣泛支持。實(shí)際上,它沒有固定的駐地和辦公處所,其主要官員也都是越南勞動黨的干部,一切活動均接受越南北方的領(lǐng)導(dǎo)。王若杰大使是從部隊(duì)調(diào)來的老革命,1955年即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中國駐也門大使。現(xiàn)在雖身為特命全權(quán)大使,卻無法赴任,又不能兼任其他職務(wù),平時(shí)只能呆在家里,偶爾到外交部亞洲司看看相關(guān)文件,參加一些與越南有關(guān)的外事活動。
1973年,王大使曾去越南南方解放區(qū)參加過臨時(shí)革命政府成立4周年慶祝活動,這是第二次。當(dāng)時(shí)越南的抗美斗爭仍十分激烈,南方解放區(qū)和敵占區(qū)犬牙交錯。北方經(jīng)過美國飛機(jī)多次的狂轟濫炸,道路交通已被嚴(yán)重破壞,沿途遍布彈坑,美國飛機(jī)還會不時(shí)再來轟炸。乘車前往南方解放區(qū),無疑是一次艱苦和危險(xiǎn)的行程。但這些對于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王大使來說算不了什么。而我,60年代曾在駐越使館工作過5年,經(jīng)歷過美國飛機(jī)的無數(shù)次轟炸,而且年輕力壯,去一趟南方也不算什么問題。比較難辦的是如何處理與同行的蘇聯(lián)大使的關(guān)系。
當(dāng)時(shí)承認(rèn)越南南方共和臨時(shí)革命政府的國家不過五六十個(gè),由于條件艱苦,越方無法邀請更多國家的使節(jié)前往。中國和蘇聯(lián)是支援越南抗美斗爭最多的兩個(gè)社會主義國家,肯定在被邀請之列。但當(dāng)時(shí)中蘇關(guān)系高度緊張,中國既不承認(rèn)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拒絕同蘇聯(lián)一道參加帶有“社會主義陣營”色彩的活動。為解決這個(gè)問題,越南又邀請了緬甸和阿爾及利亞兩個(gè)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一道前往,這樣中國便不好說什么話了。在整個(gè)行程中,我們始終注意體現(xiàn)出堅(jiān)定、鮮明的反修立場,王大使未同蘇聯(lián)大使說過一句話,未打過一次招呼。
當(dāng)時(shí)四位大使乘坐的都是吉普車,但中方拒絕乘坐蘇式“嘎斯69”吉普車。越南只好找來一輛中國援助的北京牌吉普車,供王大使乘坐。那時(shí)的北京吉普質(zhì)量尚未過關(guān),不僅彈性差,開起來顛簸厲害,而且車門關(guān)閉不嚴(yán),沒開一段路,車門便會松動,自行打開。越方隨行人員只好臨時(shí)找來一根橡膠帶,綁在車門上,樣子十分難看。四輛車被編在一個(gè)車隊(duì)里。盡管我們努力體現(xiàn)出不亢不卑、落落大方,但在當(dāng)時(shí)我卻真切地感受到我們的北京吉普無論在外觀上,還是在性能上,都顯得十分遜色,內(nèi)心始終有一種說不出的尷尬。至于蘇聯(lián)大使有何想法,則不得而知。
時(shí)隔30多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受到了包括俄羅斯在內(nèi)的外國朋友的高度贊揚(yáng)。中國也成為了汽車生產(chǎn)大國,當(dāng)年乘坐北京牌吉普車的尷尬局面再不會出現(xiàn)。我深刻感受到社會主義祖國的強(qiáng)大是外交工作的堅(jiān)強(qiáng)后盾,同時(shí)也是外交人員的體面和自豪。
親歷朱镕基總理訪越
早就聽說過朱镕基總理的坎坷經(jīng)歷和他雷厲風(fēng)行的作風(fēng),但一直沒有機(jī)會近距離接觸。直到1998年以后才有兩三次機(jī)會。
1998年8月,外交部召開第九次駐外使節(jié)會議,我作為駐越大使回國參加會議。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親切會見了全體使節(jié),并和大家合影留念。會議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請朱镕基總理在京西賓館為大家做我國經(jīng)濟(jì)形勢報(bào)告。那天我坐在會場中間靠后的座位上,但仍能清楚地看到朱總理的音容笑貌。只見他從容走上講臺,手里沒有拿任何講稿或提綱,就這樣坐下來一口氣講下去。
報(bào)告的內(nèi)容不必在這里重復(fù),但有兩個(gè)細(xì)節(jié)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dāng)時(shí)工人下崗問題比較突出,朱總理在談到下崗工人生活困難時(shí),深情地背出了老百姓中流傳的幾句順口溜:“一生跟著黨,老了沒人養(yǎng),想要靠子女,他們?nèi)聧彙!弊鳛?3億人口的總理,對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令我深受感動。
在談到外貿(mào)出口時(shí),朱總理說形勢很嚴(yán)峻,今年的出口額度必須完成,這是立下了軍令狀的。講到這里,朱總理話鋒一轉(zhuǎn)說,但外貿(mào)部長卻說要量力而行。此時(shí)外貿(mào)部長就坐在下面。散會后,那位部長從我身旁走過時(shí),有人拍他的肩膀說:總理又點(diǎn)你的名啦!部長則說:我經(jīng)常被點(diǎn)名,這也是對自己的鞭策。聽到這話,我自然想到了周總理,當(dāng)年周總理就經(jīng)常當(dāng)眾批評部、司兩級領(lǐng)導(dǎo)干部。但沒有人記恨,而總是把總理的批評作為對自己的鞭策和教育。直到幾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許多同志寫文章回憶周總理對自己的批評,講述從中得到的教益。
1999年12月,朱總理訪越,主要同越方討論兩國經(jīng)貿(mào)合作問題。關(guān)于這次訪問,要說的話很多,我只講其中一件事,就是主動提出要幫助兩家中援企業(yè)扭虧為盈。
20世紀(jì)60年代,中方曾在越南援建了兩家重點(diǎn)企業(yè)——太原鋼鐵廠和北江氮肥廠。由于年久失修、設(shè)備老化和管理不善,兩家企業(yè)到90年代都嚴(yán)重虧損,生產(chǎn)得越多,虧損也越多。雙方有關(guān)部門和企業(yè)雖多次商談改造計(jì)劃,但一直談不攏,搞得很不愉快。為此在朱總理訪越前,越方曾向中方打招呼,建議兩國總理會談時(shí)不要提及這兩個(gè)企業(yè)的改造問題,免得影響會談氣氛。但朱總理在同越南總理潘文凱會談時(shí),出乎意料地主動提及了這個(gè)問題。朱總理說,他將從國內(nèi)挑選有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專家到現(xiàn)場考察,通過加強(qiáng)管理和進(jìn)行必要的技術(shù)改造,盡快使兩家企業(yè)扭虧為盈,幫助越南政府“卸掉一個(gè)包袱”。越南總理潘文凱聽后十分高興,當(dāng)即表示感謝,但并不知道如何著手進(jìn)行這項(xiàng)工作。我和大使館的同志也沒有得到國內(nèi)的任何通報(bào)。
朱總理回國后第9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大使館接到了朱總理給潘文凱總理的親筆信。信中說:“為盡快落實(shí)我們在河內(nèi)達(dá)成的共識,中方?jīng)Q定派邯鄲鋼鐵廠和安陽化肥廠的專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協(xié)助越方進(jìn)行技術(shù)改造,改進(jìn)經(jīng)營管理,提高產(chǎn)品質(zhì)量和經(jīng)濟(jì)效益。為使上述工作順利展開,兩國相關(guān)部門及有關(guān)企業(yè)之間有必要互相溝通和了解。為此,我建議總理同志考慮能否派工業(yè)部長、鋼鐵工業(yè)總公司、化肥工業(yè)總公司負(fù)責(zé)人和兩個(gè)企業(yè)的黨委書記、廠長及少數(shù)專家,在中方專家赴越前來華訪問,參觀中方有關(guān)企業(yè)。屆時(shí)我將會見越南工業(yè)部長和中越雙方參加此項(xiàng)工作的人員。”
看到朱總理的邀請信,我極為興奮,想到朱總理動作如此迅速,我也必須抓緊落實(shí)。當(dāng)即便讓大使館經(jīng)商處聯(lián)系越南工業(yè)部,提出我要在當(dāng)天上午往見越南工業(yè)部部長鄧武諸。但對方回答說,大使要見部長,須先給工業(yè)部發(fā)照會。我聽后說了句“莫名其妙”,便親自給鄧武諸部長的秘書打電話,說我有急事要見部長。秘書說部長正在開會。我因同鄧部長關(guān)系很好,便說能否請部長出來說幾句話。不一會兒,鄧部長出來接了電話,約定上午11點(diǎn)半兩人在工業(yè)部見面。
鄧部長看了朱總理的邀請信,同樣興奮不已,表示將立即向潘文凱總理報(bào)告。但他說相信潘總理一定會接受邀請。下午剛上班,越南總理府辦公廳主任段孟蛟便打來電話說,潘文凱總理完全同意朱镕基總理的意見,將按時(shí)派鄧武諸部長率領(lǐng)考察團(tuán)前往北京。段孟蛟說,為了像朱總理那樣講求效率,打電話就算正式答復(fù),不再請大使去總理府了。
事后得知,鄧武諸部長一行抵達(dá)北京時(shí),朱總理已在人民大會堂等候,中方還特別安排了開道車引路。朱總理同越南同志和中方人員作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的談話,對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體的部署,客人們還去上海參觀了寶鋼等現(xiàn)代化大型企業(yè)。后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zhǔn),中方同意提供專款用于兩企業(yè)的技術(shù)改造。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計(jì)劃順利完成。鄧武諸部長對我說,他見過許多國家的總理,但態(tài)度如此誠懇,抓工作如此大刀闊斧、如此雷厲風(fēng)行的,可能只有朱镕基總理一人。
(責(zé)任編輯 謝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