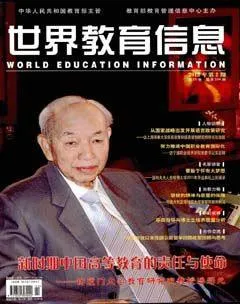從國家戰略出發開展語言政策研究
人物簡介:張治國,民進會員,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所所長,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美國馬里蘭大學訪問學者。目前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語言學(尤其是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詞匯學、語言比較教育學。2011年翻譯出版了《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以下簡稱《語言政策》)。
關鍵詞:國家戰略;語言政策;語言規劃
中圖分類號:H0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937(2012)02-0011-04
一、《語言政策》的翻譯及其意義
《世界教育信息》:張老師,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并恭喜您的譯著《語言政策》問世。請問當初您怎么會想到要把該書譯成中文?
張治國:想把這本書譯成中文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早在2006年,當我看完博納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的新作《語言政策》(英文版)時就覺得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一是非常有趣地介紹了語言政策,讓讀者感到語言政策就在我們身邊,打破了我們以前對語言政策的固定思維——語言政策是高高在上的政府行為;二是可以吸引和引導國內學界對語言政策的研究興趣,從而推進我國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的發展。另一方面,《2007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指南》指出:我國“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一直是語言學中的薄弱環節。”當我看到這句話時,馬上想起了《語言政策》這本書。了解和借鑒別人的研究成果是開展創新研究的前提,我想通過一個人的努力讓國內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太懂或不懂英語的人,以更快更徹底的方式了解此書,為此,我開始著手翻譯此書。
《世界教育信息》:在翻譯該書的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難?
張治國:在翻譯《語言政策》時,總體遇到三個比較大的挑戰。
第一是版權問題。一開始,我與該書的作者斯波斯基教授聯系,然后與劍橋大學出版社溝通,最終得到的答復是:出版社不與私人簽約,他們只能與我國的出版社商談。于是,我找了幾家出版社毛遂自薦,結果都吃了閉門羹。正在我一籌莫展之時,我的同事蔡永良教授把我引薦給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大明教授,正好該中心與國家語委和商務印書館有“語言規劃經典譯叢”的項目。經過他們對若干候選人的試譯評價,本人很榮幸地被選為《語言政策》一書的譯者,由商務印書館向劍橋大學出版社購買了該書的版權。
第二是翻譯本身的問題。我是從事英語教學和研究的,譯完該書的第一體會是:看懂一本書與翻譯一本書完全是兩回事。看書時,一些細節和難點一帶而過,而翻譯則不能,而且還要思考恰當的表達方式等很多問題。在翻譯完本書后,我想起了魯迅在《新的世故》中的一句話:“創作難,翻譯也不易。”某些時候,翻譯甚至還要難于創作,因為創作時作者可以“繞道而行”,把自己不熟悉的內容或表達方式避開。可是在翻譯時,譯者在內容和表達意思上都沒有選擇的空間,只能“人云亦云”。本人在兩種語言間的語碼轉換中尋找最佳的橋梁時常常遇到以下問題:對原文的理解、專業術語的翻譯、詞匯的空缺、長句的處理和語篇的銜接。
第三是多學科領域的知識理解問題。該書是專業書籍,術語多,使用了許多社會語言學和語言政策等方面的專業術語;內容涉及面廣,包含了政策學、語言學、教育學、歷史學、法律、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領域;書中使用的語種多,該書在論述某國的語言政策時,時常會出現一些用該國語言(如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拉丁語、漢語、希伯來語、挪威語等)表達的術語。對于這些術語的理解和翻譯問題,我主要采取了查資料和請教專家兩種方式。
《世界教育信息》:張老師,《語言政策》原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和譯者都是該領域的專家,該書的翻譯亦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資助。目前國內譯著不少,但獲得國家最高級別資助的卻鳳毛麟角,對這一情況您有什么看法?
張治國:我認為譯著能得到資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國家總體發展的原因。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教育、文化等領域進行國際接觸、國際合作的活動日益增多。在這些活動中,不管是“請進來”,還是“走出去”,語言都成為越來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國內通用語(包括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外語的教育、應用、管理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都關乎到國家的總體發展,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的對外交流與合作、信息安全、軟實力、民族關系、語言文化遺產的保護與保存等重要領域。語言問題不是光靠金錢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國家的長遠規劃和有效管理。國家一些相關部門,特別是國家語委和教育部語信司,已經認識到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待和管理語言,應該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來規劃和制定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語言政策。但科學的政策制定需要相關理論的支撐,因此,國家的繁榮和發展需要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
第二,學科單項發展的原因。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是應用語言學或社會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該學科目前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之一,盡管我國早在秦朝就有“書同文”的語言規劃行為,但語言規劃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研究起步較晚、發展較慢。前國家語委副主任陳章太在2005年指出:我國在該領域“對科學研究重視不夠,語言規劃理論基礎比較薄弱。”在中國語言學界,人們對語言的詞法、句法、語義、語用等單項技術的研究較多,而對語言的戰略研究還不夠。前者是語言的微觀研究,后者則屬于語言的宏觀研究。微觀研究涉及語言的發展細節,宏觀研究涉及語言的發展方向,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應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作為一個國家來說,缺少其中任何一種研究都是不完善的。因此,近年來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開始重視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研究和建設,可以說,語言戰略研究已開始在中國興起。引進國外經典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著作將有助于我國該領域的發展。
第三,作者、原著、譯者及譯著的原因。作者斯波斯基是以色列巴依蘭大學社會語言學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國家外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近年來,他在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關注。《語言政策》是一本語言政策導論書籍,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說,這是一本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的入門書和必讀書。作為譯者,我本人并沒有什么名氣,但我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具有英語專業的背景,系統學習過語言學和翻譯理論,并有一定的筆頭翻譯經驗,也有一些筆頭翻譯的成果;具有語言政策學習的經歷,在語言政策領域有一定的學術積累和研究經驗。譯著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利用腳注的形式對原著中出現的一些跨文化誤解進行了說明和更正;對書中可能引起讀者理解困難的語言名、地名、人名、術語等均添加了譯者注;書后附上了英漢對照術語表;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還就該書的內容進行了相關的延伸研究,并發表了文章。這些特點都為讀者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的推廣和發展。所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評審專家認為:“從譯著來看,質量上乘,頗有特色。”
二、《語言政策》作為學術譯著存在的必要性
《世界教育信息》:現在國內的英語教學比較普及,不少學者也有能力直接閱讀原著,您認為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去翻譯這種學術書籍有何必要性?
張治國:這個問題具有普遍性,也是我國目前許多人的困惑,因此我想借此機會多說兩句。時下,國內的確有不少翻譯書籍,有些質量低下,使得國人(特別是英語水平好的人)不愿看翻譯過來的書。我想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譯者英語不過關,曲解或誤解原著的地方多;二是譯者漢語不過關,表達不清,使譯作晦澀難懂;三是譯者不懂翻譯技巧,缺乏翻譯實踐;四是譯者對所譯書涉及的領域不熟,盡用外行話。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好的翻譯作品具有以下幾個功能。第一,翻譯有助于解決國人想了解外面世界而遇到的外語難題。如果根據英語水平來劃分中國人,我們可以粗略劃分出以下三類:英語水平非常高的人(所占比例少)、英語水平中等的人(所占比例介于前后兩類之間)和英語水平偏低甚至不懂英語的人(所占比例最大)。后兩類人需要借助翻譯,而第一類人(即英語水平高的人)可以不看譯著,但其中有一部分人還是愿意看譯著的,因為看譯著(好的譯著)可以比看原著理解得更透徹和更節省時間,畢竟絕大多數人的母語水平高于外語水平。雖然第一類人能看懂英語原著,但書本細節也未必記得牢(因為中國人的思維語言和思維方式都與西方人的不同),而且對一些難句的意思也不一定能吃透,對有些術語也未必把握得準,對一些長句和難句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時間去分析和琢磨,因為這樣會影響閱讀的流暢性。但是,譯著可以通過譯者的辛勤勞動而解決上述問題。如果說譯者的辛勤勞動能給廣大的讀者帶來方便和知識,那么這種翻譯是值得的和必要的。但為了提高和保持英語水平而看原著則另當別論。第二,翻譯有助于漢語的本體發展。全球化促進了語言接觸,但也加劇了弱勢語言借用強勢語言詞匯的趨勢。由于英語的滲透,漢語中的英語詞匯(尤其是英語字母詞)越來越多,長此以往,必將損害漢語的純潔性和本體發展。翻譯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方法之一,也是增強漢語的表達能力和擴大漢語影響的重要途徑。因此,各學科都應有相應的翻譯作品和術語翻譯委員會。第三,翻譯有助于中國思想文化的豐富。盡管不少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都學過英語,而且有些人英語的閱讀水平也不低,但“‘全民學外語’并不減弱翻譯對于國家的重要性。”這句話是教育部語信司司長李宇明在2010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的。不能寄希望“全民學外語”而忽略翻譯工作,應當充分發揮外語專才的作用,將世界上有價值的文獻及時翻譯成中文。只有翻譯工作跟得上,我們才能及時了解世界和豐富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另外,李司長在論文中還指出:“仔細想來,外國文獻只有經過翻譯,用本民族的語言表達它的概念、命題和思想推演,才能最終成為本民族的精神財富。”誠然,多少國外經典名句和作品都是以漢語的形式保留下來并廣為傳誦的。如英國詩人雪萊的名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可以說在我國是家喻戶曉,但有多少中國人最初是從英語原文獲知該名句的?即使現在,又有多少中國人能準確地說出該句的英文版本(“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呢?
三、斯波斯基對《語言政策》漢譯本的期望
《世界教育信息》:據了解,該書作者斯波斯基是以色列著名語言學家,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對此書的漢譯以及我國在語言政策研究方面的現狀是如何看待的?
張治國:斯波斯基是一個非常熱情、樂于助人的教授。他雖然年事已高,但還活躍在世界學術界,2009年他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專著《語言管理》,這本書可以視為《語言政策》的姊妹篇,2012年初他主編的《語言政策大全》一書即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各章的撰稿人都是世界各地語言政策領域的領軍人物。此外,他還時常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會議上做主旨發言。2008年,當我告訴他我將翻譯《語言政策》一書時,他非常高興,并欣然同意為譯本作序,正如他在該書中文版序中所說:“中國具有廣袤的領土和復雜的社會語言生態,這為中國語言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世界各地有關語言政策的正式研究都還相當年輕……研究社會語言學的中國學者已經關注到西方的這些發展潮流,但是他們只關注到其中的一部分,還有一些發展潮流尚未被關注到。”最后,斯波斯基以謙虛的態度表達了對我國語言政策研究的期望:“我希望《語言政策》一書的中文譯本也將是語言政策登高進程中一個有價值的臺階。中譯本可以把該書的思想展現給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家,以便他們能夠把該書的思想應用到中國復雜的語言實踐中去,并且通過與中國思維和中國學術研究的融合能夠對該書的思想加以完善并提出挑戰,我允許并鼓勵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家這樣做。科學知識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際合作的培養以及跨越學術門第之見和地理空間之隔而進行的自由的思想交流。我能參與這個過程感到非常榮幸”。
四、國內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的發展現狀
《世界教育信息》:我們拜讀過您關于中美語言教育政策的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近年來您在一些語言類和教育類核心期刊上也發表了一些學術文章;您現在還擔任上海海事大學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請問您的研究興趣是如何轉向語言政策研究的?
張治國:謝謝你們對我的關注。如果說我在這些年取得了一些成績,那是因為我在研究的道路上一直有高人指點和貴人相助。首先,我要借此機會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周南照教授,是他引導我走向了語言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其次,我要感謝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毛立群教授,他對我申請和籌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所給予了大力支持,使得我可以在一個較好的平臺上發展:組建研究團隊,共享研究資料,互通研究信息。所以,博士畢業后,我就與團隊成員一直從事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方面的研究,關注國內外在該領域的研究動態,并結合我國的現實需求進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
《世界教育信息》:張老師,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在國內的發展現狀如何?您能否就此談談個人的看法?
張治國:這個問題很大,也很難回答。就我個人而言,有以下幾點看法。
首先,談談國內的研究現狀。語言戰略,在學術上應該稱作“語言政策”或“語言規劃”或“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其研究開始在我國興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相關研究機構的成立。近年有關語言戰略研究的機構紛紛成立,比如2000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了外語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語信司分別與暨南大學于2005年共同建立了海外華語研究中心、與南京大學于2007年共同成立了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與上海外國語大學于2007年共同成立了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2010年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成立了語言文字應用研究中心。它們的相關出版物分別是《世界語言戰略資訊》月刊、《全球華語研究》、《中國語言規劃》、《外語戰略動態》季刊和于2010年開始試刊的《語言政策研究》。此外,寧夏大學外國語學院成立了語言規劃與政策研究所,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成立了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所。二是相關學術會議的召開。近年來有關語言戰略的學術會議逐漸增多,如2006年由教育部語信司主辦、渤海大學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承辦的“語言國情與語言政策高級專家研討會”,2009年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的“中國外語戰略與外語教學改革高層論壇”,2010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主辦、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協辦的“2010年中國外語戰略論壇”,2010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育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外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高層論壇”,2010年中國社會語言學協會主辦的“第七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其中包含語言政策分議題),2010年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三是相關研究成果的發表。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陸續以譯著、專著或論文的形式發表。如國家語委和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共同倡議和組織了“語言規劃經典譯叢”項目,周慶生主編的《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等等。
接下來,對國內研究現狀談談我個人的兩點看法。第一,學科發展還比較滯后。由于我國不少人不太了解這個學科的內容和重要性,誤認為語言政策是國家領導和政府部門的事,學界用不著去研究,就算研究了也不可能被采納。這種成見導致學科課程的開設、人員的配備、課題的申報和論文的發表等方面的發展都受到了抑制。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國家的一些相關部門,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教育部語信司和語用司,已經關注這一領域,國內的一些語言類和教育類核心雜志近年來也開始刊登一些有關該領域的研究論文,這極大地鼓舞著該領域的研究人員。第二,國內缺乏金字塔形的研究隊伍。跨學科研究是現代科學發展的重要趨勢,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學科就屬于一門跨語言學、社會學、教育學、政策學、歷史學等的綜合學科。目前,我國還比較缺乏該領域的大師級領軍人物,這與我國的大國形象極不相符,而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在該領域都有自己的“達人”,如美國的費什曼(J. Fishman)、弗格森(C. Ferguson)、庫帕(R. Cooper),挪威裔學者豪根(E. Haugen)、開普蘭(R. Kaplan)、馬福威(S. Mufwene)和霍恩博格(N. Hornberger),以色列的斯波斯基和肖哈米(E. Shohamy),荷蘭的德斯萬(A. De Swaan)和布羅馬特(J. Blommaert),澳大利亞的樓必安可(J. Lo Bianco)和巴爾道夫(R. Baldauf),英國的艾哲(D. Ager)、萊特(S. Wright)和克里斯托(D. Crystal),丹麥的菲利普森(R. Phillipson),芬蘭的斯古納伯-康格斯(T. Skutnabb-Kangas),德國的克洛斯(H. Kloss)和哈爾曼(H. Haarmann),加拿大的里森特(T. Ricento)、托爾夫森(J. Tollefson)和科森(D. Corson),法國的加奇(A. Judge),新西蘭的梅(S. May),新加坡的黃(L. Wee),等等。此外,目前我國該領域的研究隊伍還很小,大師的出現需要以學科發展和眾多參與者為基礎。因此,營造良好的學科發展環境是大師的出現與研究隊伍壯大的必備前提。
編輯: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