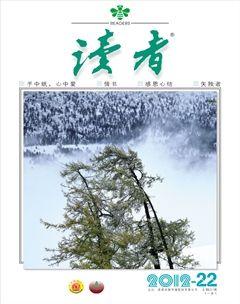三世情話
朱桂華

拒聽情話的耳朵與旋風式的甜嘴
1963年,臺灣,春天的傍晚。
三十八歲的聶華苓走進美國新聞處大院,她一身素裝,眉宇間夾著哀怨與愁悶。過去的幾十年,她一直是孤苓一朵,生于武漢,流離于重慶,又漂泊到臺灣。大院里正舉行一場雞尾酒會,舉杯交談的多是詩人、作家。現場十分喧鬧,身材嬌小的聶華苓被熱浪裹挾著飄落在椅上,任斑駁的燈光將秀氣的臉龐勾勒出幾分蒼涼。
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越過人群,將深邃的目光投到她臉上。他叫保羅·安格爾,美國著名現代派詩人,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負責人。該工作坊主持美國第一個以寫作獲學位的項目,為此,他正在世界范圍內搜羅和邀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免費赴愛荷華學習和創作,臺灣是其中一站。
來臺灣之前,他讀過她的作品,還試著翻譯那些意象稠密的文字。他想過去跟她說話,但是幾次被人打斷。酒會接近尾聲時,聶華苓被人拉到了保羅跟前,他便急切地說:“你就是《翡翠貓》的作者?為什么不跟我說話?”她畢業于金陵大學外文系,英語流暢,回答冷而尖銳:“你是主人,你也沒跟我說話。”他以關切回報冰冷:“你應該到愛荷華去!”她故意冷若冰霜:“我不可能去!”
那時候,聶華苓的處境非常糟糕,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剛剛病歿,丈夫六年不曾回家,她獨自撫養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當時最讓她苦惱的是,她參與編輯的《自由中國》,因為刊登了觸犯當局的內容而被查封,她整天被特務監控。她太需要抽離這險惡的環境,然而她丟不下女兒,當局也不會允許她出境。
冰冷的語言,最能制造距離。然而,保羅微笑著說:“我要說服你去!”次日,他約她單獨吃飯,送她回家。他談她的作品,對她的《翡翠貓》《葛藤》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你跟我想象中的一樣,頭腦性感,身子聰明!”
這話像箭一樣,穿透她的頭腦和身子,留下被命中的痛楚與暢快。她就是這樣的,為文字癡狂,在文字里性感。小說《葛藤》寫的就是知識分子婚外戀的悲劇。但在現實中,她認為人與生俱來要被命運的葛藤纏繞,她要尋找正確解開束縛的方法。
他送她到樓下,再也不掩飾對她的一見鐘情,說:“你不能回家,我們應該繼續走,繼續談心!”他力邀她去愛荷華:“我一天都不能忍受見不到你,你先跟我去日本,之后到新加坡、菲律賓,然后我們一起回美國!”雖然心動,但聶華苓還是清醒的:“我是母親,還有丈夫,你是父親,還有妻子,怎么可以放肆地說這些?”保羅回答:“是你讓我意識到生命不完整,我覺得自己也能填補你的不完整,我們應該大膽地相愛!”
他情真意切,可她是一個有著強烈中國性格的女人——隱忍,因此火辣辣的情話讓她不太受用。盡管1964年出于對文學夢想的追逐,以及擺脫險惡形勢的需要,她接受保羅的幫助,成功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1965年,她跟分居七年的丈夫離婚,但她與保羅的關系,仍然發乎情,止乎禮。
造化弄人,保羅偏是一個有著強烈美國性格的男人——不虛偽,敢說也敢做,她愈理性他愛得愈烈。保羅的妻子瑪麗患有精神病,跟保羅結婚時,瑪麗隱瞞了精神病史,這使得保羅整整三十年生活在不和諧的婚姻中。為給愛爭取希望,他頂著法律和輿論的壓力,開始了艱苦的離婚戰。
于萬千變化中說不變的情話
聶華苓獲得在愛荷華大學執教的工作。1965年,她創造性地提出“國際寫作計劃”,該計劃單純地給青年作家創造良好的寫作環境,沒有學位束縛。被納入計劃的人,可以前往愛荷華生活四個月至兩年。這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也面臨瑣碎的管理事務,這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對此,保羅一直樂觀地給予支持。他會在滂沱的雨夜去接聶華苓下班,告訴她他們的未來,告訴她醞釀中的國際寫作計劃會迎來金燦燦的太陽。面對面,年近六旬的保羅,聲音和眼神中滿是對她的依戀和尋覓。
1966年,保羅前往歐洲列國搜集優秀的短篇小說,他每天說不同的語言,談不同的話題,住不同的旅館,勞累困頓,卻堅持每天給她寫信。在巴黎,他說:“我在飛機上只睡了兩個小時,非常疲倦,看到你的信,立刻來了勁……這座城市十分迷人,到處都有可愛的小景,可沒有你,一切都顯得蕭瑟冷清!”在圣路易,他說:“古老的屋子美極了,圣母院就在那兒……每當我看到美好的事物卻不能跟你分享時,就更想你,比如看到圣母院夜里飄蕩的燈,在墻上、窗上撩出柔和的幻影,就分外地想你。我想回來在山上建一座活動的小屋,你可以來看我,我們一起吃晚餐!”在布列塔尼,他說:“每天回到房中,非常想你,每次想你,都感到貼膚的溫暖,好像跟你在一起……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旅行、不同的人,我可以獨自應付,但在這么美、這么蠻荒的島上,多么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此刻,再見你仿佛永生永世那么渺茫,最快活的日子,將是我啟程回家的那一天!”他看到路邊早開的桃花,會摘下一兩朵,寄給她;看到巴黎大街上時髦的衣服和帽子,也會毫不猶豫地買下來,寄給她。他囑咐聶華苓接待他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朋友,也囑咐這些朋友,給他心上的女人帶去快樂:“我保證讓她給你喝最好的酒,但拜托你多逗她笑,她的笑聲很好聽。”
保羅于1941年接管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即使在戰亂的年代里,他也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尋找有文學才華的年輕人。二十余年來,從作家坊走出多位普利策獎獲得者、國家詩人、文學院士。1965年,因為貢獻卓越,他被約翰遜總統任命為第一屆國家文學藝術委員會委員以及華盛頓肯尼迪中心顧問。
聶華苓后來才知道,20世紀60年代初,當她在臺北一邊發表文字,一邊遭遇政治和家庭的雙重困境時,遠在愛荷華的保羅就開始關注她了。他聞出了她的才華,尋蹤來到臺北,本只打算幫助她,卻在見面那一刻真摯地愛上了她。在保羅的家里,有他寫給她滿懷敬意的詩——《致聶華苓》:“你教我從水中取木,你把一切神奇的愛的真相指點給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你把中國的心指給了我。”
原來,他愛她被長江和黃河澆灌過的靈魂,愛她的內斂與豐潤,愛她身上強烈的中國性格。他是在意識到她巨大的吸引力時才意識到自我的殘缺的,他因為年少的輕率付出三十年的光陰,因為與她相見恨晚,才更懂得矢志追求她。保羅是一條激情寬闊的河流,她逆流而上,去了解他坎坷而充滿溫情的成長經歷,仿佛自己經歷了一場精神旅行,她感覺真正地被滋潤了。
她穿上他寄回來的新衣,給他回信:“苓,是一種菌類植物,只尋松寄生。從大陸到臺灣到美國,我以為自己活了三世,前世飄零,二世危迫,三世,終于找到命里的那棵松!”
1971年,保羅離婚后,她送給他一把用絲絨布包裹的家門鑰匙,意寓他們真正打開了情感上的禁錮,可以自由交往。
鹿園回響三世的情話
結婚時,她四十六歲,他六十三歲。他們在愛荷華河邊的山坡上筑起了自己的家,那是一棟木質結構的赭紅色樓房,樓房周邊是蒼翠的森林,保羅在森林里喂養了許多只鹿。孩子們已經成人,鹿園成了他們兩人的伊甸園。
他們的一天常常這樣開始:聶華苓賴在床上胡思亂想,保羅端進來暖暖的咖啡,說他正在構思一首長詩,問她要不要聽聽。她聽完后說:“好極了!寫!寫!”保羅的眼里倏然就閃出淚花,說:“別人不懂的,你懂!你和我是這般默契。”
漫長的白日時光里,也不沉悶。他們各有各的書房,一個在樓上,一個在樓下,但都對著愛荷華河。河邊,保羅為聶華苓種上了楊柳樹,為的是讓她能在愛荷華看到中國的江南。他在樓上打字,突然停下來,喊道:“華苓!”聽到她答復后,打字機又響起來了。有時他不喊,而是走下樓,將手搭到她肩上,說:“我只想知道,你在這兒。”
保羅在上班,聶華苓打電話過去。保羅用中國話說:“喂!”她問:“你怎么知道是我?”他回答:“你的鈴聲里透著溫柔!”保羅肚子疼,醫生問他有沒有過痙攣史,他回答:“有過,就是在遇到華苓的那一刻!”保羅和聶華苓參加朋友聚會,他不斷伸長脖子找她,他對朋友說:“我的脖子上有一顆定時炸彈,見不到華苓就會爆炸!”他和她坐在靠河的長窗前聊天,聶華苓說:“快看,一只紅鳥飛上了橡樹!看那邊,那只鹿走出樹林的姿態像嫻雅高貴的公主!”保羅不看鹿也不看鳥,看她的側臉,說:“我真喜歡我們的生活。”
他帶給她的愛,像孩子一樣熱烈純真,沒有絲毫的暮年氣息。而聶華苓依然是中國的聶華苓,她堅持用漢語寫作。保羅說情話時,她會微笑和臉紅。她不那么主動示愛,卻把他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給保羅留言:“以前我認為相愛很難,對人有刻骨的感情更難,如今我深深地知道,真正的愛情,就是兩份孤獨,相護,相撫,喜相逢。”
1990年的除夕夜,鹿園冰雕玉琢,紅樓里一爐紅火。保羅為聶華苓斟了酒,說:“華苓,祝我們倆健康快活!我要再重復一遍——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沒有多少人有我這樣的生活。我還要重復一遍——你的腦子很性感,身子很聰明!”六十六歲的聶華苓笑得像一朵怒放的花——她老了,他還是把她當寶,這種日子,可真過不夠!
遺憾的是,這是兩人相處的最后一個除夕。1991年3月22日,他們啟程前往歐洲,打算去見作者,去領波蘭政府頒給他們的文學獎,去接受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接見。在芝加哥機場,保羅突然發現拿在手里的愛爾蘭鴨嘴帽不見了,那是聶華苓送給他的圣誕禮物。他十分焦急,來來回回地找,直罵自己笨蛋!他找到了,立刻轉悲為喜,心情還沒平復下來,他說:“我去買份《新聞周刊》。”他轉身走向轉角的小店,卻再也沒走回來。聶華苓找到他時,他躺倒在書報攤前的地上,沒了知覺。
聶華苓失去了保羅,起初還沒覺得天塌地陷,她以為自己做好了失去他的準備。然而,當她獨自回到愛荷華,在山腳下想起無數次跟保羅回家,保羅遠遠地望著紅樓說“我真喜歡我們的家”時,巨大的痛楚開始襲來。她走進家門,看到他養的鹿上前來迎接,種的蔦蘿在風里搖曳;她走進屋子里,看到他親手為她做的黃色書桌,上面放著他的詩集《中國印象》,其中有一首是《想到我會死在中國》,他動情地寫道:“在那迷茫和苦惱的時刻,我想,中國啊,您把美麗的妻子給了我,我在暮年,只好把可憐的骨頭給你!”在《中國》這首詩中,他這樣歡天喜地地描寫1980年的中國:“現在生命飛過中國像一只鶴,現在生命像雨水向中國灑落,現在生命像金黃的麥穗在中國生長,現在生命洋溢在中國城市的街道上,現在生命向中國滔滔流去,又響又急,現在生命就是中國,死亡都成為過去。”
愛一個女人,并將對她的愛擴大到愛她的國家和民族,這是一種怎樣深沉的情感啊!她跟他相處一世,他的愛照亮了她的三世,也照亮了她身后魂牽夢繞的故土。
他晚年一直致力于國際寫作計劃,繼1979年邀請蕭乾訪美后,1980年是艾青,1981年是丁玲,1982年是王蒙,1983年后是王安憶、茹志鵑、陳白塵,汪曾祺、余光中、馮驥才、北島、蘇童、劉恒、李銳、遲子建等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都從該計劃里獲益良多。
12年后,聶華苓走出悲痛,寫就傳記《三生三世》,隔著時空回憶保羅。2012年5月,聶華苓被南京大學評為“十大杰出校友”之一,入選理由是:她是國際寫作計劃創始人,是“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筑師”,是“世界文學組織之母”。聶華苓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運地遇到保羅,得以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