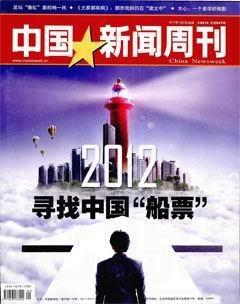木心:一個美學的倒影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無雙草草逸筆猶嘆壯志未酬。”這是木心最后歲月的自我詮釋
“你曉得嗎,(29年來)你跟我講過多少笑話?”陳丹青問木心。
木心卻回道:“文學在于玩笑,文學在于胡鬧。”躺在病床上的木心喘了一口氣,又緩緩地說:“文學,在于悲傷。”
2011年11月中旬,木心住進了浙江省桐鄉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部12樓的VIP病區。肺部感染,身體每況愈下。神智清醒時,他不忘開玩笑,畫家陳丹青的夫人黃素寧問木心:“你還想吃什么?”木心思索了一會,用上海話說,“我想吃魚翅。”陳丹青覺得,“生病期間的先生就像一個小孩。”
12月初,木心病情加重,又轉移至2樓的重癥觀察室。21日凌晨3點,詩人、畫家、作家木心離世,享年84歲。當天下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貝貝特公司發布了訃告和治喪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在微博上迅速引起十幾萬條的熱議。很少有人再問“木心是誰”,更多的人知道這個“文學魯濱遜”落葉歸根,在故鄉烏鎮安享了晚年。
這一天,陳丹青在木心的手稿中翻到一副對仗工整的遺聯:“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無雙草草逸筆猶嘆壯志未酬。”這是木心最后歲月的自我詮釋。“一舉一動都有英國紳士的風度”
就在木心住院期間,陳丹青在一個上海朋友那里翻到一張民國時木心和友人的合照。那時木心大概19歲。陳丹青將病床搖起來,木心靠在床上,拿起照片,認了半天才認出照片中的帥小伙是自己,“神奇得很吶!”
陳丹青問:“你怎么這樣不在乎你的照片,隨便把它就送給人呢?”那時,木心的精神已經半糊涂、半清醒,他自語:“國破家亡,幾張照片算什么!”
“這就是民國人的情懷。”陳丹青說。在他眼里,木心是—個延續民國風范的文人。
1982年,陳丹青和木心不約而同地從上海奔赴紐約。在地鐵上,陳丹青和木心第一次見面,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是一個上海籍的年輕畫家介紹認識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只簡單地問知他是搞工藝美術的。過了小半年,我非常驚訝地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文章,便馬上打電話約見,一見面就談到第二天凌晨。”從此,兩人成為師友。日后,陳丹青在很多場合都稱木心為“師尊”。
1989年至1995年期間,木心在紐約家中給一群文學青年、畫家講授《世界文學史》,其文學作品也被美國文史課程的教材收錄為范本讀物,木心這個名字被海外華人作家所熟知,而他的畫作在1990年代末也開始在全美陸續展出,成為上世紀第一位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作品的中國畫家。
據陳丹青回憶,木心的記憶力過人,講課時雖作講義,但全憑早期的文學記憶。有時,他的課從晚上一直講到第二天天亮,學生們趴在桌子上已東倒西歪,木心仍目光如炬。陳丹青回憶說,“他所講全是靈感。”
木心少年時期即熟讀《詩經》《圣經》以及莎士比亞、尼采等人的著作,而他鄉紳家庭中也有在英美留學的親人,使木心得以接觸到西方文化。“人們已經不知道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南方的富貴之家幾乎全盤西化過。”木心曾這樣回憶。
見過木心的人都回憶,木心外出或在家里待客都會打扮得一絲不茍,一身西服,腳踏锃亮的皮鞋,一身正裝地說玩笑話。在一幀幀照片中,他的派頭頗像美國硬漢明星。
2010年11月,歷任臺灣《聯合文學》和印刻出版總編輯的初安民來到烏鎮,“從他進房間、打開自己的畫、戴帽子、送東西,每個動作都是緩慢的,但每個細節他都很注意。”初安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木心精神很好,老了動作開始變得緩慢,但一舉一動都有英國紳士的風度。”當時木心還表示希望來年去一趟臺灣,辦個畫展。或許這即是遺聯中的一個“壯志未酬”。
這樣一個美男子,卻未有婚姻也未留下子嗣,這成為木心生命中的一個謎團。在住院期間,木心說:“我一個老光棍從來沒有女人。”陳丹青說,“現在給你辦一個老婆,你要誰?”木心說:“我想一想,嗯,瑪麗蓮·夢露。”
有讀者曾在網上議論木心是同性戀,其作品中也有描寫男子間同居的故事。木心作品在大陸的責編曹凌志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木心的作品亦虛亦實,“從文字里能感覺到他對世界的態度,但不一定能看到他自身歷史的細節,不能對應入座。”
2011年10月,曹凌志來到烏鎮和木心商討文集事宜,“當時他就感覺到木心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需要扶著上樓。聊完出文集的事,木心腳步突然變得輕快。”這或是應了遺聯中的另一句“私愿已了”。“沒想到這一生我還能回來”
有一件東西是始終陪伴著他的,那就是香煙。2011年12月24日上午,在桐鄉市殯儀館,火化遺體前,陳丹青深知木心生前所愛,塞了一包煙在木心手中。
下午,追思會在烏鎮的昭明書合舉行,由兩位美國獨立導演所拍紀錄片《木心》的片花在會上放映。木心坐在木船上,徜徉在烏鎮的溪流間。他曾表示:自己的精神故鄉在古希臘,為追求藝術的自由去了紐約。
木心本名孫璞,1927年2月14日出生于桐鄉鳥鎮東柵財神灣一家富庶家族。1946年,他就讀于劉海粟刨立的上海美專學習油畫。20歲出頭時,因為領導學生運動,木心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又被國民黨通緝,避走臺灣。直到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前不久,才回到大陸。
在194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木心任職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1971年因言獲罪,被關進廢棄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后開始勞動改造,20本手稿也全部遺失。出獄后的第一件事卻是因為高超的工藝美術技藝被調往北京,負責修繕人民大會堂。之后,木心任上海工藝美術家協會秘書長。1982年,55歲的木心自費前往美國。之后的一段時間,他默默著述、繪畫,作品逐漸被異國接納。但于故鄉,木心的名字卻從此少人知曉。
事實上,上世紀末木心曾孤身一人從紐約回了趟烏鎮。面對鄉音與舊景,他備感親切,然而到了東柵財神灣的祖宅時,庭院敗落、污穢,他寫道,“這樣的凄紅慘綠是地獄的色相,棘目的罪孽感”。1998年11月,木心在臺灣《中國時報》發表《烏鎮》回憶這段經歷,并寫下“永別了,我不會再來”。
世紀之交,烏鎮著手開發旅游,曾任烏鎮黨委書記的陳向宏擔任旅游開發公司總裁。2000年冬天他剛好翻到那張臺灣舊報,讀到了《烏鎮》一文,至今他還記得木心那篇文章透露出來的失望。
陳向宏下定決心尋找木心,并著手修復木心的故居孫家花園。那一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在浙江烏鎮頒獎,王安憶的《長恨歌》便是獲獎作品之一。陳向宏向王安憶打聽,“你知不知道木心這個人?”王安憶說,“我的朋友陳丹青知道”,并把后者的聯系方式給了陳向宏。由此,在陳丹青的協調下,陳向宏與木心開始了長達5年的溝通。
2005年4月,木心在陳丹青的陪同下,再次回到烏鎮,和陳向宏當面溝通。彼時,
整個烏鎮也被修復。次年9月8日,在陳丹青的全程“押送”下,木心從紐約飛赴北京,然后轉機上海。
飛至上海時已是深夜,歸鄉心切的木心對飛機的速度很不滿,尤其是降落時飛機緩慢地傾斜。“真隉啊!蒼蠅—停就停下來了,看飛機的降落,簡直讓蒼蠅笑煞。”木心對陳丹青說。9月11日下午,木心終于抵達了烏鎮,“沒想到這一生我還能回來。”
歸鄉之后,烏鎮旅游公司挑選了精干的廚師、保潔阿姨以及兩個青年員工照顧木心的起居,其中侍護青年代威利用晚上的閑暇時間學會了水彩畫。
這一年,大陸讀者才開始逐漸知曉木心。陳丹青牽線自己作品的“東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木心作品《哥倫比亞的倒影》出版,首周即登陸三聯書店暢銷榜。之后—年,木心數部作品陸續出版。
這其中少不了陳丹青的推動,他甚至說,愿意用后半生的精力來推薦自己的老師木心。除他之外,文學教授陳子善、作家陳村、阿城等人也紛紛激賞木心的為人與作品。
陳丹青當時評價木心是“我們時代唯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寫作者”,同時也有人認為陳丹青借高調推銷木心炒作自己。《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在博客上和陳丹青展開論戰。朱偉認為,推崇陳丹青的讀者有很多是看重他批判體制的態度,而這些“憤青”并不會欣賞木心的文字。他覺得,陳丹青的這種借力推銷方式是失效的。“木心的文字與見解,對這些(憤青)讀者恰恰沒有意義”。朱偉寫道。
關于外界的評論,木心并非充耳不聞,他的外甥王韋也曾將報刊上的各方評論都收集起來寄給木心。在追思會上,王韋回憶,“他也沒有想到作品在大陸出版后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映。”王韋認為,木心是很自負的。木心曾對王韋說:“宗教像云,是淡淡的;而藝術是霞,五彩繽紛。”
“把讀者看得很高”
2011年12月23日下午,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和作家陳村趕到了烏鎮木心故居,來參加次日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思會。
木心的故居孫家花園,總面積近3000平方米,他自己命名為“晚睛小筑”,一片花園包圍著一幢兩層的古屋。在二樓的靈堂,擺放著木心的書和照片,房間里循環播放著他生前最愛的莫扎特、巴赫、貝多芬的古典音樂。外界都熟知木心寫作、繪畫,并精通中西方哲學,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也譜曲。陳丹青回憶,在紐約時,木心提及文革期間獄中沒有音樂的日子,“他用白紙畫了鋼琴的琴鍵,無聲彈奏莫扎特與巴赫。”
陳子善和陳村拿出手機在孫家花園拍照,并發布微博悼念。陳子善是大陸地區最早讀到木心作品的人,1984年11月他就在臺灣《聯合文學》創刊專輯上看到了木心的文章。陳子善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的文字很特別,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從內地出去的。”此后木心的詩文集在臺灣出版,陳子善托人將能收集到的木心作品全寄到上海。2001年,他在《上海文學》主持一個關于老上海的專欄,發表了木心的《上海賦》。作家陳村看到后稱“如遭雷擊”,他把這段“驚為天人”的文字敲到網上小范圍內流傳。2007年3月,陳村曾專門到烏鎮探訪過木心,后者給他的印象是談笑風生。
木心回國后,大陸的讀者逐漸熟知了這位流浪歸來的文人,各地的讀者紛至沓來。《無錫日報》文教專刊部主任孫昕晨曾見過木心一次。2007年11月5日,孫昕晨本是到烏鎮游玩,作為詩人同時也是木心的讀者,他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木心已歸鄉,倒可以去東柵探望一番。
孫昕晨向門衛表明自己的記者身份,未料吃了閉門羹。孫昕晨馬上改口說自己是讀者,才得以進入花園。那天,天氣陰沉,室內的光線更顯昏暗,孫聽晨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木心當時穿著一個毛衣從樓上下來,不像是午睡中醒來,而是從寫作中走出來。”
木心和孫昕晨便談起魯迅。木心對孫昕晨說,“在我心目中最優秀的作家應該是文體家,魯迅就是個文體家。”
孫昕晨認為:“木心把讀者看得很高,作品是獻給少數人的,但這少數人是無限的。”孫昕晨和木心單獨聊了近一個小時,后來他有些慶幸,‘因為據他了解木心很少接待外人尤其記者。
更多的人總是徘徊于“見與不敢見”的矛盾中。陳子善曾多次到烏鎮,都想去拜訪木心,但又怕打擾后者,第一次見面卻是在木心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在12月24日下午的追思會上,生前照顧并陪伴木心度過最后歲月的青島青年劉正偉也是一個靦腆的讀者。
2007年陳丹青到青島簽售《退步集續編》時問劉正偉,“你想不想跟我去烏鎮(見木心)?”劉正偉很激動,又覺得“天方夜譚”,當時竟沒有答應。2009年12月,劉正偉辭掉了在青島的工作,毅然到烏鎮,并在當地找了一份工作長期駐扎。此后1年零8個月的時間,每逢周末劉正偉都會到孫家花園徘徊,他稱之為“像狗一樣在那周圍轉來轉去”。直到2011年8月末,木心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劉正偉終于鼓起勇氣見木心,更幸運的是“先生特別喜歡我”。陳丹青感慨地說:“木心也曾說過自己像狗一樣,圍著《詩經》轉。”
2012年,木心的一些畫集將會出版,他的美術館也在興建。木心的骨灰將下葬在故居的花園里,碑文僅“木心”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