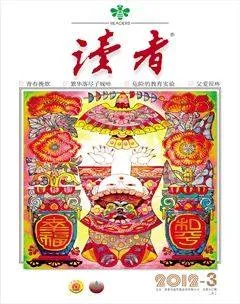不見之親
老愚

當同學們數張臉孔湊到一起相互打量時,我恍惚間像回到高家學校的那間教室。數學老師正在黑板上板書一個數學公式:﹙a+b﹚2=a2+b2+2ab。我端詳著這些精靈似的字母,它們之間的變化令我驚奇。它們不容置疑地擺成那種陣容,讓人遐思也讓人困惑。當時我腦袋里想的是:如果父親是a,母親是b,他們會生出多少孩子?
教室外面,太陽一不小心就被老槐樹架在樹杈上動彈不得,把銹紅的腮幫子丟給我們。圍墻外傳來一聲懶洋洋的牛叫,我能想象得出它拖著犁鏵的模樣,頭耷拉著,假裝恭順地往前挪動,不時翻動的眼睛里隱含一抹哀愁。這是世界上最讓人不能正視的哀愁,它一定在沉思:日復一日的耕作到底是為了什么?
妹妹弟弟們沒有征兆地相繼來到人世,當母親把他們塞過來時,我并不樂意接。他們是誰?為何來到我們家?我還不能想清楚和他們的關系。我是愿意做弟弟的,幾里外王上村有好看的干姐干哥,我跟他們好像天生是一家人,我不想有人分享他們。一旦把妹妹弟弟們抱在懷里,情況就不由自主地變了。他們散發出一股熟悉的氣息,那是出自一個母親的氣息,在人世間連接起孤獨的生命。
一口鍋里吃飯,一方熱炕上睡覺,聲息相聞,也喜歡也怨恨。不經意間,各自長大了,幾歲十幾歲的年齡差,逐漸露出了利爪。陌生感與日俱增,我感覺到各自有了可怕的秘密,相互間也好像滋生了某種戒備。在農家有限的資源里,誰能多分一杯羹,誰就可能有不一樣的命運。做父母的還要考慮養老,會把一個男孩留下來,娶妻生子,他的求學生涯便在初中或高中結束……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睡,也沒誰大聲說話,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驚濤駭浪。多年后,妹妹時常抱怨沒供她上大學,耽誤了前程;二弟有時淡淡念叨一句:“如果讓我上高中,也許能上大學呢。”父母唯有一笑,岔開話頭。此時,我隱隱有負疚感,好像自己耽誤了同胞們的人生。
唯一認命的是小弟弟。他從小喜歡擺弄機械,厭惡讀書,我后來為他找了一份開車的差事。他豪爽,愛幫人,深得老板喜愛,自此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親人的見面以年為單位,有的甚至幾年難得一見。見面時,話其實也不多,總有許多敏感區域不敢涉足,怕傷了別人的心。命運寫在每個人的臉上和身體上,走路的姿態,說話的語態,臉上的表情,眼里的神情,生活已經雕刻了一切。那是你的親人,但都擁有自己的命運,你無法改變他們的軌跡,你甚至也不知曉他們的人生。坐在一起,你們就是親人。打牌、抽煙、喝酒,在這些動作里,一家人和悅地坐在一起,時光仿佛又回到了從前。親情在空氣里流淌,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但不會有人說出來。詩人,這個時候一定站在門外,吟誦著贊美親情的詩篇。
生活不如意的,不愿意讓弟兄們看見自己窘迫的神色,他們會選擇一個平常的日子回家看父母一眼,說幾句話,掏一小包禮物,把薄薄的信封塞到父母手里;過得還順心的,愿意在每個節日回家,呈上一大堆包裝精美的東西,呈上鼓鼓的紙袋子。
暮色四合,又一個夜晚降臨,幼年時的情景一一浮現:我們為一盤裹面蒸出來的紅薯秧子而雀躍。糊湯、饃,還有母親巧手蒸的這盤菜,夜晚一下子變得美滋滋了。我們幾個睡在廚房的炕上,我說睡,一口氣吹滅煤油燈,眨眼間,就都沉入夢鄉。有時柴火旺,炕熱得人躺不住,我們便坐在被褥上,等炕稍冷一點再鉆進被窩。也不知道說了些什么,也許什么都沒說。外面黑嚴實了,煤油燈撲閃,昏暗的屋里彌漫著剩菜的氣味,老鼠在灶間磨牙,發出窸窣的聲響,院子里幾只不老實的雞大鬧一番,就又安靜了。
夜黑透了,我曾在這樣的時刻坐在田野里,讓濃濃的黑裹緊自己。那是一個安詳的世界,我和自己說著話,感覺會有無數的明天等著自己,我會在一個個這樣的日子里長大。
親人們,今夜可好?
(孫秦摘自《新周刊》2011年第22期,李小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