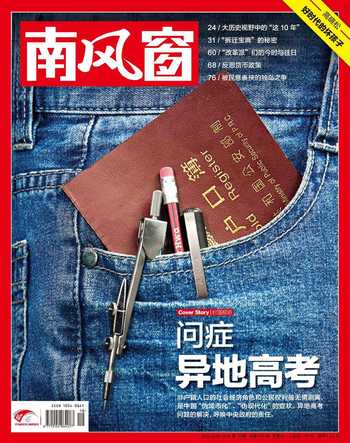政治宗教中的人
寒漠
“一般來說,政治處理的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事情。與之相比,偉大的宗教則通常聲稱它們有權利統治全部生活。”彼特沃克在《彎曲的脊梁》一書中,繼續將無所不包的極權主義運動置于宗教視域中考察,他所提醒的是這樣一種反觀:極權政治與宗教的競爭,可能是源于政治在群體性精神渴求與權力結構中的宗教變體身份。
當我們發現亟缺科學常識的人同樣可以聲稱“相信科學”,“科學”的內涵便已經異化,成為一種信仰。這種信仰與納粹德國“元首永遠正確”的信念卻別無二致,它們都堅信這世上存在絕對正確、無所不能和亙古不變的東西—那就是他們現在所信奉的“科學”或者“希特勒”,而其間出現的“小錯誤”只是具體方式上的瑕疵。考慮到納粹德國和宣傳“科學信仰”的民主德國之間的先后關系,書中指出了這兩種看似迥異的信仰間隱秘的承接關系。
極權政治似乎在人類心靈的宗教獨霸時代到近代科學理性的過渡之間,辟出了一條“政治宗教”的道路,充分滿足了人們對世俗生活秩序與神圣精神追求的雙重渴望,《彎曲的脊梁》則用可索引的詳盡資料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使用宣傳手段所完成的部分,但書中最值得玩味的卻是政治宗教中人們的反應。
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只存在一條統一的評價標準,那便是“是否有切實的成就”—可以將其理解為“政績型合法性”。再強大的宣傳也敵不過人們對“看得見的好處”的固執,于是宣傳影響力的消退幾乎必然伴隨著戰爭的失利或是經濟的衰退。當本該是順勢而為、錦上添花的宣傳手段被極權主義異化成維系權力的重要工具時,人們終于發現事實并非那樣美好。但一開始便以“絕對正確”作為根本前提的極權主義信仰,卻幾乎必然無法容忍公開的質疑和反思:“兩個體系都沒有為重要批評提供公共論壇,宣傳和武力監管著它。”
彼特沃克蘸著黑色喜劇色彩將這一矛盾的情景描繪成:為了達到“公開的一致性”所作出的“公開的偽善”。“它們塑造的公民是,在命令下歡呼,在公共場合談論正確之事,甚至相信宣傳告訴他們的一些或許多內容,但這些行為都只是表面的而非發自內心的。”政治宗教中的每一個人即便不會完全表現出別人期待的樣子,但起碼他們清楚別人在期待什么。
在行動上,人們的容忍和配合看起來是全方位的。東德的幾乎每一位公民都會參加好幾個群眾組織,比如德蘇友好協會;兩種體系中的許多普通公民都被選作了“宣傳員”或者“鼓動員”;人們欣然接受順從所帶來的“小恩惠”,比如假期、升遷、出國旅行的機會等等。他們既沒有理由不接受這些“恩惠”,也沒有理由不害怕那些幽靈般存在的恐怖懲罰。實際上,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與這種體制密不可分,書中引用了哈爾伯格的觀點,認為東德知識分子并不是主要因為監禁或酷刑才選擇順從,他們更多的是擔心專業受到阻礙。不過,相互作用的另一面是,本該是極權主義堅定維護者的官員群體開始動搖甚至瓦解,哈維爾描述了這種精神真空對官員造成的影響:“這個國家正被無個性的官僚們所操縱,他們公開宣稱支持革命意識形態,但是他們照料的只是自己,而且不再相信任何東西。”
最終,當人們公開以行動撕破表面的和平時,一切已經太遲了。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信仰在人們心中無以倫比地重建,繼而又轟轟烈烈地毀滅,其間穿插著體制與人的寸土必爭的較量。人們極其隨意地表示順從,卻又近乎苛刻地堅守底線。人,并不是政治宗教的玩物,或許相反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