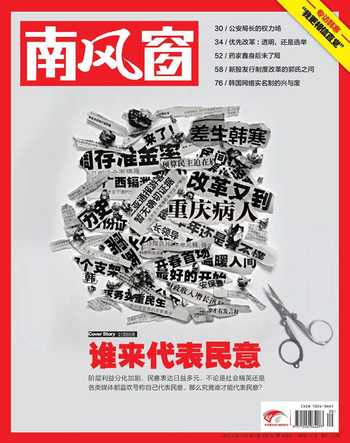不行反思,何來共識
趙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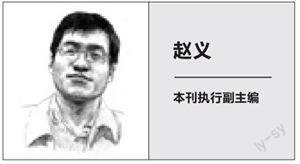
當下中國社會,共識度稀缺,對于這一點恐怕多數人都不會有異議。缺乏共識,已經成為改革陷入停頓等重要問題的最明顯的表征。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對于缺乏共識的一般解釋是“帕累托改進”空間的萎縮和排他性、獨占性利益的形成。缺乏共識的后果就是既定利益結構的固化,而后者的實現又反過來強化了前者,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面臨陷入特定困境、無以自拔的危險。
不過,任何在社會問題上形成的概念、觀念,一旦產生,在人們的頭腦中扎根,自身就有了生命力,就像預言的自我實現現象一樣,會自我強化。這個時候,反思就很重要,并且是毫無例外,無論你屬于哪個階層,權力和財富的差別有多大。一旦喪失反思的能力,沒有政治共識的社會可能就真的會徹底扎根了。只要保持反思的能力,凝聚共識的前景就仍會有一絲曙光。
漢語的反思常常被理解為內省的意思,在英文翻譯上,很多翻譯的著作將英文deliberation一詞翻譯成“反省”。從這個詞語的源頭上說,是權衡的意思,權衡自然意味著不止一個選項,所以又引申為自由的意思—自由(liberty),就是有得選擇。顯然,這種理解更有啟發。失去反思能力,意味著不再權衡,從本質上說也是陷入了徹底的不自由的狀態。
這種反思或者權衡是民主政治的源頭活水。正如人們看到的,民主社會里,充滿著各種政治性的爭執,這不是民主沒有效率的表現,而正是民主的本質,即以公開的政治程序對于不同價值進行艱難選擇,或用流行詞匯說,就是“左”還是“右”的選擇。
在共識變得稀薄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反思能力并沒有徹底喪失。在政治事務層面,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有一些新的共識的形成,比如說追求穩定,可以說多數人自覺不自覺內心是有一個權衡的過程的,最后就是多數人并不傾向于激進的改變政治秩序的做法,而傾向于持續的改進。
而改革開放本身,也是執政者權衡的過程,特別是在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和多數人的物質福利兩者之間,選擇了后者,從而告別了短缺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今天人們所懷念的就是當年打破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的勇氣和責任倫理。用執政黨的話語說就是“實事求是”。1977年處理“逃港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年鄧小平復出第一次視察到廣東,就聽到了當地的反映,他留下了兩句著名的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考察當下的缺乏共識,那么就應該進一步考察其背后面臨的權衡,作出正確的、“實事求是”的決斷。今天最大的改革的“實事”是什么?應該說就是公權力難以受到有效約束。鄧小平在1980年用“權力過分集中”的話語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
造成共識難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們尤其是掌握公權力的人在進行權衡時,忽略對于公權力的約束。不管是發展經濟,還是解決某種社會問題,為了“短平快”,往往是以公權力進一步集中,以一切手段維護公權力“暢通無阻”,破壞制衡和約束的方式來進行。反思、權衡出現了盲區,其后果無不是進一步撕裂了社會的共識。不然,人們為什么會懷念改革開放之初的改革者,而對近些年出現的一些所謂“鐵腕改革強人”卻充滿疑慮和不安呢?
這種疑慮和不安本身就是凝聚共識的希望,因為疑慮和不安代表了一種反思、權衡的能力。越是如此,人們將越會發現,對于公權力的約束應當具有更優先的價值序列上的地位。也只有如此,使用源于西方的“左”還是“右”的概念才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