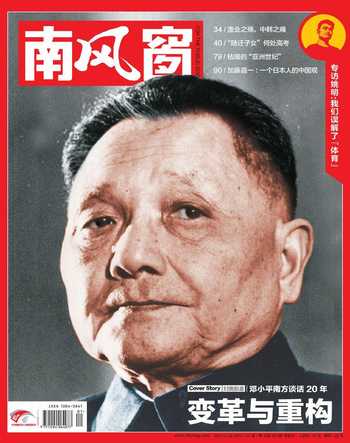“城市人口超農村”的風險
石勇
一個數據在描述中國的深刻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在北京發布《社會藍皮書: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指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50%,中國歷史上城鎮人口首次超過鄉村人口。
這似乎足以告慰從100多年前就開始的“現代化”夢想。一日千里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終于終結了幾千年來農村人口多于城鎮人口的超穩定社會結構。5000年的歷史,以人口比例改變為象征,中華民族在這里開始了拐彎。
畢竟,城鄉人口結構的改變,會傳導給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使一個國家不可逆地擁抱現代文明。從世界范圍,尤其是西方來看,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軌跡大抵如此。
然而,放眼現實,這個消息并不怎么讓人高興。其城市化路徑讓人深感不安。
第一個問題是:城鎮人口超過鄉村人口,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嗎?
顯然不全是這樣。如果說從改革開放后,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基本上是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農村居民轉化為城市居民無論是否有制度相配套,還有產業結構相配套的話,那么,從21世紀初開始,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從那時開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的擴張沖動,權力對農村居民“強制城鎮化”的抱負,已經成為主角。城市的擴張迎合了官商通過占有農民土地來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訴求,而農民則在這種擴張中遭到剝奪,或轉化為依賴城市利益結構,尤其是畸形的房產利益結構為生的寄生階層。
而在對農民的“強制城鎮化”中,一方面既具有政績的先驗渴望,同時也有打農民土地主意的深謀遠慮。在這種思維下,“強制城鎮化”嚴重缺乏產業結構的配套。農民確實從農村搬到了城鎮的居民小區,然而,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需要錢的情況下,往往陷入窘境。新增加的“城鎮化率”,使城市處于一種表面繁榮實際卻危險的狀態。
第二個問題是:城市化是否實現了在制度上給予所有居民同等國民待遇,是否預設他們是平等的權利主體?
在一個到處都有“暫住證”、“居住證”之類標簽的社會里,這是讓人遺憾的。《社會藍皮書》里提到,目前城鎮常住居民里有近四成是農民工。這是無根地漂浮于城鄉之間的一群。
在城鄉存在制度隔離的時代,農村社會具有為城市社會“造血”的功能。而現在雖然農村和城市所分隔的社會結構已經打破,但城市社會仍然企圖只是通過對農民工身體的“城市化”,掠取其勞動力來支撐自己的經濟結構,以及分配給戶籍居民福利。它拒斥農民工在權利上、身份上變成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想而知,這種“城市化”是多么沒有意思,而所謂的“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完全是現有經濟結構能夠支撐農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的一種錯覺。一旦經濟結構出現大問題,社會危機就不邀而至。這一幕幕,近年來已經屢見不鮮。
中國用30多年的時間,以世所罕見的速度改寫了5000年的歷史。城市化的這種低劣質量,當然不是速度的過錯。但一定是某種程度上的失策。它從一開始并沒有把城鄉居民權利和福利均等化,現在仍然對已經融入城市經濟結構的人進行權利排斥。
到了下決心廢除一系列阻礙真正的城市化、阻遏國民權利平等的制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