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履責的困境與突破
石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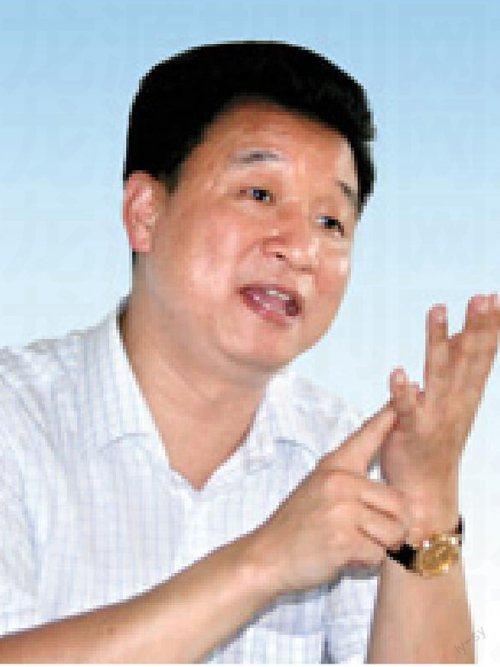

2012年新年伊始,地方“兩會”陸續召開。地方人大應是與民眾聯系最緊密的機構,但由于人大職權的虛化等原因,普通民眾對人大接觸不多,對其內部運作了解甚少。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自2005年至2011年當了7年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是全國唯一一位出任地方“人大常委”的憲法學學者。他的體會是:在中國漸進式變革的路上,人大仍是民眾表達聲音、監督政府的最佳渠道。
憲法學者當上“人大常委”
1970年代末,中國社會對民主法制建設要求迫切,地方開始設立人大常委會,目的之一是加強對政府的監督。但剛設立的地方人大常委會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甚至不知道怎么開會。于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時,專設了旁聽席,地方人大常委會領導前去觀摩,回來照搬照抄。
1988年~1993年任武漢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珣,認為要把人大常委會會議開好,必須吸納有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士參加。他與著名法學泰斗、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馬克昌商量,達成一項協議:在每屆市人大常委會中,給武大法律系留一個名額。
于是,馬克昌成了武漢市人大常委會中第一位法學專家。嗣后武大法律系改為法學院,前后4任院長當過武漢市“人大常委”。但很快問題來了:第三、第四位院長都是研究國際法出身,對國內法律的學習不系統,而地方人大的運作主要與國內法律有關,包括憲法、組織法、選舉法等。這兩位院長在人大會議上不愛發言,又經常缺勤。
第四位院長干脆請辭。這位院長本來還有兩年任期,接替他的是武大法學院教授秦前紅。秦前紅曾在市人大機關搞過法學講座,時任人大常委會主任趙零對其印象頗佳。趙零認為,我們從武大選“常委”,不一定選法學院院長,更要選熟悉與人大有關的法律法規,并對人大工作有熱情的人。2005年底,秦前紅被補選為武漢市“人大常委”。
怎樣開會?
198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曾說:地方人大有四項職權:立法權、人事任免權、監督權和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如何體現這四項職權?主要方式就是開會。
2006年1月上旬,武漢市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有項議題是“審查和批準2005年全市和市本級預算執行情況及2006年全市和市本級預算”,由市財政局長向大會作預算報告。在預算報告的主頁后面,附了當年預算項目的表格,最后一項“其他”,竟然列了38億。
以前人大會上,這項審議是走過場的,但秦前紅是研究憲法的學者,很想知道納稅人的錢怎么花的。他就詢問:“請財政局長解釋一下,這38億是怎么回事?”財政局長猝不及防,愣在當場,因為從來沒有人大代表詢問過他。局長說:“對不起,這個問題我不大清楚。是不是會后再告訴你?”秦前紅說:“按照《地方人大組織法》、《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的規定,人大常委對你提出口頭詢問,必須當場答復。”局長更尷尬了,連說:“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會后,消息迅速傳開:市人大來了一個新常委,是武大教授,敢較真。
3個月后,市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審議“本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的報告”。會上來了個市長助理,說:“我代表市政府,就整改情況來向人大常委會作報告。”
市長助理報告完,秦前紅又發言了:“你的身份有問題。第一,你是市長助理,不是市長或副市長,《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地方人大組織法》沒有規定市長助理的地位,沒規定你可以代表市長來作報告;第二,報告里也沒說你受市長委托來作這個報告。你既非法定代理,又非委托代理,說明你沒有法制觀念,我們表示很遺憾。”
市長助理也很尷尬。
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出臺,規定人大不能再對司法機關搞個案監督,但人大又不能完全放棄對公檢法的監督職能,有些地方人大就摸索出一個辦法:每年人大常委會安排專門會議,聽取公檢法的“辦案質量專項報告”。
以前,一些地方人大在開會之前,都會安排幾個固定發言人員,一是防止人大常委在會上都不發言,導致會議冷場,二是掌握發言尺度,“正確引導輿論”,給會議定調。
有一次,武漢市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來作辦案質量報告,由人大常委評議。市公安局長的報告,內容有可商榷之處,邏輯也不太通順,但幾位固定發言的常委都一致稱贊。秦前紅本來沒準備發言,但他實在聽不下去了,也來發言:“我認為書記和局長的報告水平非常高,體現在哪里呢?這份報告寫得如此之糟,你還把它念得瑯瑯上口……”
第二年,公安局長又要來作報告。手下起草好了報告,局長退回,批示:“去年我們去作報告,秦教授對我們的批評,言猶在耳。今年一定要把報告寫好,不能再讓我難堪了。”
2007年1月9日,武漢市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內容有聽取和審查武漢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換屆選舉等。本屆政府市長李憲生已被提名為下屆市長人選。大會前,市領導到各區代表團聽取意見,秦前紅見到李憲生,向他提意見說:“李市長要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有一個重要標題:‘明年工作的安排,但在人大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府之前,這一屆政府不應該安排下一屆政府的工作。”李憲生聽了,馬上令秘書班子修改,到他正式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這個標題改成了“對政府明年工作的建議和打算”。
2008年,在一次武漢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一位列席會議的副市長手機響了,他很大聲地接電話。全場的眼光都看著他,覺其做法不妥,但又拉不下情面說。秦前紅申請發言:“有人說過,民主從開會開始。你對人大會議的態度,就是對人民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態度。副市長在人大會場上接聽電話,是不合適也不嚴肅的,是極其不民主的。”
副市長極為難堪。消息傳到市政府,時任市長阮成發特地召開一次市長常務會議,阮成發說:“同志們,我們以后到人大開會,不是接不接聽手機的問題,而是你根本不要帶手機去開會!”會后,市政府專門出文:《市政府組成人員出席人大會議的相關規則》。
如何立法?
2001年,中國《立法法》出臺,規定地方人大(副省級和計劃單列城市)有地方性法規制訂的權力,但地方人大缺乏懂法律、懂行政機關事務的人才,不具備自己起草法規的能力,于是,起草工作往往由行政部門來承擔, 這些部門把自己的意志加進法規草案,導致的結果就是“部門利益法制化”。
秦前紅當上人大常委后,積極倡議“專家起草”法規。專家的立場和態度是中立的,他們可以借助充分的調查研究、科學的研究方法、專業化的技巧,把法律從語言、結構、制度安排、制度表達都搞得更適合。幾年下來,武漢市人大依靠專家起草了多部法規,地方立法水平,很快排在了全國前列。
對法律、法規的審議一般要經過“三讀”或“三審”。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由人大法制委員會審議環節。但很多地方人大法制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形形色色,法律專業人士不多,審議法規時隨意把條例翻一翻,發表一下感性意見,就算完事了,武漢市人大也不例外。
人大審議法規時,有一個工作班子負責記錄,這個班子是人大機關的法律法規室,它并非人大常委會的組成部門,但在立法過程中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因為,這個工作班子記錄時,對人大常委、代表所提的意見只作選擇性吸納,甚至根本不聽你的。
這讓秦前紅感到奇怪,因為法律規定地方人大常委會、人大代表對法規有審議權,他建議:“人大常委提的意見,如不被采納,應被告知原因;法制委員會審議法規前,應事先發材料到每個委員手上,以便熟悉情況;審議中應該建立‘逐字逐條審議制,盡可能提高立法質量。”他的這些建議,都被采納了。
在立法過程中,很多地方人大領導不想多惹事,特別是涉及行政機關利益時,不愿與行政機關對立。而且在中國的現實中,人大代表會上討論的法規,往往是已在人大常委會報送年度工作計劃時由市委常委會議通過的,涉及行政機關主導起草并提出立法議案的還要經過市長辦公會討論,人大如通不過或作太過重大的修改,不好向市委、市政府交差。
武漢市人大審議的《東湖風景區保護條例》,秦前紅建議充分借鑒國內外保護湖泊的先進經驗和先進制度。他說:在武漢市經濟發展過程中,東湖逐漸遭到破壞。要遏制這種狀況,就必須在人大立法中創設一些具體制度,禁止在東湖周圍亂開發、亂建設,這一點,國內外都有先行者。但秦前紅的建議最終未被采納。
不輕易碰人事問題
人事任免,也是人大常委會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同級政府及法院、檢察院的組成人員,都要經過人大選舉或決定產生。這項權力理論上很重要,但在實際行使時,任何一個地方黨委,都不希望人事任免出問題。現在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多由地方黨委書記兼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最怕人事任免通不過,在書記那里交不了差。
秦前紅所在博士點的一個學生,如今在某地當了市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他說:“人大最要命的是當場表決,特別是電子表決,當場公布票數,你想改都沒機會了……”秦前紅當常委這7年里,武漢市人大有過10幾項人事任免通不過,包括對法院副院長、檢察院副檢察長、發改委主任等人的任命。
秦前紅說,那一次發改委主任的任命案未通過,是常委們普遍對這位擬提請任命人員有意見。本來審議任命案之前,應該先免去此人的原職務,即“先免后任”,但那一次卻改為“先任后免”。當時,一看任命議案沒通過,主持會議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立即宣布散會,不再進行免職議程,總算把此人的官職保住了。
早年有學者認為,要提高地方人大的地位,就要提高人大主任在黨內的地位,最好由地方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這樣既能夠體現黨對人大的領導,又能體現黨的依法執政思路—不是黨直接管政府,管具體案子,而是由黨委領導到人大去,通過人大來實現對“一府兩院”的領導。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體制在實際執行中也有困難和問題。用某些學者的話說: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后,既可以“左轉身”,用人大名義監督政府;又可以“右轉身”,以黨的名義指揮人大。這種情況下,人大的地位就可能達不到當初制度設計所要提高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