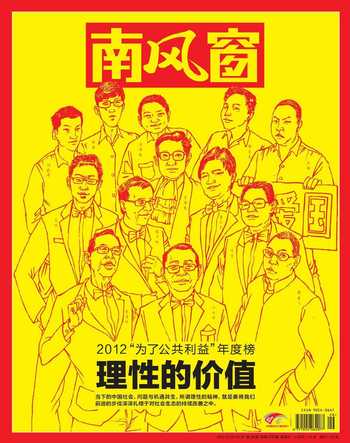參與的困境:2012年的社會沖突
于建嶸

2012年,中國發生了很多社會沖突事件,相對于往年,在特點上有一些變化。
總體來說,群體沖突事件在數量上有所減少,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是中國政治權力換屆移交變動較為重要的一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管控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預防和化解群體性事件。
不過,這也不能排除個別地方在面對上級的“維穩”考核壓力時,采取強力打壓、“欺、瞞、捂”等非法方式,使得群體性事件只是統計數字上有所減少。但就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某些事件在規模和影響上要遠遠超過去年。這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和因反日游行示威引發的社會騷亂。
近幾年來,有關大型化工企業、采礦及大型電站建設、垃圾焚燒等領域的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快速增加。據有關專家統計,自1996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中國環境重大事件也有大幅增長。這其中2012年發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浙江寧波事件均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影響。
預防型維權
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調查,我們可以發現有如下幾個特征:
其一,從“事后救濟型維權”向“預防型維權”發展。2005年,浙江東陽受到污染侵害的民眾多次群體上訪,并最終造成了激烈的沖突,是學界公認具有影響力的第一起環境群體性事件。從行動爆發的時間和維護權利的性質來看,屬于“事后救濟型”,即環境污染已經發生,并對特定的人群產生了危害,是權益已受侵害后的維權。而自2007年廈門PX事件延續至今的許多事件,如2012年發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浙江寧波事件則是因“可能發生的風險”而引發的群體事件。這些事件,均在立項或施工階段;項目是否有危害,并沒有得到確切的證實,且不一定有科學依據。維權民眾抱著對自己沒有好處,卻可能有害處的心理,進行維權。某些項目還具有符號的意義,如從廈門PX事件后,到大連再到寧波等地都因此項目引發了群體性事件,而參與的民眾并不一定知道、有的甚至不想去知道PX是什么,有什么危害。
其二,許多事件背后均有較復雜的利益關系,環保可成為各種利益訴求共同運用的具有正當性的話語。如江蘇啟東事件,就有普通民眾、活動的組織者、房地產商、本地公務人員、外地交流來的主政官員以及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等之間的利益沖突。許多遭到反對的建設項目背后存在著官員的個人政績、征地拆遷、漁業受損、房地產項目、小化工企業等諸多復雜利益的糾葛。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和自身密切相關的居住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環境問題容易成為一個公共話題而引起廣泛的關注。
其三,網絡時代的社會動員方式,使事件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度。環境問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網絡時代的意見領袖通過自媒體,很容易將其變成地域性的社會公共話題。
一般來說,議題最初源于網站的地域性帖吧或論壇,近年來個人微博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會以網友聚會的方式從網絡走到現實生活。在民意互動過程中,一些地方名人也會參與其中,并在事件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如某一排污引發的群體事件,具有本土身份的原法院副院長和政協副主席就是核心人物。
其四,環境群體事件抗爭的主要對象是侵權的企業和政府,往往造成多輸局面。在各種利益的糾葛中,事件會轉化為民眾對地方政府的抗爭,其發展過程容易偏離最初的議題,在各種社會不滿的情緒背景下,經常發生較激烈的對抗,并伴有圍堵黨政機關、阻塞交通、圍堵河壩乃至于打砸搶燒行為,最后均以政府妥協而告終。如什邡宏達鉬銅礦屬于四川災后重建中國家支持的項目,根據設計及環評,并不會對當地造成環境問題,而且會對當地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無“社會組織”的后果
2012年因反日游行示威引發的社會騷亂,也是一起非常嚴重的事件。9月15日,隨著中日釣魚島爭端的演化升級,不少中國民眾舉起愛國大旗,許多城市均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抗議日本的購島等侵犯我國主權和領土的行為。
然而,在游行示威過程中,一些城市如湖南的長沙、陜西的西安、山東的青島等地出現了打砸日本車、打傷日系車車主,甚至焚燒大型商店等違法行為。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底層民眾對社會強烈不滿情緒的極端宣泄,而當時正在爭議的釣魚島事件使這類宣泄披上了愛國的外衣。
由于這些民眾自發的游行示威行動,不能約束不法分子的打砸搶燒行為,最終將愛國行為演變成了局部的社會暴力,破壞了社會秩序。這既是社會上存在不滿人群的一個結果,也是我們缺乏公民訓練、社會組織處于一種總體性壓抑,沒有多少發展的一個癥狀。
群體性事件是觀察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在其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國家與社會的博弈,又可以看到民眾與政府的互動。
就2012年群體性事件的特征來說,其中的一個教訓尤其值得重視:不僅國家對社會的管控習慣,政治上或行政上自上而下地“組織”社會的方式已經不適應當下的社會結構、人們的權利意識以及市場體制,而且,也已經不適應存在著很多失意者、存在著復雜的利益沖突的社會格局了。
擴大政治社會參與
因此,2013年,在調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進行社會改革時,有三個方面必須加強。
一是增強社會自治的力量,既培養“社會”相對于“國家”的壯大,自我組織,同時也是在培養它的自律,保證公民和政府在互動時能夠在理性和法律的軌道上。缺乏自我組織的社會是脆弱的、結構是紊亂的,而在公民以一個個攜帶情緒的社會原子和政府互動時,也將混亂而無序。社會秩序的穩定,其實是以社會能夠自我組織為基礎。
二是通過調整社會的利益結構,改善已經畸形的社會結構。一般而言,人們在進行社會行動時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有利益的訴求。但不公平的、構成了剝奪的利益結構,讓人們在進行社會行動時,可能已不僅僅是有利益訴求,或根本不是為了利益訴求,而是為了發泄。當利益訴求有一個合理的預期時,人們會懂得理性地約束自己,但如果利益訴求沒有預期,或者就是為了發泄,則只會導致社會行動過激化。破解這一困境,不是消除人們的社會行動,而是通過調整利益結構,為人們理性的社會行動提供社會和心理的背景。
三是為人們的政治和社會參與提供制度性的渠道。事實證明,人們有多大可能進行實際的政治參與,就有多大可能減少社會行動。社會行動中的參與往往是政治參與中制度渠道堵塞的結果。而在社會行動中,人們的參與不應該視為是對既定秩序的挑戰,而是一種表達,這一表達應在憲法、法律框架內給予承認。只有政治和社會參與越開放,公民才能在參與中獲得一系列的程序、經驗和方法,減少當下的社會沖突所產生的風險。
建構一個由在意識上、權利上都具有公民特征的人所組成的社會,這一命題越來越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