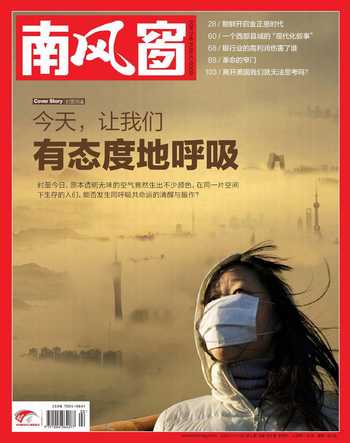俄航天為歷史還債
方亮

自戈爾巴喬夫改革始,俄羅斯民族走過了一代人還多的時間。政治經歷反復,經濟難上正軌,紅色帝國留下的家底日益攤薄。過去一年來,曾經輝煌無限的航天業連續經歷失敗,意味著老本已經吃光,俄航天業像這個迷茫的國家一樣被迫重新上路。
“政權回來了!”
從2010年12月到2011歲末,俄經歷了8次重大航天項目失敗,其中不乏“進步”號貨運飛船30年來首次發射失敗使國際空間站險些陷入“無人駕駛”狀態和中俄兩枚火星探測器未按計劃變軌至今處于下墜狀態這樣的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失敗。眼下已然開始布局新任期人事班子的普京,把愛將德米特里·羅戈津從駐北約特別代表的位置上召回莫斯科任副總理負責軍工問題,并在12月26日與其會面時稱“俄航天業管理體系和治理手段均存在不足”,要求后者著重解決該問題。
3天后,羅戈津便與航天署署長波波夫金會面,要求他提交幾次項目失敗調查報告和今后的發展計劃。當天,素來被視為鷹派代表的羅戈津在“推特”上發言稱:“我警告你們,政權回來了!”
2011年俄通過了一份被媒體稱為“為戰爭而非為商業而準備的”2012~2014年預算。其中,國防和軍工采購費用大幅提升,而教育、衛生、住房交通等撥款卻面臨縮水。因在北約表現強硬而頗受普京青睞的羅戈津,回歸后負責的正是包括航天產業在內的國防和軍工領域。所以可以預見,羅戈津高調宣示“政權回來了”的底氣來自普京對航天的財政支持。這對于自蘇聯末期就從未“吃飽”的俄航天產業來說確實是最為急需的。
10多年的“饑餓狀態”
蘇聯解體時,圣彼得堡只剩下了3天口糧,時任市長的索布恰克(普京日后政治導師)被迫向中央求救。1992年,蓋達爾任俄羅斯總理后,由于資金緊缺,顧不上航天產業,曾試圖通過一項法案,禁止各銀行向航天業發放貸款。法案雖被俄共阻止,但國家對航天業仍基本“斷供”。此后,經濟改革失敗,油氣價格疲軟,想活下去就只能自力更生。就像“蘇霍伊”戰機設計局的設計師西蒙諾夫費盡心力向中國出口蘇-27戰機救活了這家傳奇企業一樣,俄航天也將目光瞄向了國外。
向俄航天人伸來橄欖枝的是美國人。1990年,建造國際空間站的計劃被證明非美國可獨力承擔。1993年6月,美國國會因一票之差未能阻止國際空間站的建造計劃。隨后,俄美迅速走近,簽署了兩個航天大國聯合其他多國建造國際空間站的協議,俄航天因為美方資金的注入而得以延續生命。
自此,俄航天開始吃老本,賺外匯。它同全球10多個國家合作,承攬發射項目。從1992~2005年,俄僅向該產業投入43億美元,而國際業務卻為其帶回了55億美元。但是,用俄《航天新聞》雜志專家伊戈爾·利索夫的話說,這10幾年俄航天一直處于“饑餓狀態”,可以糊口,卻無力搞開發。以即將廣泛投入使用的“格洛納斯”全球定位系統為例,其第一顆衛星在1982年進入軌道,按計劃1995年就應該實現全球覆蓋,但財政的糟糕讓該計劃一推再推。雖然2011年末俄羅斯人已經可以買到裝有“格洛納斯”信號接收模塊的iPhone 4S手機,但該模塊的出現已經晚了16年。
2000年,為了糊口,一幅巨型“必勝客”比薩廣告被掛到俄火箭上,在眾目睽睽下升入太空。2002年,俄航天幾乎“斷糧”,甚至國際空間站項目都無法維持,最后勉強依靠送兩名富豪進太空旅游賺來的錢度過難關。嘗到甜頭的俄航天署欲擴大太空旅游規模,他們趁著美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船爆炸造成俄壟斷通往國際空間站線路之機,提出航天員在空間站駐守時間由6個月延長至1年的建議,這樣可讓俄方每年多發射一次飛船,將更多的游客送入太空。但美方以在失重情況下待的時間太長會造成肌肉萎縮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眼下,俄方已將太空旅游船票價格從2000萬美元升至6000萬,自是應者寥寥。
2004年小布什宣布結束航天飛機計劃,壟斷地位鞏固的俄方先后8次對美方加價。如今,美國通過俄“聯盟號”飛船運送一名航天員的費用已經漲至4000多萬美元。
全面衰落
從2004年開始,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開始將大筆的石油美元投向航天領域。普京秉持蘇式經濟理念,喜歡使用略帶民粹色彩的政治手段,而航天產業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又可以激發民族自豪感,提高其支持率。此外,航天產業帶來的利潤也被他看重。如今,國際太空經濟總規模超過2765億美元,但俄在其中只占3%。意欲在此間大賺一筆的普京這些年持續增加對航空業的撥款,即便當經濟危機來襲后,對航空業的傾斜也在持續。
但是持續了10多年的“饑餓狀態”不可能不留下后遺癥。2011年“進步”號飛船墜毀后,航天署署長波波夫金被請到杜馬,向全體議員解釋航天業的衰落。他稱,現在俄100多家航天企業只有33%能接到訂單,他們的設備急需升級卻沒有足夠的資金,而剩下的企業基本上處于停產狀態。此外,航天業25萬從業人員中90%要么超過60歲,要么低于30歲,年富力強者極少。由于工資太低,很難吸引尖端人才。以產業龍頭“能源”集團為例,那里平均工資僅不到1000美元。利索夫評論稱,如果航天業開出的工資仍然比不上手機開發商,那么俄將繼續造手機而不造衛星火箭。
多年來,俄每年航天發射次數占全球總數的40%以上,卻只能占到太空經濟份額的3%,主要原因在于俄無力承擔技術上更復雜的項目,比如地球探測、氣象研究、全球定位、災難預警和通訊等。10多年的“饑餓狀態”讓俄無力搞技術上的探索與開發,不進則退,落后是必然的。英國路透社給出分析,俄在發射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那是因為1990年代當美國衛星可以持續在太空待上10年時,俄羅斯衛星卻只能運行半年。為此他們不得不頻繁更換衛星,其發射次數便冠絕全球了。俄目前的技術可以保證“格洛納斯”這類地球衛星項目,但當進行深空研究時,其技術力量便遭到質疑。中俄捆綁發射火星探測器的項目是俄時隔10多年后再一次向火星發起沖擊,卻遭到尷尬失敗。這些都凸顯了俄技術領域的尷尬。
2010年12月3顆“格洛納斯”衛星發射失敗、2011年8月“進步”號太空船墜毀,問題都出在運載火箭身上。而承載它們的“質子”號和“聯盟”號火箭卻都已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其設計斷無問題。如此一來,問題便只能出在火箭制造上,這便又牽出了俄制造業的落后。就像佩爾米諾夫所言,航天業是整個國家制造業的塔尖。如今,俄羅斯制造業的衰落有目共睹,長期投資不足,加上油氣經濟所引起的“荷蘭病”的擠壓,致使俄連拖拉機都要進口,火箭制造問題頻出就更不足為奇了。
資金、時間,一個都不能少
資金缺口、人才短缺、技術落后,俄航天業面臨的這些問題都與俄軍隊面臨的問題極為相像。資金的短缺讓俄軍長期以來只能堅持單純依靠戰略武器保衛國家安全的方針,一場“5日戰爭”讓普京終于痛下決心進行軍事改革,但俄軍工卻已經造不出滿意的戰艦,而不得不從法國人手里買艦船和技術。在被俄各界稱為“第4++”代戰機的蘇-35上,電子系統均采購自法國。被俄寄予厚望的第五代戰機T-50目前尚未裝上電子系統,估計它們也將進口。
遲來一步,這成了普京治下許多產業所面臨的大問題。1990年代的混亂所耽誤的俄航天業革新進程,仍需要巨量投資和時間來補課(前蘇聯航天員格列齊科認為最起碼需要10年)。以普京對航天業的持續投入以及派心腹集中解決問題的做法來看,俄航天業暫時可以不必擔憂財政和國家意志問題。
只是,俄現在對航天業的高投入建立在油氣價格穩定的基礎上,倘稍有閃失,財政傾斜能否持續便不得而知。說到底,俄眾多產業的前景是與這個尚處迷茫的國家的改革方向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方向選擇不當,難保不再現衰落與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