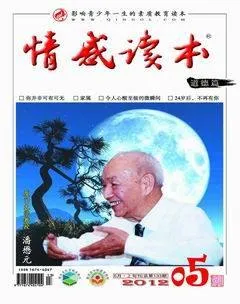家屬
鄧一光
1
在西藏聽了幾個關于家屬的故事。
一個故事是有關邊防某團政治處主任黃白華妻子的。邊防某團駐守在察禺,那是麥克馬洪線的一段,自然條件十分艱苦,交通極為不便。一條破舊的道路在極其危險的山間蜿蜒穿行,冬天大雪封山,天氣轉暖后又老是下雨,路其實是三天兩頭不能暢通。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也常有塌方、滑坡和泥石流一類的險情發生。這樣的路,若放在了內地,是沒有人會去走的。
但那是通往察禺唯一的路,不管你是進察禺,還是從察禺出來,如果你不是鳥兒,只能從那條路上通過。
團政治處主任黃白華駐守邊境,已經好幾年沒有探過親了。
于是黃白華的妻子就請了探親假,收拾好東西,啟程探望丈夫。
在成都要買到飛往昌都的機票很難,一般的情況下得等上一個多星期,如果遇到暑期探親季節,十天半個月滯留在成都是常有的事。當然也可以走陸路,由道路險惡的川藏線進藏,那樣的話,由成都到昌都,也得一個星期。
黃白華的妻子千辛萬苦到了昌都,然后又等去察禺的車。好不容易上了去察禺的車,車顛顛簸簸地往察禺走,走一段,停一下,走一段,停一下。妻子抱著帶給黃白華的家鄉特產,被顛簸的車子不斷地拋起來,又摔下去,五臟六腑都差點兒沒顛出來。妻子那一刻想流淚,不是為自己,是為丈夫和丈夫的戰友,她想他們真是太難了。
車子終于徹底地停下來了。不是到了察禺,察禺沒到,而是遇到了一場暴風雪,路被封住了。
司機無可奈何地對黃白華的妻子說:嫂子,不是我不送你們,路再險,道再難,四個車輪子我管著,但管不住老天。我沒法把車開上雪山,咱們只能回昌都了,你和大哥在電話里商量商量,明年再約個好日子進來。
黃白華的妻子把額頭上的亂發理了理,拉開車窗,看了看眼前的雪山。
雪山美極了。
黃白華的妻子轉過頭來問:翻過這座雪山需要多長時間?
司機回答:8公里山路,要是壯小伙,睡足了覺,帶上酒和肉干,不遇到雪崩什么的,順利的話,五六個小時吧。
黃白華的妻子說:謝謝你了,兄弟,你請回吧,我就在這兒下車,我自己往前走。
司機大驚道:那怎么行?!你還要不要命了?!
黃白華的妻子微微地笑了笑,平靜地說:怎么不要命,我是來看他的,不要命我怎么進去看他呢。
司機怎么攔也攔不住,一旁有個探親返隊的戰士見狀說:嫂子,我本來打算等等,等路好走了再說,你一定要進去,我陪你。
他們開始走了,往雪山那一頭的察禺走。
她背著帶給丈夫的東西,戰士背著自己的東西,在雪地里一腳淺一腳深地走。
他們走了足足10個小時,也許時間更長,誰知道呢?反正他們用光了所有的力氣,已經走不動了,幾乎就要躺在雪里睡了,并且永遠不再起來,但他們終于走到了。
黃白華接到消息,說他的妻子趟著大雪進來了,不顧一切地進來了。黃白華丟下手上的事沒命地朝山下跑去。他看見了他們,看見了他的妻子和那個可愛的戰士,他們在雪山腳下,是兩個慢慢蠕動著的小黑點。他咧開嘴傻笑著,揩一把頭上的汗,撩起兩腳的雪粉朝他們奔去。
他跑近了。
他站住了。
他像一個真正的傻瓜站在那里——
那肯定是他的妻子,她一身雪粉,仰著烏紫色的臉兒,兩只手探索著,遠遠地伸向前方,明亮的眼睛呆滯著,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她害上了雪盲,什么也看不見了!
他叫她。
她聽見了他的聲音。她能分辨出他的喘息聲來。她朝他伸出手去。她也叫他。
黃白華撲上去,緊緊地、緊緊地、害怕再失掉了地摟住了妻子。
那個漢子,就那么站在雪山腳下,嗚嗚哭出聲來。
那個戰士沒有害雪盲,他在察禺當了兩年兵,鍛煉出來了,但因為一直攙扶著黃白華的妻子,用自己的身子支撐著她,甚至拖著她在雪地一步一步地走,他向著陽光那一邊的臉被紫外線嚴重地灼傷了,成了黑色。
講這個故事的人告訴我,一年之后,有人看見了那個戰士,他不知在和身邊的戰友說著什么事情,在那里呵呵地笑著,他的那張英俊的臉仍然是陰陽分明著。
雪山很美,所有見過了雪山的人都這么說。
2
另一個故事說的仍然是察禺的事,仍然是進察禺探親的家屬們的事。
這回不是一個,是二十幾個,二十幾個在內地做著西藏軍人家屬的女人,因為自己的丈夫巴心巴肝地守著邊境線,生生死死地守著邊境線,不能按預定的那樣回內地探親,她們就索性約好了時間,一起結伴進西藏去探親。
到昌都了,離丈夫近了,丈夫們也知道她們來了,兩邊的心兒都急切地想要早一點見面。包袱一丟下,臉來不及洗,女人們便爭先恐后地涌進郵局打電話。電話一通,沒說上兩句貼己話,就知道情況不妙——通往察禺的路,因為雨季造成的塌方斷掉了,不是斷了一處,也不是斷了兩處,是斷了好幾處,車輛根本無法通行。
那怎么辦?女人在電話這一頭叫。
等等吧,也許會修好的。男人在電話那一頭安慰女人。
等吧,那就等。
誰知一個星期過去了,十天過去了,故事說完了,路卻還沒有通。通是通過,但沒通兩分鐘,又斷了。西藏這種地方,遇到了雨季,這是很正常的事,雨季路不斷相反沒有道理。
女人們急了。女人們大老遠地從內地趕到西藏來,來見自己的丈夫,來和自己的丈夫團聚,卻被擱在半道上白天黑夜地講著故事。她們有的請了一個月假,有的請了兩個月假,不管假請了多長,大家在成都集中時花去了一個星期,從川藏線進來又花去了一個星期,在昌都等路通再花去了十天,眼見一個月時間過去了,連丈夫的影子都沒見著,還得從川藏線出去呢?還得從成都返回各自的家鄉呢?女人們總不能在昌都一直等下去,等到海枯石爛吧?
女人們的丈夫從察禺打電話過來說:要不,你們回去?你們回去,等明年,或者后年再進來?
不!女人們喊。
不!有女人咬牙切齒地抹開眼淚了。
女人們抹淚的時候,情況再一次出現變化。變化的不是路,路仍然沒通,仍然斷成珠鏈的樣子。變化緣于一位西藏軍區副司令,那位副司令正在昌都檢查工作,聽說了察禺的一群軍官,因為國防重任不能回家探親,聽說了他們的妻子們,結伴進藏來探親,被堵在昌都,做著海拔四千公尺高原上的織女。副司令聽說這件事后,眼睛紅了,他沉默了一會兒,斬釘截鐵地說:不能讓女人們就這么離開!不能讓她們的丈夫眼巴巴地看著她們離開!就算通往察禺的路斷得不可收拾了,斷成盤古開天地前的樣子,就算前往察禺的山全都塌下來,也要把女人們送進察禺,讓她們見到她們的丈夫!
副司令下令:由昌都軍分區組織最好的車輛和人員,送女人們進察禺;通知前往察禺路途中所有的部隊和武裝部,組織精干力量,在每一處斷路的地方等著,女人們一到,就把她們背過去、抬過去、扛過去、架過去,再往前一站送,一站一站,一直送到察禺!
在滯留昌都十幾天后,女人們再次上路了。
車艱難地往察禺開去,在第一個斷路處,她們下車,由等在那里的部隊和武裝部組織的人員攙架著,攀過爛石,趟過泥漿,送往斷路處的另一頭等待著的車輛,再往下一個地方開去。就這樣一程又一程,交通工具不斷變化:越野車——卡車——吉普車——拖拉機,在接近察禺的地方,一身泥水的女人們已經騎上了牦牛或者步行。
她們朝察禺走去。
察禺的丈夫們已經接到消息,在最后一個斷路處等著了。
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人給我講了最后的那個場面:當女人們出現在斷路的盡頭處時,等待在那里的男人們朝她們奔來。她們也朝自己的男人奔去,他們和她們跑近了,緊緊地抱在一起。然后,二十幾個內地女人和二十幾個邊境線上的男人,他們都哭了。
胡昕摘自《軍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