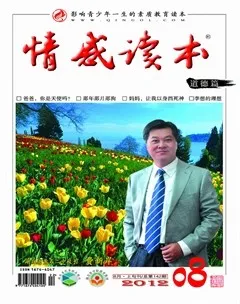努力活著只為等到你
彭珺紫
讓我見見她吧
94歲的蒂絲布羅坐在陽臺的一把老搖椅里,手里捧著那張泛黃的黑白照片:一個身上裹著毛毯的嬰兒,在搖籃里安詳地沉睡。思念溢滿蒂絲布羅的雙眼,她還能等到與孩子見面的那一天嗎?
16歲那年的夏季,蒂絲布羅和幾個女孩去野餐時,不幸被3個男人玷污。幾個月后她變大的肚子才向父母泄漏了這個不幸的秘密。在思想單純的蒂絲布羅的觀念中,嬰兒是送子鳥銜來的,并不是那次不幸遭遇的產物。
信奉路德教的父母,把她送到了一個專門接收懷孕少女的教友家中。教友會安排一切,包括孕婦的護理、孩子的出生,以及領養。
蒂絲布羅嚇壞了,她并不想把孩子送走,“求求你,媽媽,我想把孩子留下來。”
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嬰,為她取名貝蒂·珍。她每天都守著嬰兒,貪婪地盯著她,她臉上有兩個深深的酒窩,她的頭發是金色的。
領養家庭還是來了,母親嘆著氣勸慰她:“我知道你愛她,但你才17歲,你能給她什么?”
她被問住了。母親是對的,她一無所有,但她也想給孩子最好的。女兒被送走的那天,她拍下了那張黑白照片。
她繼續著自己的生活,嫁給了一個水果攤販,生育了另外兩個孩子。多年來,從羅德島州到明尼蘇達州再到加州北部,最后定居在圣克萊門蒂的一個海邊城鎮,她做過裁縫、賣過絲綢、當過學校食堂的管理員,顛簸的生活卻從未抹去她對女兒貝蒂·珍的日夜思念。
最初,她常給領養中心寫信,詢問女兒在領養家庭的生活狀況,后來,領養中心的工作人員發生了變動,她就再也沒有收到過回信。她多想去看看女兒,但領養夫婦的名字、住址,她卻一概不知。
閑下來的時候,她只能一遍遍翻看那張照片。她每天都在祈禱:上帝,如果你讓我見見她,哪怕只在遠處偷窺一眼,我發誓從此便再不會去打擾她。
這個身份盜竊賊
電話聲突然響起,蒂絲布羅從思緒中驚醒,從搖椅里顫巍巍地挪動著身體。
拿起電話,不等她開口,電話那邊傳來一個陌生男人急促的聲音:“您是茗卡·蒂絲布羅嗎?您今年多大年紀了?您是荷蘭移民的女兒嗎……”
“嘿,住嘴!臭小子!”蒂絲布羅生氣地掛斷了電話,蒼老而沙啞的嗓音依然有著震懾的力量。這個身份盜竊賊!她嘟嚷著。
電話聲卻再次響起,那個男人又問:“您愿意與貝蒂·珍通話嗎?”蒂絲布羅驚呆了,兩條腿不聽使喚地顫抖著。突然聽到那個在心底里呼喚了77年的名字,竟有幾分陌生感。
她終于與思念了大半輩子的女兒聯系上了。電話中的那個男人,正是貝蒂·珍54歲的“老兒子”布賴恩。當年,貝蒂·珍被一對挪威的基督教牧師夫婦收養,他們給她取了個新名字露絲·李。
露絲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個被領養的孩子,但她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她沒想過要尋找親生父母,直到七十幾歲時,她飽受心臟病的痛苦折磨,醫生希望她能提供家族醫療史,這對病情的治療有很大幫助。
她不得而知,兒子布賴恩于是決定弄清楚母親的身世。布賴恩向母親的出生地——南達科他州法庭請求,希望看看母親當年被領養的記錄。他拿到了一堆資料,足足270多頁,包括蒂絲布羅遭到性侵犯的書面記錄、她給領養中心所寄的手寫信……每一頁他都仔細閱讀。
布賴恩憂心忡忡,九十幾歲的蒂絲布羅可能早已過世了吧。遲疑中,他還是打開電腦,在網絡號碼簿的搜索引擎中輸入了“蒂絲布羅”這個名字。他以為會看到外祖母的訃告,但吃驚的是,一個電話號碼赫然跳了出來。
熟悉多年的老姐妹
一個月后,布賴恩帶著母親露絲飛到了圣克萊門蒂,來到外祖母蒂絲布羅那早已打掃得纖塵不染的公寓內。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一條寬闊的街道,它被兩旁的棕櫚樹籠罩著,散發著沁人心脾的棕櫚花的芳香味道。
在見到78歲的老女兒露絲的那一刻,94歲的蒂絲布羅掩飾不住自己的驚喜,她的雙眼噙滿了淚水,嘴里緩緩地吐出幾個字“我的寶貝兒”。露絲遲疑地回應了她,“媽媽。”在一旁的布賴恩和蒂絲布羅的另一個女兒——65歲的戴安娜都忍不住流下淚來。
兩個老太太促膝而坐,她們看上去就像一對熟悉多年的老姐妹。蒂絲布羅閃動著小油燈一樣透亮的雙眼,目光久久停留在露絲臉上。
她們一邊回憶著往事,一邊翻看著對方的家庭相簿,仿佛要抓住這些年失去的所有時光。
令蒂絲布羅驕傲不已的是,她一個荷蘭移民的女兒,沒讀過什么書,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牛奶場做事,竟有一些頗了不起的后代。露絲生育了6個子女,他們都各有成就,其中有一個是二戰時期的老兵,他參與了4次太空飛行、繞世界飛行了517次,還有一個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宇航員馬克·李。
那次見面之后,她們一直保持著聯系,也常去看望對方。露絲那些子孫還常邀請蒂絲布羅到自己的家鄉度假。
2011年12月28日,蒂絲布羅迎來了自己100歲的生日,在亞拉巴馬州,子孫們濟濟一堂,為她舉辦了一個熱鬧非凡的100周歲生日慶典。那天,她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了媒體。她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是從94歲開始的。
馬桂潔摘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