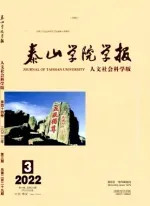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通俗藝術的審美辯護”的批評
劉德林
(泰山學院漢語言文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就標題的含義而言,本文的內容是介紹與批評舒斯特曼教授對通俗藝術的辯護,而并非對通俗藝術本身提出審美辯護及批評。因為在這方面,英美分析美學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已經對此作了足夠多的工作。當然,筆者是在分析判斷的含義上使用“批評”這個詞匯的,力圖對舒斯特曼教授的通俗藝術觀點從邏輯上進行分析,并努力避免出自非難的主觀性傾向。舒斯特曼是我的老師,筆者曾經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美國跟隨舒斯特曼教授學習他的新實用主義美學。我雖然由衷感謝他在學術與生活方面給予的幫助,但是,懷著促進學術交流與發展的目的,秉承著“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原則,筆者也就寫出了這篇文章,并將它看作為老師布置的作業,將其視為與老師在課堂之外的一次對話。
通俗藝術有時也被稱作為流行藝術,這兩個術語都來自相同的一個英文詞組popular arts,但是在中文含義兩者卻有著細微的差異:前者強調藝術品在內容上的通俗易懂;后者強調藝術品被認可與接受的廣泛性。為著方便起見,本文在今后的敘述中一律使用通俗藝術。通俗藝術大致出現在18世紀的歐洲。當時,隨著現代藝術的應用,一些原本并不存在的藝術形式相繼出現,比如歌劇、電影、攝影、表演藝術、家具、海報、計算機及電子藝術、大地藝術等,它們與傳統的藝術形式判然有別。西方現代藝術包括音樂、詩歌、繪畫、雕塑和舞蹈等五種基本形式,現代西方美學基本上是以這五種藝術形式作為審美的主要客體,并且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系統的、帶有自律色彩的美學體系。通俗藝術的出現必然要對現代美學形成巨大的沖擊,但美學家們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對其展開研究。
“通俗藝術一直就沒有受到美學家和文化理論家的歡迎,至少是不在他們的專業考慮之中。通俗藝術或者被輕蔑地完全忽視,或者被典型地譴責為沒有腦子、毫無趣味的垃圾。”[1](P169)舒斯特曼的這段話語非常典型地概括出西方當代大多數美學家對待通俗藝術的態度。在他看來,對通俗藝術的指責與批評主要出自于在社會-政治觀點及信仰事物上持有極端態度的知識分子,他們既包括右翼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也包括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分子。
他對通俗藝術的辯護出自于以下兩種理由:首先,站在杜威的實用主義的立場上,舒斯特曼批評高級藝術的疏遠的深奧主義和總體性的主張,而且對高級藝術產品和通俗文化產物之間的區分持有懷疑態度。他認為,高級藝術與通俗藝術之間的界限既不清晰又充滿爭論,因為即使在同一個文化時期,一部作品是通俗的還是高級的藝術主要取決于公眾對它的解釋和利用。其次,舒斯特曼認為通俗藝術給人們(也包括知識分子)提供了太多的審美滿足,所以不能把它完全貶低為沒有品味、敗壞人性的垃圾而不給予其美學的合法性。否則,就不僅使人們與社會的其他成員對立起來,而其也使人們自身對立起來。在舒斯特曼看來,“通俗藝術給人們帶來了快樂,如果人們譴責通俗藝術,這就意味著一方面蔑視給人們帶來快樂的事物,另一方面為它帶來的快樂而羞愧”[1](P170)。
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思想主要受惠于經典實用主義者杜威。杜威在其美學著作Art as Experience(《藝術即經驗》)中倡導連續性美學的主張,反對美學傳統中的二分觀念。這些二分的觀念包括:藝術與生活的區分,美的藝術與應用的或實踐的藝術的區分,高級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區分,實踐藝術與空間藝術的區分,以及審美與認識及實踐的區分。杜威認為美學上的這些二分思想在更深層、更基礎的層面上反映了哲學上的二元論,比如,身體與心靈、物質與觀念、思想與情感、形式與質料、人與自然、自我與世界、主體與客體以及手段與目的之間的二分。在杜威看來,這種二元論的觀點不僅將上述列舉的雙方嚴格地分割開來,同時,區分兩者的分界線及規定是固定不變的。但實際上,對于不同事物之間的區分,杜威是樂意接受的。比如,在Art as Experience一書中,杜威就將審美經驗從其他經驗中區分開來,將審美情感區別于普通情感,他還通過不同的媒介將藝術區分開來。就藝術與生活的關系而言,杜威批評了藝術的“博物館制度”,因為在這種制度下,“藝術被奉為一種高高在上的、一個遠不可及的‘偶像’、脫離物質和人類其他成就的‘單獨領域’,這已經將藝術從我們絕大多數人中撤走,從而使我們審美質量變得貧乏。”[2](P15)杜威強烈要求,盡管冒著被非審美世界墮落地盜用的風險,藝術還是應該撤去它那神圣的分割,而進入日常生活領域。這樣,藝術才能更好地改善人們的當下經驗,可以使更多的經驗變得更加豐富和滿足。在筆者看來,杜威主張去除藝術的博物館制度,使藝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這并非意味著藝術與生活的等同,博物館制度去除之后,藝術依然是藝術,日常生活依然是日常生活,消失的并非是二者之間的實質,而是將兩者分割開來的區域。這就好比廢除了院墻的大學一樣。大學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的組成部分,院墻消失了只是說明大學與社會其他部分的聯系變得更為密切了。大學依然是大學,大學可以有實驗室,但不能成為工廠;大學的教室可以在節假日當作歌舞廳使用,但其大部分時間卻只能充當教與學的場所。
在Art as Experience(《藝術既經驗》)的第9章The Common Substance of the Arts(不同藝術的共同基礎)中,杜威談到了他對流行藝術和官方藝術的區分問題。他認為,“假如現在深受人們喜愛的藝術產生于贊助商的經濟支持和牧師與當權者的操縱之下,即使它們仍然使用著‘官方的’名稱,但是原本的‘官方’的分界標準已經不再適合它們了。哲學理論知識關注那些帶著標簽的被社會的權威階層認同保護的那類藝術。通俗藝術一定在過去流行過,但那時并沒有受到文藝界的關注,也沒有引起理論界的討論,甚至也沒有被看作為藝術。”[2](P194)由此可見,杜威的聯系性的美學思想反對的是不同藝術的區分標準。在他看來,將不同藝術區分開來的標準是歷史的產物,隨著歷史的發展,原本設定的標準在新的歷史時期失去了效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取消藝術之間的區分,而只是說明區分標準應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生改變。杜威對通俗藝術也持有同情和支持的態度,認為通俗藝術也應被看作為藝術,應該引起理論界的關注。與西方現代的藝術理論相比,杜威的高明之處在于打破了建立在“美的藝術”(高級藝術或精英藝術)基礎之上的藝術隔離制度和美學體系,將通俗藝術劃歸到藝術的門類之中,這同樣也并不意味著將通俗藝術和高級藝術等同起來。為了說明藝術理論的形式和批評標準的變化,杜威列舉了雕塑、詩歌、小說等藝術形式規則的歷史性演變。比如: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曾經將悲劇看作為文學的最高形式,它的范圍被規定為描述那些在社會中高貴的人的不幸故事,而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只適合于用低等的戲劇來表演。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狄德羅則要求悲劇要拋開貴族中的偉大人物而表現市民,拋開宮廷生活而寫家庭日常生活,因為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以更好地激發起人們的痛苦與恐懼的情感。
因此,當舒斯特曼聲稱自己是站在杜威的實用主義的立場上對通俗藝術進行審美辯護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卻誤解了杜威的美學思想。他過分強調了杜威美學思想中的民主、多元、聯系的特征,卻掩蓋了其中的理想主義成分。按照杜威的思路,人們可以認同高級藝術與通俗藝術之間不存在本質的區別,通俗藝術也應當在美學及藝術理論關注的視野范圍之內,但卻不能認同二者之間不存在區別。可以認同高級藝術和通俗藝術之間的界限模糊不定,但是卻不能因此而否認界限的存在。實用主義美學家應該根據時代與環境的變化,適時地指出舊的界限的局限性,并積極地為建立新的分界標準付出努力。如果說文化的保守主義者與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通俗藝術的不含認同、全盤否定的批評反映了傳統哲學二元論的陳腐思想;那么,對通俗藝術不加否定而全盤肯定的批評同樣也體現著二元論的局限性。這兩種觀點對于通俗藝術的健康發展都是有害的。當然,在對通俗藝術眾多的否定性批評之聲中,舒斯特曼的肯定性批評不僅為通俗藝術在美學上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辯護,更有價值的是他的批評為人們提供了認識通俗藝術審美價值的一種嶄新視角。
舒斯特曼對通俗藝術辯護的第二條理由出自于他對通俗藝術審美價值的認識上。他認為,由于通俗藝術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審美滿足(或審美快感),因此對它不能全盤否定。舒斯特曼的邏輯是這樣展開的:審美快感是構成審美價值的最為重要的成分,通俗藝術可以給人們帶來審美享受(審美快感),因此,通俗藝術具有審美價值。我們由此可以很容易地發現舒斯特曼對通俗藝術進行辯護的根源在于他所主張的審美快樂主義,這也是舒斯特曼新實用主義美學思想的基本傾向。這個邏輯是否成立取決于以下兩個因素:首先,通俗藝術帶來的快感是審美快感。毋容置疑,通俗藝術可以給人們帶來快感,通俗藝術的眾多批評家們也對此表示認同,但是他們卻不將這種快感當作為審美快感。其次,審美價值是否必然表現為審美快感。
關于審美價值與審美快感的關系問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及比較文學教授亞歷山大.內哈姆斯(Alexander Nehamas)對舒斯特曼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與批評。在他看來,“快感不能等同于價值,快感可能是形成價值的一種因素,但價值也同樣取決于其他因素。”[3](P51)內哈姆斯贊同舒斯特曼關于審美客體的看法,即審美客體不應局限于藝術品,也應該將生活包含在內。但是他認為,藝術與生活在美感上有價值的是它們的凸顯的部分,它們不必是給人帶來快感的。審美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在此之前,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可能性。藝術“是對這個世界的時空兩度方式的再現。意識在表現中自身完全敞開,聲音的安排從對位法獨立出去,在熟人之間的微細的描寫,營養元素之間的準備,關于事物運動法則的破譯,構成有機體各元素的結合,以及對生活樣式的展示。所有的這些活動都可以給我們提供某種敬畏感和價值感,但并不一定給我們提供快感。”[3](P51)在內哈姆斯看來,藝術活動也可能讓人產生拒絕、不安全、危險等感覺,但是它們拓展了可能性因而使人們感到敬畏與價值。如果快感與經驗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但價值與經驗的聯系就不是那么密切。即使我們認同它們之間的密切聯系,但是,對有價值的事物與活動的經驗在于它們自身就具有價值。因此,內哈姆斯盡管贊同當代的藝術哲學與大眾對藝術的認識脫節了,但是他并不認為返回審美經驗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所強調的是人們應當如何對藝術作出價值判斷,而不是對藝術的感覺做出價值判斷。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舒斯特曼與內哈姆斯兩人之間的分歧所在:前者強調審美經驗對于人們如何解釋藝術活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審美經驗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們可以給人們帶來快感,因此審美價值(或者說藝術品以及其它審美客體的價值)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使人們產生快感。而內哈姆斯則主張快感不是價值的決定性因素,價值是藝術品或其它審美客體的內在的因素,與審美經驗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比較起來,我們更認同舒斯特曼關于審美經驗與價值的看法,即藝術價值只有在審美經驗中才能被人們認識。但是,舒斯特曼的觀點也存在著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地方。無可否認審美快感是審美價值的一種形式,但是審美快感卻不能等同于審美價值,因而從審美快感的角度去辯護通俗藝術審美價值合法性的邏輯推論就不是那么充分。
舒斯特曼并非是對通俗藝術辯護的第一位哲學家,在他之前,美國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在1974年已經對通俗藝術做出過辯護。甘斯承認通俗藝術在審美上無法達到高級藝術的水準,但是對于身處社會底層的大眾而言,由于他們缺乏必要的教育和閑暇,因此也就無法享受高級藝術,只能選擇通俗藝術作為欣賞的對象。但是,必須承認大眾欣賞通俗藝術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一旦人們具備了欣賞高級藝術的條件,就不應該再留戀通俗藝術。正是基于高級藝術始終高于通俗藝術的認識上,甘斯反對一個人總是沉浸在通俗藝術之中,贊賞人們對高級藝術的刻苦學習和不懈追求。顯然,甘斯承認高級藝術和通俗藝術在審美價值上的差異,他只是辯護了通俗藝術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舒斯特曼認為這種辯護不僅沒有為通俗藝術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反而鞏固了人們對通俗藝術的偏見,是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下對那些缺乏教育和閑暇去欣賞高級藝術人們的寬恕。“這種對通俗藝術的社會學上的同情損害了對它的真正辯護,因為這類辯護實際上繼續維護了它們所反對的關于通俗藝術審美赤貧的神話,這正如它們鼓勵了關于社會和個人成為碎片的觀點一樣”。舒斯特曼將自己為通俗藝術辯護的立場定位在責難的悲觀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和頌揚的樂觀主義(通俗文化協會)之間,這種中間立場對通俗藝術采取的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說,“既承認通俗藝術嚴重的缺點和弊端,也認可它的優點和潛能。”[1](P177)舒斯特曼主張的中間立場和改良主義態度無疑是值得尊重和學習的,問題是他在對通俗藝術的辯護中是否堅持了這種立場和態度呢?他對甘斯觀點的反駁既反映出他對通俗藝術的審美價值的認同,又含有將通俗藝術的審美價值等同于高級藝術審美價值的傾向。筆者對前者表示贊同,但對后者卻持有懷疑。在《實用主義美學》的第七、第八章節,舒斯特曼教授具體分析了存在于當代美國的兩種通俗藝術形式爵士樂和拉普,以此而展開了對通俗藝術的審美辯護。在這兩章中,舒斯特曼逐一批駁了種種對通俗藝術的完全否定性批評,也逐一論證了通俗藝術具有同高級藝術一樣的審美價值。筆者在仔細閱讀過這兩個章節之后卻發現他的辯護是一種完全肯定性的頌揚。雖然舒斯特曼在為通俗藝術的辯護中顯示了他深厚的哲學素養及敏銳的藝術鑒賞力,筆者也在閱讀這些章節的過程中獲益頗多,但是卻不能因此而消除對他所強調的中間立場和改良主義態度的懷疑,即認為他偏離了這種立場和態度而陷入了他所反對的“二元論”的泥沼。我的懷疑是否成立有待于下文對他為通俗藝術辯護內容的具體分析。
舒斯特曼在全面考察了對通俗藝術的各種批評之后,將它們總結為以下6個方面的內容:(1)通俗藝術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審美滿足,盡管通俗藝術可以讓無數人獲得享受,但這種享受通常被批評為虛假的審美享受。(2)通俗藝術不能提供任何審美上的挑戰或能動的相應,通俗藝術的簡單形式只能引起一種被動的消費。(3)通俗藝術不僅形式簡單而且內容膚淺,不能引起智力上的積極參與。(4)通俗藝術是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商品,必然具有標準化、技術化和批量化的特征,而與藝術的原創性、個體性要求背道而馳。(5)通俗藝術缺乏審美的自律性和反抗性。(6)通俗藝術始終沒有獲得適當的形式。[1](P177-200)我們可以將這6種基本的指控進一步簡化,從審美經驗、藝術形式及審美自律性三個維度將它們歸納并區分開來:(1)、(2)、(3)主要涉及了通俗藝術的審美經驗問題,(3)、(4)、(6)主要涉及了通俗藝術的形式問題,(5)主要涉及了通俗藝術的審美自律性問題。這些內容是通俗藝術的批評家們通過比較分析高級藝術和通俗藝術后獲得的。批評家們認為高級藝術可以為人們提供審美經驗,而通俗藝術不能為人們提供真正的審美經驗;高級藝術具有創造性的、個體性和復雜性的形式特征,而通俗藝術的形式特征則是標準化、定型化和單調;高級藝術體現著審美的自律性以及藝術對生活的反抗上,而通俗藝術則是他律的、媚俗的。
批評家們對通俗藝術的指控建立在現代美學的基本原則上。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批評家們為高級藝術和通俗藝術之間設定了種種區分的標準,將二者嚴格區分開來。舒斯特曼首先批評了現代美學的基本原則(比如審美靜觀、藝術自律等)在后現代語境下已經陳舊過時了,但是他仍然大部分采用了適用于高級藝術的現代美學原則為通俗藝術提供辯護,并且得出了通俗藝術可以在審美經驗、藝術形式方面與高級藝術具有相同的價值。他完全否定了現代美學的審美自律性原則,將其看作為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并認為高級藝術與通俗藝術一樣是他律的。在他看來,通俗藝術的批評家之所以頌揚高級藝術而非難通俗藝術,是因為他們“根據著名的天才作品來思考高級藝術,而通俗藝術則典型地被等同于它的最普通的作品。”而他認為“正像高級藝術不是完美無疵的杰作的集合,通俗藝術同樣也不是一個沒有差別的、缺乏趣味的地域。”[1](P172)總而言之,與通俗藝術的批評家們過于強調高級藝術與通俗藝術的界限并且全盤否定后者的審美價值不同,舒斯特曼則辯護了后者的審美價值并取消了二者之間的界限,這顯然違背了他所主張的中間立場和改良主義的態度,因此也無法避免哲學二元論的局限性。
“實用主義不過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范疇’和假定是必須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4](P37)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歸納并總結實用主義時得出了上述結論,這個結論體現了實用主義哲學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即根據命題的效果來判斷它的真偽。我們無須對實用主義“這種向后看”的方法所造成的相對主義結論進行指責和批評,但必須對這種方法的正確性與可行性保持一定的警惕。因為這種方法必然要首先對命題的效果有明確的認識,然后才能對該命題進行價值上的判斷。然而,一個命題或一個事件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以及解釋的深入可能產生無窮多的后果,這就很容易造成判斷的局限性甚至從學理上講無法進行判斷。當然,在特定的語境下,這種方法依然具有操作上的有效性。因此,我們不妨借助它對舒斯特曼教授為通俗藝術所做出的審美辯護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與批評。
從目前看來,我們并不能夠清晰地看到舒斯特曼為通俗藝術辯護所產生出來的實際效果。因此,我們也就只能夠從他為通俗藝術辯護的初衷(即他所設想的效果或目的)出發進行批評。
舒斯特曼認為,“即使對大眾文化的辯護幾乎不能實現消費這種藝術的那個被統治群體在社會-文化上的解放,但它至少能幫助我們解放自己那些被統治的部分,這些部分同樣受到這種高級文化的孤傲獨尊的主張的壓抑。這種解放,與它對文化壓抑的痛苦認識一道,或許能夠給范圍更廣的社會改革提供刺激和希望。”在他看來,為通俗藝術提供審美的合法性以及對其審美價值的辯護可以使人性中被高級文化所壓抑的成分得到解放,進而由此為更廣范圍的社會變革提供條件,這便是舒斯特曼為通俗藝術辯護的目的,也是他的預想的效果。這里,他同樣采取了與通俗藝術批評家們截然相反的態度。他認為那些對通俗藝術的指責以及取消其藝術合法性的批判實際上代表了一種禁欲式的克制形式,是受到柏拉圖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審美感性魅力的消極抵制。
準確地評價舒斯特曼對通俗藝術辯護涉及到美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即美學的基本精神是對感性的頌揚還是對感性的培育。美學的建立者鮑姆加通在提出這個概念時將其定義為“感性認識的完善”,這其實意味著美學的目的是將不完善的感性認識(丑)提升到完善的高度,是教導人們怎樣更高級的控制感性而不是對感性的增強。其后,浪漫的詩人兼美學家席勒在鮑姆加通的基礎進一步明確了審美教育的任務,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席勒希望通過對人性進行審美教育可以對世界有所幫助,審美教育更準確的說,也既是對感性的訓練與培育,在此基礎上將處于“物質的狀況”的人們提升到“審美的狀況”。簡而言之,德國的理性主義美學傳統強調通過藝術的形式來約束自然的感性,而舒斯特曼則出于美學的民主主義考慮而倡導感性不應該受到因傳統而制定下來的美學思想的約束。由于論文的篇幅所限,本文不對這個問題進行更為詳細地析。我們可以將其簡化為一個較為簡單的問題,即我們是否應該對人性中的某些部分采取壓抑和控制的策略?或者是說人性中的某些部分是否應該受到抑制呢?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縱然是高級文化對人性的壓抑含有錯誤的因素,但完全取消壓抑又必然地給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生存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人性中被壓抑成分的解放并不意味著人的解放,它還可能導致人被一種新的形式所奴役。德國美學家維爾茨告誡道,“審美倫理學要求人們保持足夠的警惕性,不僅要意識到每一個范式都是特殊的、各種范式可以共同存在這樣一個事實。同時,還要充分意識到任何一個范式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排他性,都排斥其它的范式。”[5](P73)因此,從目的上看來,舒斯特曼認為他對通俗藝術的辯護具有積極的解放人性的意義,而忽視了這種辯護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總而言之,舒斯特曼教授對通俗藝術的辯護凸顯了通俗藝術的審美價值,并將美學的合法性賦予了這類一向遭受美學家們批評指責的藝術。他試圖通過對這類藝術的美學分析從而改良通俗藝術的制作和接受狀況,并消除長期以來設立在通俗藝術和高級藝術之間的界限,這明顯地體現了他美學思想的民主的精神。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話語看作是舒斯特曼為通俗藝術辯護的基本目的,這種辯護大致可以達成上述的目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參考他對美學最高作用的規定,舒斯特曼在《實用主義美學》中對此作出了如下的敘述:“美學的最高作用,是增進我們對藝術和美的經驗,而不是制造關于這些概念的語言定義。而且,增進我們對藝術的經驗,不只是意味著增進我們個人對藝術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為藝術不僅是內在愉快的一個源泉(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而且也是賦予日常生活的社會運行以雅致和優美的一種實踐方式。”[6](P3)那么,對通俗藝術的審美辯護是否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這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取消了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的界限也就取消了現代美學建立的各項原則與標準,這些原則和標準被取消之后必然會導致藝術和非藝術界限的喪失,進而造成人們對藝術自身的混亂。即使是通俗藝術具有了審美合法性的地位,并且它的創作和接受狀況也因此得到改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日常生活的運行就會更加雅致和優美,因為通俗藝術的興盛將導致大眾對經典藝術關注度的減退,也就可能將人們的行為變得更加的粗俗化,這中后果也正在從美國與中國的社會現實中顯現出來。
[1]Richard Shusterman:Pragmatist Aesthetics,Second Edition,Rowman&Littlefied Publishers,Inc.
[2]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 Inc.
[3]Alexander Nehamas,Richard Shusterman on Pleasur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Winter 1998.
[4]詹姆斯:實用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5]Woflgang Weitz,Undoing Aesthetics,Translated by Andrew Inkpin,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
[6]理查德·舒斯特曼.實用主義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