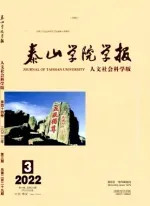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南齊書》的文體構成及其語料價值
黎平
(貴州大學 中文系,貴州 貴陽 550025)
《南齊書》是南朝梁代蕭子顯所作的史書,是研究中古漢語的較好的語料。其所錄文獻基本上是南朝齊代的作品,史書的作者和史書的內容可以說是同一時代的,而正史又較少有被刪改的可能,因此語料時間和內容的可信度都很高。它所反映的語言處于中古中期,時間跨度大約在100年左右,可以看作是一個共時平面,因此語料所反映語言現象的系統性強。本文從另外一個角度即文體的豐富性來討論《南齊書》的語料價值①。
一、文體構成分析
從整體來看,《南齊書》是史書中的紀傳體。但這個“體”,是史書的體例,不是“文體”所指的體裁。一本史書只能有一種體例,但可容納各種文體。《南齊書》包含的文體豐富多樣,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散文,一類是韻文。它們的區別在句式和韻律上。散文大多句式長短不一,不押韻,不講究節律;韻文則句式工整、押韻、講究節律。因此,在功用上,韻文擅長“表情”,散文擅長“達意”。
散文有五種體裁:詔令體、議論體、記言體、敘述體和說明體。這主要是從文章的用途來分類的。韻文有三種體裁:四言體、五言體、賦體。這主要是從韻文句式的角度來分類的。
1.詔令體,即皇帝、太后等的詔令。例如:
詔曰:“承之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卷1《高帝紀·上》)
上敕之曰:“吾前后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卷40《廬陵王子卿傳》)
2.議論體,即史臣的評論(“史臣曰”)、大臣的奏折以及書信等。這些多為議論性的文字,所以稱為“議論體”。例如:
(嶷……又啟曰:)臣自謂今啟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為微臣往事,伏愿必垂降許。(卷22《豫章文獻王傳》)
(顧歡……上表曰:)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卷35《顧歡傳》)
史臣曰:郁林王風華外美,眾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卷4《郁林王紀》)
太祖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卷23《褚淵傳》)
3.記言體,即書中人物的對白。例如: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卷34四《虞杲之傳》)
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卷33《王僧虔傳》)
4.敘述體,即本紀、列傳中史臣的敘述性語言。例如: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斗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酂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勛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儁,儁生輔國參軍樂子,宋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卷1《高帝紀·上》)
5.說明體,即“志”中史臣的說明性語言。例如:
天符瑞令,遐哉邈矣。靈篇秘圖,固以蘊金匱而充石室,炳《契決》,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啟覺天人之期,扶獎帝王之運。三五圣業,神明大寶,二謀協贊,罔不由茲。夫流火赤雀,實紀周祚;雕云素靈,發祥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為盛;魏膺當涂之讖,晉有石瑞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偘撰《圣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撰《瑞應圖》,其余眾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為志云。(卷18《祥瑞志》)
6.四言體,這類主要有廟堂歌辭、史臣的“贊曰”等,這些韻文大多是四言一句。例如:
皇帝升壇,奏登歌辭: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卷11《樂志》)
7.五言體,這類主要是民間歌謠等。例如: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翣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腳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卷19《五行志》)
8.賦體,這類主要是文人寫的賦、銘之類。例如:
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卷41《張融傳》)
二、文體差異及其價值
《南齊書》中各種文體語言風格存在顯著的差異。有的文體句式大多較短、變化較多,語言生動活潑、淺顯易懂,對話感強,明顯體現出口語風格;有的文體則句式整齊、長句較多、修飾較多、關聯詞較多、述論性強,同義詞語極多、同義表達形式多,有時語義較為含蓄隱晦、甚至好用典故,體現出典型書面語的言語風格。文體與言語風格間的對應性也必然導致文體和語體之間有很強的對應性。呂叔湘先生曾說:“以文章體制而論,用語體最多的是記言之文,其次是記事文和說明文,又其次是抒情文和議論文。”[1]呂先生這里所說的“語體”,指的是“口語體”,也即通常所說“言文”的“言”。在研讀《南齊書》的過程中,我們對呂先生的這種說法深有同感。《南齊書》的記言體“言”的成分最多,詔令體和議論體“文”的成分最多,而敘述體、說明體則介于二者之間。
《南齊書》豐富的文體為語言研究提供了一些便利,其主要體現是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古代文獻中的語體分析。這從一個方面體現了《南齊書》獨特的語料價值。
文體和語體之間有很強的對應性。我們對語料中的文體加以區別,將不同風格的文體中的語言項目作為取樣的對象,進行相關的數據統計和頻率分析,這樣就可以得出語言中區分“言”“文”語體的重要參數。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統計語言現象在幾種不同風格的文體中的分布情況,然后相互比較,以分析考察項目的語體屬性。這種研究方法,可以稱為“文體分布比較”法。
例如:我們對《南齊書》幾種文體中人稱代詞、總括副詞、處所介詞及牽涉連詞這四種二級詞類的分布頻率和功能進行了考察,由此可以看出它們在語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的明顯差異。從分布頻率和功能上看,第一人稱代詞比較明顯地分為兩組:“我、身、儂”和“吾、余、予”;總括副詞也比較明顯地分為兩組:“皆、都”與“并、悉、咸”;而處所介詞引導的介賓短語,做狀語和做補語這兩種功能在文體中的分布也存在著對立。據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在語體屬性上,上述三個方面中前者大致屬“言”,后者大致屬“文”。
通過語料中的文體的區分來研究語言成分的語體屬性,這一作法無疑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我們過去進行語體屬性的判斷多憑語感。“憑語感來定性”是語言研究中常見的一種“內省法”,而當代的人們對于古代漢語,缺少的正是這方面的語感。即使是一些造詣很深的古文家,也不能保證他們具有與古人一樣的語感,他們對于古人言語的理解也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失真”。這一方法即使在現代漢語研究中也常常會導致因語感差異而各執一詞的尷尬局面。因此,我們認為,用可操作可驗證的文體分布數據分析代替傳統的“內省法”,可以說是方法上的進步。
“文體分布比較”的研究不僅可以從共時的層面幫助我們分析語料中的語體差異,而且可以從歷時的角度幫助我們及時捕捉到某些語言演變規律的信息。我們知道,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其演變只能是漸進的。新的語言現象出現時,不可能一下子在言語社團全面展開,只能是先在某種語體中零星出現。《南齊書》文體的豐富性導致其語體較為全面,這樣它就有可能及時記錄到某些能代表語言演變規律的實際語言的新變化(盡管它也會有較大程度的遺漏)。例如,我們從《南齊書》中可以看出,人稱代詞的“身”在此期流行一時。
“身”的出現最早是在口語之中,是頗為“粗俗”的語言成分(有點類似于“老子”),因此一般文獻中很少出現,就連同時代口語性較強的佛經中也很少見到。而在《南齊書》中,“身”共出現了12次,其中作主語7次,定語4次,兼語1次,均在記言體中。
從另一方面說,《南齊書》是一部正史,它的寫作應該較少受到作者個人語言風格的影響,這樣,它就能在較大程度上避免言語中的個體變異現象。因此,它所記錄到的語言的新變化可信度比較高。這些體現發展變化的成分,在當時的語言中應該既是新的同時又已經是較為穩定的語言因素。這一點跟同時期的漢譯佛經相比顯現得尤其突出。在譯經過程中,由于原典的影響和譯經者水平的限制,這種受個體因素影響的言語變異現象會較多出現[2]。佛經中出現的許多屬于言語變異的現象,很顯然不能體現基于全民的語言的演變規律。因此,今天的研究者不應該把佛經中的言語個體變異和語言的演變混為一談。與此相比,我們更可以看出《南齊書》一類正史在其中某些文體里所體現的語言變化信息的重要性。
三、史書語料的局限性及其應對
當然,我們在充分重視《南齊書》語料價值的同時,也應看到其局限性。總體上說,《南齊書》中“文”的成分要比“言”的成分多。在全書近20萬字的文字中,屬記言體的只有3萬余字。不僅如此,另外在這3萬余字的記言體中,也還存在這些特點。
一是在《南齊書》接近口語的語體中,“文”的成分還占有相當比例。例如:人稱代詞中的“吾”早在東漢佛經中就已罕見[3],在此期的佛經中也大體如此。但在《南齊書》的“記言體”中,“吾”的頻率大體是“我”的四分之一。雖然口語中也有某些正式場合會用到“吾”,但即使將這一情況考慮在內,“吾”的頻率也還是偏高。《賢愚經》中“吾”的頻率在同期佛經中是很高的,但也不超過“我”的十四分之一。總括副詞中的“并”也是這種情況,在《南齊書》的使用頻率遠高于同期佛經。因此無論是歷時的考察還是共時的比較,《南齊書》“文”的成分還是較高。做正史語言研究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語言事實,通過對《南齊書》語體差異的語法表現的考察,我們對正史語言的“文”的特征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
二是在《南齊書》接近口語的語體中,有些新興成分的比例還很低。例如:總括副詞中的“都”,在《百喻經》中的使用頻率超過了“皆”,但在《南齊書》中卻遠低于“皆、并、悉”。處所介詞此期有些新生的成分(如“著、到”)在《南齊書》中卻難覓其蹤影。這可以明顯地看出《南齊書》在反映實際語言新變化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滯后性。同樣是做正史語言研究,何亞南通過對《三國志》及《三國志裴注》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結論[4]。他認為《三國志》的某些語法特征在歷時軸上與某些更早的文獻相比顯示出了較大的滯后性,與幾乎同期的《裴注》的共時比較它竟然也有某種程度的滯后性。看來,研究史書的語言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史書這類語料在漢語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我們認識一部完整的語料中存在著“言”與“文”之間的較強的不平衡性特征。
三是《南齊書》中“言”“文”語體在諸文體中有相混的情況。例如總括副詞中的“皆”與“并、悉、咸”等,在典型書面語體中就有較為嚴重的相混現象。人稱代詞中的“我”混入典型書面語體時與“吾”等發生沖突,以至于它在典型書面語體中的句法功能頻率高低格局產生變異。這又給我們對“言”、“文”語體的分析設置了障礙。必須使用一定的方法才能分離出其中的“言”、“文”區別,雖然這些差別是由于作者不經意中流露于文本的而具有很高的語料價值。有嚴重的“言”、“文”相混,說明史書的語言雖然的確存在著不同語體中所顯現的“言”、“文”差異的兩極,但在更大程度上卻表現出了書面語體中的大面積交叉。這種大面積交叉不僅反映了正史語言所走的“中性”語體的發展道路,還反映了更多的非語言因素對史書語言語體風格的影響。這些非語言因素包括歷來重文輕語的文章觀,史書編寫中的“正統”史學觀[5]。
正史中的這種“文”多“言”少,及一定程度上的“言”、“文”混雜現象,給我們的“文體分布比較”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在利用《南齊書》等史書來進行漢語史的研究的同時,還應該充分參考同期的其他語料。同期可資比較的語料,如《百喻經》、《賢愚經》、《雜寶藏經》和《世說新語》等可作為記言體的參照和補充。這些語料的時間都稍早于《南齊書》。《賢愚經》共13卷,元魏時(公元445年)慧覺等譯[6];《雜寶藏經》共10卷,元魏(公元472年)吉迦夜共曇曜譯[6];《百喻經》共4卷,蕭齊(公元492年)求那毘地譯[6]。這些語料的口語性,學界已有定論。呂叔湘先生[1]曾說:“初期的小說本來全文都近于語體,如《世說新語》是很好的代表。”方一新、王云路對此也有過論述:“由于多種原因(諸如為了便于傳教、譯師漢語水平不高、筆受者便于記錄等),東漢以至隋代間為數眾多的翻譯佛經,其口語成分較之同時代中土固有文獻要大得多,并對當時乃至后世的語言及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7]
[注 釋]
①文中引例所據的版本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南齊書》(王仲犖點校,1972年1月第1版)。
[1]呂叔湘.文言和白話[A].呂叔湘語文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A].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語言學論叢(第24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許理和.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蔣紹愚譯)[A].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語言學論叢(第14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4]何亞南.《三國志》和裴注句法專題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M].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6]呂 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A].呂澂佛學論著選集[C].濟南:齊魯書社,1991.
[7]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漢語讀本[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