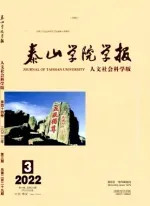思想的蘆葦——讀劉凌《思路雪鴻:一個讀書人的人生觀感》
張鵬
(泰山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近讀劉凌先生的文集《思路雪鴻:一個讀書人的人生觀感》,我被劉凌先生強烈的思想者的精神氣質所感動,年逾古稀的劉凌先生始終保持敏銳的思想活力和學術敏感,辛勤筆耕,積極入世。劉凌先生這種責任感、洞察力和承擔精神,源于憂國憂民的士人情懷,也見之于他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反思、批判和對個體生命的自省、叩問、追索。他數十年來讀寫不輟,體恤世情,埋首書山學海,見證社會轉型的復雜與陣痛,進而為國家民族的苦難歷程、同時代人的曲折生命,也為自我生命的不斷超越,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史證和心跡。閱讀他的文集,我覺得,他就像一棵翠綠的思想的蘆葦,在歲月的風塵中堅韌而淡定的守望著泥沙俱下的滔滔江河。
劉凌的寫作風格堅韌沉實、端莊耐心。他的語言表達,不求絢麗的文采或尖銳的發現,而是以一種責任和誠意,為歷史留存記憶,為記憶補上血肉和肌理。在其高屋建瓴、剖白心跡的自序《應似飛鴻踏雪泥——我的讀寫人生》中,劉凌先生對自己的讀書、思考、為文進行了總結和回顧。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對讀書作用和知識分子的價值判斷。“讀書是突破直接經驗局限,聯系廣闊世界的最佳途徑;能使人更自覺地體察人生,增強自我認知,是人格成長的營養液。人的尊嚴也就是思想的尊嚴,鉗制思想就是踐踏人的尊嚴;思想特權者限制他人思想,是一種犯罪行為。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思想者對人類命運的關切、悲憫、沉思和無能為力的苦悶,正是一切思想者的特征。放眼世界,關注國計民生、現實矛盾和社會變革,乃至人類未來命運,乃是‘知識分子’題中應有之義,雖然‘行之’甚‘難’。堅持獨立觀察、獨立思考、獨立表達、不作俯仰隨人的‘媚時語’,我以為,一切真正的知識分子,或想做知識分子的人,不論地位高低,學識深淺,均應獨立思考并發聲,‘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他的隨筆和論文作為文化史研究的生動個案,為理解20世紀下半葉乃至新世紀十年的中國社會增加了豐富的注釋。在《獨立思想者魯迅》一文中,劉凌深刻體悟到了在魯迅身上確實見不到絲毫奴顏媚骨,這是極為可貴的。劉凌認識到,思想者離不開成長的土壤:“應當為全民族尤其為思想者的獨立思考,創造盡量好的社會條件。當然,真正的思想者不應被動依賴這些條件,而應以其艱苦卓絕的獨立思考,催生相應社會條件,并充分利用現有言論空間”。在追懷王元化先生高風亮節的《清園滋潤綠意濃》一文中,劉凌把傅雷先生與王元化先生的著作進行對比:“《傅雷家書》、《清園書簡》它們都倡導德藝雙馨,治學(藝)根于做人。前者舐犢情深,格局雖小,卻別具洞天;后者悲天憫人,海納百川,又洞燭幽微。后者似或具有更大的歷史深廣度。人們有理由相信,它會長久置于精神提升者的枕邊,也將留在學術史、思想史家的案頭。清園將不斷播灑濃濃的綠意,直到永遠,永遠”。這樣的真知灼見彌散在劉凌文集的字里行間。劉凌的寫作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就在每一個人身上,熱愛現實者理應背著歷史生活。在“世人風范”系列文章中,劉凌論述了知識分子的職責與使命。在《儒家的道義承擔》一文中劉凌歷時性的梳理了“先秦儒家:道義重則輕王公;漢代儒家:屈民申君,屈君申天;宋代儒家:尋顏子、仲尼樂處;明清儒家: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儒家知識分子道義擔當的歷史變遷線索。劉凌指出:“道義承擔的實現,既需要比較寬松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尤其是自由的政治話語權,也需要有知識者的悲憫情懷、社會責任感,清明的史識,道義自信和堅定性,以及殉道、獻身精神。”
劉凌的文字溫婉細膩,圓融通透。在其寫景狀物、情景交融、抒情言志的隨筆如《秦淮尋夢》、《問道江南》、《武夷之游故事多》、《相見時難別亦難——環臺八日游感思》等篇什中可見其柔情似水的一面。他的寫作賡續著中國小品文的悠久傳統,也浸潤著深刻的現代意識。他精微、準確、銳利的藝術感覺和睿智、靈動、富有創見的話語風度,充分展現了隨筆文字所獨具的功能和風采。他對文化生活的敏銳觀察,對文學實踐的積極參與生動練達地注解了文學與時代的親密關系,并通過自身豐富的生命感悟和內心爭辯,呼應著一種獨立而有精神體溫的學人風范。他的寫作接續了散文的古老傳統,也汲取了諸多現代元素。感性與知性,幽默與莊重,頭腦與心腸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他獨特的散文路徑。在關注社會現實的系列隨筆中,他則顯示了直面困惑努力探索的勇氣,比如對愛國主義的沉思、對道德建設的建言、對權利意識的敏感、對以德治國的反思都顯示了他淵博的學識和天真性情的流露,他雄健的筆觸,發現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他崇尚散文的自然、隨意,注重散文的容量與彈性,他探索文體變革的豐富可能性,同時也追求漢語自身的精致、準確與神韻,充分展示他的散文個性。他從容的氣度、深厚的學養,作為散文的堅實根基,在他隨筆的寫作中更是成了質樸的真理。他的學術視野開闊、廣博,思想立論謹慎、嚴密。他通過梳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來的文化視角,為求證當代文學中的諸多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他的分析,善于發現覆蓋在研究對象身上的學術肌理,他的判斷,常常帶著可貴的學術反省和自我質疑。他不回避自己面臨的思想疑難,不迷信單一的解決方案,而是冀望于對眾多人類優秀思想資源的有效清理來緩解內心的焦慮。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從教學崗位上退休十多年來,劉凌先生的閱讀和寫作突破了學科領域和學術體制的局限,讀寫進入游刃有余的自由之境,享受著“我手寫我口”的快樂,他的這本文集既是對往昔讀寫歲月的紀念與總結,更意味著自我精神歷程的拓荒與探索。我們衷心祝愿劉凌先生體健神怡,佳作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