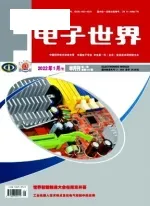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與積累的社會結構
北京師范大學 孟慶峰
農民工是當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事物,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它是半無產階級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結合。因此,農民工不僅僅是農民進城務工的個人問題,或者說農民工群體問題,亦不僅僅只是與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農民工以及農民工問題還具有國家層面上的意義。因此,要理解農民工問題,首先要理解國家和農民工問題之間的關系,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為此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
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
積累的社會結構(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簡稱SSA,亦有人將此概念譯為“社會積累結構”)是美國一批激進經濟學家就資本主義社會為什么會發生周期性波動問題,提出的一個分析概念,其代表人物有戈登、愛德華、里奇、鮑爾斯、E.韋斯科普夫、M.科茲、麥克唐納夫等。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對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與停滯相互交替的內在機制作了深入研究。早期關于SSA理論范式強調特定制度結構提供的穩定性,近來其研究重點轉為如何促成新的SSA。
(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早期觀點
SSA這個概念是由戴維.M.戈登于1978年提出來的。它源于一個極其簡單的命題,即資本積累既不會在真空中進行,也不會在混亂中進行,而是在一個穩定、有利的外部環境中進行。因此,SSA學派將“影響個體資本家資本積累可能性的政治—經濟環境作為宏觀動力分析的出發點”。“如果沒有一個穩定且有利的外部環境,資本家是不會進行生產投資的。我們將這種外部環境稱為積累的社會結構……積累的社會結構由所有影響積累過程的制度組成”。SSA既包含經濟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制度;既包括國內制度,也包括國際制度。但是,SSA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制度,而僅指那些與資本積累過程緊密相關的制度。
SSA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個長時期的、相對快速且穩定的經濟擴張需要一個有效的社會結構,這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就是SSA。但是,一個SSA只能在一段時期內促進經濟擴張,最終要衰落。其后將是一個長時期的停滯和波動時期,一直持續到一個新的SSA出現為止。
(二)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近期的發展
近來SSA的理論范式更多的聚焦于新的SSA是如何出現的。科茲(2004)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完全是內生的,但危機的解決方法卻不完全是內生的,資本主義遠沒有轉變成一個所謂可以自我調節的理性文明的實體。
鮑爾斯等認為,SSA不僅塑造了資本家之間、工人之間以及其他階層和群體間的關系,定義了國家在經濟當中的角色,同時它還決定了資本家與外國資本家或其他生產組織的外部聯系。美國的戰后SSA就是基于這四方面的制度設定:美國霸權統治下的和平、勞資集體協議、資本—公民合約以及對國內資本競爭的遏制政策。
二、中國改革時期積累的社會結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序幕。中國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國家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
波蘭尼對市場模式的演進過程的研究表明,市場模式所體現的交易或交換原則并沒有壓制其它原則,如互惠、再分配,而獨自擴張的傾向。一個自發調節的市場必須把社會制度性的分離為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也就是說,自發調節的市場是國家構造出的。這種虛構性,在勞動力、土地和貨幣身上體現的極為明顯。正是在這種虛構的幫助下,關于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實際市場才得以組織起來。
(一)改革時期SSA的形成:國家對經濟的塑造
按照波蘭尼的觀點,自發調節的市場機制有三個主要重要組成部分: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改革開放至今,可以劃分為兩段,前一階段大約從1978年到1997年,是產品市場的形成,后一階段從1997至今,是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建立。
(二)中國改革時期SSA特征
3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巨大成功。從經濟上看,經濟增長創造了持續30年年均9.8%的世界奇跡。從國際地位看,GDP總量在世界各國的排位,按匯率折算,從改革之初的第10位上升到第3位,進出口總額由27位上升到第三位;更加重要的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正在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
按照SSA學派的觀點,這些成就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是發生在一個穩定的、有利于積累的制度環境中。換句話說,中國在改革后進行的一系列制度變革,為投資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形成了改革時期的SSA。
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干預主義。自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把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把經濟發展視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激勵地方政府貫徹中央政府的意圖。為此,中央政府改變了對地方政府的激勵結構,第一,改變了對干部的考核標準,將其同社會政治指標和經濟績效相聯系。第二,改革財政體制,通過分稅制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財政自給,但與此同時,它還要求地方干部履行稅收的責任。
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解除束縛的勞資關系。就勞動力市場來說,國企改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變了用工體制,在改制過程中,國家拿出巨額資金支付廣大職工的轉變身份補償金和社保欠賬,數千萬工人下崗,進入勞動力市場。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得農民獲得了擇業自由,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業,進入工業領域。目前市場經濟正朝向完善階段發展,但此時社會的自我保護性政策還沒有到位,如200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臺的《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就體現了我們努力的方向。
老工人與新工人:工人的分化。老工人指的是原國有企業工人,新工人指的是農民工。土地集體所有制、戶籍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系政府再分配制度將農民工束縛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老工人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在改制后仍就留在企業或者在其它國有企業找到新工作,處于一級勞動力市場,另一部分則進入了次級勞動力市場。
穩定的國際環境與經濟全球化。自二戰以來,盡管期間也不時爆發局部戰爭,但國際大環境基本處于穩定狀態。阿里吉在探究美國霸權體系興衰時,指出了這種和平狀態背后的制度基礎。二戰后需要一種制度體系維持或確保世界和平,美國霸權體系應運而生。
美國霸權統治下的和平,不僅使得美國獲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而且在經濟上也獲益極大,使其獲得了極為有利的貿易條件。美式和平也為其他國家帶來了發展的機會,反過來又侵蝕了美國霸權體系的根基。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和平的支撐體系由美國霸權向多極制衡機制轉變的趨勢逐漸明朗起來。
自改革以來,中國面向全球的開放型經濟已經逐步形成。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僅為200億美元,而至2000年就上升到2000億美元。從英特爾到包括美國通用公司在內美國大公司,“面臨一個簡單的規則:要么在中國投資,利用其廉價勞動力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優勢,要么輸給競爭對手”。
三、改革時期SSA與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
改革時期SSA形塑了國家與經濟、資本與勞動、勞動與勞動以及國內資本與國外資本之間的關系,而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則是這些關系相互作用的一個綜合表現,或者說它是改革時期SSA下資本與勞動的雙向互動的結果。只有透過這些制度表面,才能較為深入地理解農民工問題。
(一)農民工:缺乏社會保護的勞動力商品化與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在改革之后,隨著統購統銷制度的廢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鄉鎮企業的興起以及戶籍制度的松動,在農村形成了完整的農戶經濟,農戶家庭或者“小商品生產者”不僅可以生產農業產品,還可以生產工業產品;不僅可以以“家庭”單位來從事工業生產,還可以通過雇傭關系或者經由集體所有制企業直接從事工業生產。然而,在市場機制下,資本和農民工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政府偏向城市的再分配制度成了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所加以利用的資源。因此,在改革時期SSA下,半無產階級化沒有起到社會自我保護的作用,相反,半無產階級化與勞動力商品化結合產生了一種缺乏社會保護的勞動力商品化: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
可以說,在改革時期SSA下,半無產階級化實際上變相地補貼了雇主,為企業提供了充足的低工資且富有彈性的勞動力。改革時期SSA不僅為半無產階級化的積累方式提供了制度條件,更是將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進程“定格”在半無產階級化上,使他們不能轉變成真正的工人,只能處于農民和工人這兩種職業之間的尷尬狀態.
(二)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與周期性失業
改革時期SSA使得半無產階級化與勞動力商品化的結合成為促進資本積累的推動器。在國家強調經濟增長的大背景,半無產階級化的資本積累方式又反過來強化了改革時期SSA。
這種外向型的經濟結構意味著,國際市場的景氣波動,很容易就傳導國內市場,進而到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由于農民工處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因此,經濟波動對農民工的影響更強。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曾把鄉鎮企業至于困難的境地,這也是中央和各省政府為危機期間強行推動鄉鎮企業轉制的一個重要原因。鄉鎮企業改制,使得小城鎮喪失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可以說,在1997年是農民工存在形式變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在鄉農民工轉變為進城農民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一次沖擊到了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據農業部2009年1月統計,提前返鄉的農民工數量在2000萬人以上,約占農民工就業總量的15%。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農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了,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城市化結束了,無產階級化過程完成了。因為,當處于經濟周期的蕭條時期或經濟危機期間,大批農民工就會失業,將被迫返回農村,又變成農民,形成周期性失業。這種“風吹草動”使得農民工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一覽無余。而目前所發生的民工荒恰是周期性失業的一個表現。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
②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M].第356頁.
[1]大衛·M.科茲.劉祥琪摘譯.新自由主義與長期資本積累的社會積累結構理論[J].國外理論動態,2004,10.
[2]戴維.M.戈登,托馬斯.E.韋斯科夫,塞繆爾·鮑爾斯.力量、積累和危機:戰后積累社會結構的興衰[A].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編.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5輯),1992.
[3]喬萬尼·阿里吉.路愛國等譯.亞當·斯密在北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4]David M.Gordon,Richard Edwards,Michael Reich,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